推薦序
用一種味覺形容瓦力的文字,我覺得是「酸」
JoJo(KISS RADIO 電台主持人)
用一種味覺形容瓦力的文字,我覺得是「酸」。
有回憶腐敗的臭酸,有身心健康的檸檬酸。
誰准你把音樂寫成這樣迷人的?
講個與《瓦力唱片行》既無關係卻又相關至極的事,誰教《瓦力唱片行》一直讓我想起我的小時候。
每當下節目,我都跟聽眾說,如果想看我聲音甜美但本人帥氣的廬山真面目,可以上「DJ JoJo桑」的臉書粉絲團。但我很少講我明明叫JoJo,臉書粉絲團卻取做「JoJo桑」的原因。
寫這篇推薦序時,我一直使用YouTube播放著陳小雲演唱的〈長崎蝴蝶姑娘〉。
我出生的那個年代,第四台轉到很後面時,會有可以打電話進去,然後就可以看著電視唱歌的那種節目。不少音樂風格很那卡西,好多首台語歌的旋律都是從日本歌翻唱,有陳小雲,有陳盈潔,有白冰冰,好多好多。其中一首,就是〈長崎蝴蝶姑娘〉。我還記得電視中的陳小雲,在一群伴舞者前,副歌時唱著「啾啾桑~啾啾桑~」。
在父親忙碌時,電視音樂陪著他做汽車裝潢,而我還小,什麼都不會,所以電視音樂也忙著在陪我。看著電視,我沒有想要成為歌唱明星的嚮往,反而是記住了當時因為有音樂陪而不孤單寂寞冷的體會。
我想記住被音樂陪著的體會,所以我把「啾啾桑」這三個字帶著走。
後來,那個被音樂陪著的啾啾桑長大了,開始戀愛了。要談分手時,我選擇讓車內無限循環魏如萱的〈困在〉,以為氛圍可以留住他,但失敗了;很抱歉,三角戀必須要了斷,「藥水請蕭邦地擦,謊言請李白地講」,蘇打綠的〈你心裡最後一個〉記錄了我最後的溫柔;「深深的話要淺淺地說」,在職業迷惘時,以前的張懸現在的安溥用〈親愛的〉告訴我:別忘了要快樂……
哎呀對不起,在別人的書裡講自己的事。
瓦力的文字風格大概就是這類型,講的是他自己感受的各種事,還有看似不可能發生但他就是寫出來了的事。
弔詭的是,明明跟他不認識,可你進入到他的故事情節裡會刻骨銘心。那種溫度,跟我小時候聽到〈長崎蝴蝶姑娘〉的溫度很靠近。
「啾啾桑」這一聲喊出來,喊的是做廣播想帶出陪伴感的初衷。
《瓦力唱片行》它讀起來,讀的是被音樂擺渡到彼岸的大人中。
你從我的廣播中被最優化,我從他的心事裡被修復重組。
對於那些討厭卻又愛死了的,我總說,你這傢伙真的是吼……嘖!
瓦力這傢伙真的是吼……嘖!
生命為材料,血淚為薪火──不賣唱片的瓦力唱片行
蘇文鈺(國立成功大學資訊系教授)
你可曾聽過一首曲子時,全身如觸電般顫抖起來?你年少時可曾聽過一首曲子,之後的日子裡,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想再聽到它,像是遊子思念家鄉菜?你可曾聽過一首曲子後,一開始沒什麼印象,那旋律卻如附骨幽靈一般時常在你的腦子裡浮現?
有吧?有啦!
自從小時家裡莫名其妙出現了幾大箱台版西洋流行音樂黑膠唱片以及一台○○七手提箱音響,我指的是把黑膠唱盤,擴大機與喇叭都一股腦給塞進去還可以提著走的那種,我的生命就出現了巨大的改變。我開始要求父親讓我去學鋼琴,未果。於是,開始了長達數十年,不管做什麼事都要有音樂陪著的日子,包含睡覺這件啥都不用做的事在內。隨著家裡音響升了級,家住高雄電子街旁的我又再動手把那套音響給再次升級,鄰居總是會半開玩笑地對我媽說,「你兒子回來了喔?」不知道鄰居心裡想的是這死囝仔怎麼老是把聲音搞這麼大,還是這音樂分享得好?
缺乏想像力的我,就這麼聽呀聽呀,到底音樂裡頭說什麼可是一點也想不出來,要看到「田園」二字才知道原來貝多芬那首交響曲講的是鄉村風景,至於那鄉村到底長怎樣,要等後來看了迪士尼那部配上《田園交響曲》的卡通之後才算有了點概念。我開始去蒐羅音樂背後的故事,例如青年殺死單戀的情人後下了地獄的故事,渣男殺了女主的老爸,最後老爸從地獄裡回來復仇的故事,兔子追著自己的尾巴快速旋轉的故事,學校如何以生產線的方式產出學生的故事,所有的愛情都要用死亡作為救贖的故事。數不盡的音樂與故事伴著我走過一段又一段的青澀歲月,於是年少好友的逝去與初戀情人的別抱等等不如意的人間事,都變得比較可以忍受。多年後到了異鄉,每日搭上夜裡慣於疾駛急停的A車地鐵,以及買了打折票坐進藍音符與百老匯座位的最角落,我算是比較能編織出自己的故事了,也終於知道為何公爵可以在小紙片上隨意寫下音符,幾個小時後就能跟夥伴們上場演出令人激賞的音樂。
真的是要有那個環境以及滿腦子為著音樂而瘋狂的思緒才行。
多年以來,我以每次十公斤的數量買進成堆的黑膠唱片,每一張唱片都用不同的唱針一一滑出動人的音樂,不管是一九三二年曼紐因稚年時由作曲家親自指揮所錄下的小提琴協奏曲,或是一九二七年的卡薩爾斯盛年時所演奏的巴哈《無伴奏大提琴》,還是卡拉揚在一九八九年所演繹的布魯克納《第七號交響曲》,他人生的最後錄音。在卡內基音樂廳裡,卡拉揚顫巍巍地指揮著維也納愛樂演奏布魯克納《第七號交響曲》的那一幕,總是隨著這場演奏之後出版的黑膠唱片響起時浮現在跟前,然後,我總是行如儀式地把卡拉揚一九五○年指揮維也納愛樂演出《費加洛婚禮》的錄音取出來聽,那是卡拉揚即將成為音樂帝王,意氣風發的年代,此時,我總是又會聯想起安迪在肖申克監獄播放這首曲子的場景。朝如青絲,暮已白雪,一切轉成空。
一切都將成空,樂音在空中迴盪又何嘗不是轉瞬成空,一點也留不住。黑膠唱片的特性是每一次的重播都不會是一樣的聲音,每次的唱片演奏都是一期一會,那樂聲就如同流水,而似是一樣的流水卻不會是同樣的水所組成,生生滅滅,生滅滅已,不變的是什麼?因此,痴心的我仍然一直在尋找著故事,跟音樂有關的,不管是音樂家的故事,音樂本身的故事,還是從音樂裡衍生出來的故事,當然,我自己也在寫著故事,只不過寫來寫去,從來沒滿意過。直到有一天,一本藍皮藍骨藍調的書,《然而,很美》的出現。我沉迷在這本書裡,反覆地,一次又一次,看了又看,直到書裡的每一個爵士樂手的悲慘故事都會背了,我甚至還模仿這本書的手法寫了篇小說,那是對早逝的摯友的思念與不捨。
尋找下一本《然而,很美》的過程從沒有斷過。我總是把唱片櫃左手邊的唱片取出來聽完後放回右手邊,日子就這麼循環往復,日出日落,秋去春來,音響器材也如流水一般變換,我把成品廠機一一出脫,慢慢地,從喇叭開始,接著是擴大機,一樣樣換成是自己與友人動手做的或是設計的,包含黑膠唱盤與唱臂,日子在平凡無奇中波濤洶湧滑將過去,我也已待在這所表面上看來似是可以自由來去的監獄二十個年頭,如同安迪一般,來時萬青絲,今已兩鬢雪。
二○一九年中,在臉書上發現了家新唱片行,本想去交關幾張唱片,未料到這唱片行竟不賣唱片,只說故事,音樂故事,鬼故事,還有音樂鬼故事。我納悶著,即使是解憂雜貨店也還賣著雜貨啊!但瓦力老闆用生命為材料,血淚為薪火,徹夜熬煮雞湯,在人心惶惶的歲月中,寂寞無助又徬徨空虛的闇黑心靈得到了撫慰。
二○二○年初,正當瘟疫蔓延時,心中不能說沒有惶惑,收到《瓦力唱片行》的初稿,我對自己說,尋覓的過程可以暫時停歇了,如果那一天終要到來,至少遺憾可以少了這麼一樣了。我細細地讀著每一個字,每一個字所形成的每一個故事流淌過我的心裡,把每一寸受傷結痂的地方熨平,卻又緊接著把似是平坦無瑕的日子的底下挖出新的傷口,血汩汩地流呀!流呀!
三生石上舊精魂,欲話因緣恐斷腸。
五十年來我聽過的每一分鐘的音樂的感受,多數都可以在這本書裡找到,推薦此書給在我生命中出現過的每一個朋友,不論是人間還是天上。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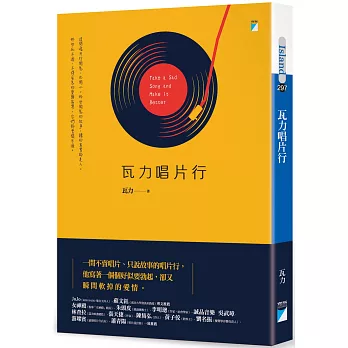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