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版序
在歐洲,從古希臘一直到文藝復興,一般研究文學理論的著作都叫做詩學。「文學批評」這個名 詞出來很晚,它的範圍較廣,但詩學仍是一個主要部門。中國向來只有詩話而無詩學,劉彥和的《文心雕龍》條理雖縝密,所談的不限於詩。詩話大半是偶感隨筆,信手拈來,片言中肯,簡練親切,是其所長;但是它的短處在零亂瑣碎,不成系統,有時偏重主觀,有時過信傳統,缺乏科學的精神和方法。
詩學在中國不甚發達的原因大概不外兩種。一般詩人與讀詩人常存一種偏見,以為詩的精微奧妙可意會而不可言傳,如經科學分析,則如七寶樓臺,拆碎不成片段。其次,中國人的心理偏向重綜合而不喜分析,長於直覺而短於邏輯的思考。謹嚴的分析與邏輯的歸納恰是治詩學者所需要的方法。
詩學的忽略總是一種不幸。從史實看,藝術創造與理論常互為因果。例如:亞里士多德的《詩學》歸納希臘文學作品所得的結論,後來許多詩人都受了它的影響,這影響固然不全是好的,也不全是壞的。次說欣賞,我們對於藝術作品的愛憎不應該是盲目的,只是覺得好或覺得不好還不夠,必須進一步追究它何以好或何以不好。詩學的任務就在替關於詩的事實尋出理由。
在目前中國,研究詩學似尤刻不容緩。第一,一切價值都由比較得來,不比較無由見長短優劣。現在西方詩作品與詩理論開始流傳到中國來,我們的比較材料比從前豐富得多,我們應該利用這個機會,研究我們以往在詩創作與理論兩方面的長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鑑。其次, 我們的新詩運動正在開始,這運動的成功或失敗對中國文學的前途必有極大影響,我們必須鄭重謹慎,不能讓它流產。當前有兩大問題須特別研究,一是固有的傳統究竟有幾分可以沿襲,一是外來的影響究竟有幾分可以接收。這都是詩學者所應虛心探討的。
寫成了《文藝心理學》之後,我就想對於平素用功較多的一種藝術—詩—作一個理論的檢討。在歐洲時我就草成綱要。一九三三年秋返國,不久後任教北大,那時胡適之先生掌文學院,他對於中國文學教育抱有一個頗不為時人所贊同的見解,以為中國文學系應請外國文學系教授去任一部分課。他看過我的《詩論》初稿,就邀我在中文系講了一年。抗戰後我輾轉到了武大,陳通伯先生和胡先生抱同樣的見解,也邀我在中文系講了一年《詩論》。我每次演講,都把原稿大加修改一番。改來改去,自知仍是粗淺,所以把它擱下,預備將來有閒暇再把它從頭到尾重新寫過。它已經擱了七八年,再擱七八年也許並無關緊要。現在通伯先生和幾位朋友編一文藝叢書,要拿這部講義來充數,因此就讓它出世。這是寫這書和發表這書的經過。
我感謝適之、通伯兩先生,由於他們的鼓勵,我才有機會一再修改原稿,朱佩弦、葉聖陶和其他幾位朋友替我看過原稿,給我很多的指示,我也很感激。
朱光潛
一九四二年三月於四川嘉定
增訂版序
這部小冊子在抗戰中由重慶國民圖書出版社印行過二千冊,因為錯字太多,我把版權收回來以後就沒有再印。從前我還寫過幾篇關於詩的文章,在抗戰版中沒有印行,原想將來能再寫幾篇湊成第二輯。近來因為在學校裡任課兼職,難得抽出功夫重理舊業,不知第二輯何日可以寫成,姑將已寫成的加入本編。這新加的共有三篇,〈中國詩何以走上「律」的路〉上下兩篇是對於詩作歷史檢討的一個嘗試,〈陶淵明〉一篇是對於個別作家作批評研究的一個嘗試,如果時間允許,我很想再寫一些像這一類的文章。
朱光潛
一九四七年夏於北京大學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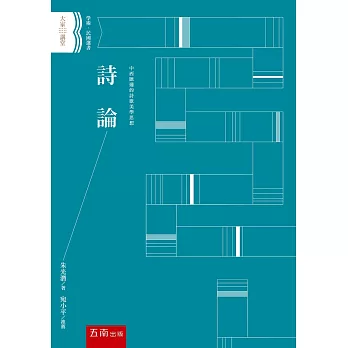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