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集子裏的東西,大多成於一九六九與一九七〇之間。當時鼓動自己寫作一些篇章的情緒,如今已是烏有,已為不同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所取代;然而,一頁頁的黄舊的紙張,卻跟自己走了不少里路,還蜷縮在帆布袋的一角裏,刻刻提醒這過去的實存。此情與詩,蓋在無與有之間,故選出一輯,題曰「鏡花」,即以鏡為有,以花為無。惟花不存鏡,鏡不留花,以其為有,則情去景消並無花影,以其為無,則鏡在人在,及今所反照的,已不是東一簇西一團的香幻,而是反抗者底緊握如心的血拳和斷鏈了。另外一部份,寫作的時候,存着「以諷世也」的念頭,舉凡與心目中的「宏旨」有關的、不論書、報、雜誌,片片斷斷,皆蒐輯起來,作古文新寫或外文直譯;其他,自然更有用心血胎孕而成的。但,目的還是只有一個:「以諷世也」。這裏所諷的世,卻是自己有生廿多年來在漂西泊東的所見。以既存的事實,感念在心,復以外界相合的寓言表之,這就和古人的「資書以為詩」或今人的以「人生的失落與痛苦」為創作的根源很有些距離。現在,望眼之中,唯一的岸,只有「紅堤」。是則,第二輯中所喻的雖是時事,所待者卻是將來了。
年前讀《吳越春秋》,本擬就其中一節刻意重寫,至今卻仍不曾着筆,這裏不妨轉錄一遍,即對並不持「以歷史為殷鑒」的人而言,也當能在其中見出一些熟悉的影像:
吳王……坐於殿上,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王怪而視之。群臣問曰:「王何所見?」王曰:「吾見四人相背而倚。聞人言,則四分走矣。」子胥 曰:「如王言,將失眾矣。」吳王怒曰:「子言不祥!」子胥曰:「非惟不祥,王亦亡矣。」後五日,吳王復坐殿上,望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王問群臣:「見乎?」曰:「無所見。」子胥曰:「王何見?」王曰:「前日所見四人,今日又見二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子胥曰:「臣聞: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向,臣殺君也。」王不應。
是則,吳王的敗亡,並不在於美人的誘惑才開始,而在於伍子胥所說的:「將失眾矣。」類似的戲文和表演,在中國歷史上,彷彿也不時的重做。這裏所要求於讀者的,只是:讀着集子裏的一些篇章時,請不要忘卻,過往有《吳越春秋》,即達現在,還是有《吳越春秋》,而春秋裏的這一段故事,從前是如此,現在也還歷歷的上演着。
至於前面提到過對人生和世界有了與過去相異的看法,那是因為自己從被戰火燒灼的人肉底焦味和被重負所壓迫的人底血腥中打個寒噤,醒轉過來了。像目前這些篇章,也只能代知識份子嗅嗅,未必能使一些高昂的鼻子通暢,更何況裏面還有這許多自己要掙脫掉的頹敗的影子。所要期許的,倒是有一天或能寫作為廣大的人們而不單為知識份子所閱讀的東西。那時,這些都行將泥化於歷史的塵土之中。倘若那一天能及早到來,也就讓這些越早泥化越好。
溫健騮 一九七三年一月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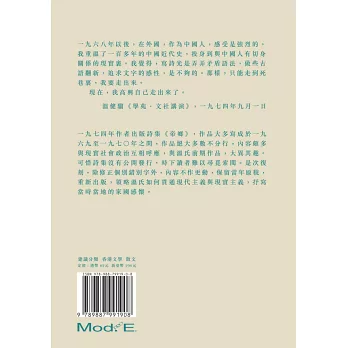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