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花上整個季節凝視
有些作品極易讓人愛上,一口氣讀完後,又永遠忘記它。
包冠涵的作品很不一樣,讓人自願跌入一種悠長的聚散,就像樂意花上整個夏季,凝望一座遠山。
乍看他的小說,富含天真奇趣,我卻覺得這些文字背後藏著很隱密的劇烈掙扎。
他的筆力像刀,可以劈開原有的向度,如同黑洞一樣,令人敬畏,因為他的重力就是比你大。
這是近年來第一個讓我感覺極亮眼的新生代作家。
朱少麟
二○一二年十二月於台北
推薦序
灰色修伯里——包冠涵小說的童幻魅力
這幾年不知分由地冒出許多很會寫的七年級生,以前東海幾年出一個,現在一、二年間好幾個都很強,楊富閔的作品與人氣皆受肯定,周紘立的散文尚有可為,這是冒出頭的,沒冒出頭的更有可為。不是說E世代對文學冷感嗎?跟前代寫作者相比,他們更純粹,彷彿是為寫作而生。這絕不是諷刺,而是跟夢一般真實;只能說他們走向另一個極端,鑽得更深。
早早地開始寫,大量閱聽,呼吸都是文學的空氣,比我們那時代更純粹,因為我們讀的書很雜,也遲遲下不定決心豁進去。但他們就這樣一路走下來,這其中包子(包冠涵)是很特殊的一個。
第一次見他是在他得首獎的評審會上,駱以軍跟袁瓊瓊都大力讚美,因而輕易得第一,他在會上,遠遠看去只是一片模糊,倒是他身邊的女朋友明艷跳脫,龐克風。
一年之後才到創作課來,他話很少,又愛穿牆壁色系,整個人完全與牆壁合而為一,這是個愛躲藏的隱形人,身邊的龐克女友像光,而他是影。
極度害羞,拼命書寫,幾乎兩三週就有新作,都是令人驚喜的作品,這激勵其他人急起直追,創作何需理論,捉對廝殺就是了,記得我們在放假的聖誕節還上課,在冷得要死的危樓上,幾乎全員到齊。
包子來東海之前,大約跟小王子一樣流浪過九十九個星球,謎樣的身世,曲折的求學路程,不知不覺環島一周。他愛顛倒看世界,用眼淚澆灌玫瑰,然後訴說他的星海遊蹤,他的夢幻氣質與純樸本色彷彿是赫拉巴爾的小說人物,具有無盡孤獨打造的鑽石孔眼。
他讓我想起王文興或黃國峻,躲在文學的國度中雕刻文字,只與自己對話,對文學的要求十分嚴峻,文字西化,個性沉默而近於自閉,寫小說再嚴肅的主題都會讓我們發笑,文字咬得很細,但能咬出生命的滋味與趣味:想像力有童話感,也跟童話一般自由,也能打蛇七吋,有股狠勁。
集子裡的小說從二○○三開始至二○一二,寫小說至少有九年以上,作品量已夠出兩、三本小說集,這本集子只有兩百五十六頁,所以是精選。他早已走在自己的小徑上,我相信桂冠與荊棘都不能干擾他,改變他,這算是我多年來看人的直覺與假設。
人都會變,但我也見過不易摧折之人,只是他們所面對的未來,是更危亂、媚俗的未來,不敢想像他們的文學夢會遭到如何之挫折與幻滅?
當此之時世,人更要護住自己,往內探求,掄九十九個星球以扭轉乾坤,往更細微的心靈層次走去,不需改變自己,應該改變的是這個世界。這個世界在該有人性的地方無人性,親情、愛情、政治……;在無人性之處充滿電流,物質、流行、空間、虛擬世界……。我們沒有錯,錯的是這個世界!
只要有此大自信,大魄力,於小王子何懼?
讀過幾年哲學系的他,腦子裡充滿怪怪的可愛想法,有時純真有時邪惡;有時嚴肅有時詼諧,他對哲學的熱情,讓他像沙特、卡繆那一代的小說家,生命的問題籠罩一切,到底什麼是真正存在的事物?他一直追問,上天下地,答案通常是美與感動,他並非存在主義者或古典理性主義者,他像禪宗或達賴喇嘛一樣只相信柔軟的心。修伯里也喜歡描寫動物表達生命的深邃與人性的慈悲:
「窗外的春光明媚,欣欣向榮的麥穗日益豐盈,一切看來生機無限,而死亡卻迫在我們的眼睫。為何這麼美好的春日要用來對照死亡呢?為何這麼甜美的生活情境卻成了對生命的諷刺呢?我實在不該再照實寫下去的…… 」
「而你就像是在老鷹翱翔身影下玩耍的小田鼠,在小麥田裡歡喜地活蹦亂跳,自以為還能好好的活著,卻不知自己早已成為老鷹的囊中物。」
「人總以為自己害怕的是死亡,其實他所害怕的只是死亡的不可知。在即將死亡時你所面臨的不是死亡,人害怕的是自己,不是死亡。當身體進入死亡狀態,人的本質竟會顯現!」(《戰鬥飛行員》)
問包子為什麼每篇都有動物,他說「有了動物,讓我比較安心。」極度怕人與害羞的他,動物就像掩護體一樣,讓他較能探出頭來,動物也是生命思索的媒介,人與自然(世界)的溝通之路。
動物在小說中常只是寓言或隱喻,如今成為小說中的焦點或重要角色,以動物為主題的小說常與哲學、信仰脫離不了關係,可以預見這個世紀動物小說會持續發燒。
仔細讀這些有極短、短篇、中篇的小說集,若干地方有翻譯小說的味道,說沒鄉土味,他也寫了台中與清水,媽祖廟與米糕。有些地方像七等生,但只有一點像。
只能說他像他自己,一個不規則的不規則動詞,不受任何拘束,他讀了四、五所大學,台灣走透透,只學會一招:不上課與躲起來。
他說小時候差點拿掃把打老師,母親被叫到學校,在自白書上寫道:「我採用的是自由放任的教育」,自由散漫的母親養出更自由散漫的人。
也只有在跟他通信時才感到他書寫的全神貫注與嚴肅,讀他的信無人不感動,如果出個書信集應是傑作:
一個幻想的人之所以不相信自己的幻想,不見得是他擔心幻想將會帶他前往到何等恐怖、虛妄或瘋狂的境地,而是他不相信自己的心中有些什麼不會毀壞的印記可以再度喚他回來。也突然想到:也許幻想最美的可能不是終於完造了幻想的國度,而是到達了那個國度後,回返的歸途才會浮現。
他的信常長達數千字,裡面充滿自省與深刻的思考,節錄一小段也許更能表達他自己。
他是一個幻想者,幻想者寫出的小說充滿奇異的幻想是自然不過的事,可以說他早一步搭上少年PI的動物熱,我們可以理解鱷魚、老鼠這些隱喻,那「耳垂湯」呢?我覺得是當中較好的一篇,他討論的無非是存在的事物不一定存在,不存在的事物也不一定不存在,人物也很鮮明,語言有趣,一篇題旨複雜的小說,被他輕輕幾筆解決,沒有太多說理,是較成熟的作品。
相較之下,〈老鼠與海〉說理的部分似乎太多,然篇後老教授的信令人心醉神迷,讓我們訝異原來小說與哲學互為表裡理所當然不過,然而我們拋棄哲學有多久了?
當通俗文化與娛樂八卦橫掃一切,哲學消失,分崩離析成生活碎片,哲學就是現實與人生,人心魂飛魄散,文學只有文字表框而無內容,我們都變成庸眾,連寫作人也拋掉深刻、理想……,每篇作品看來差不多,這正是文學的晦暗時代。
哲學並未死亡,只是在轉化,正如文學。在一篇篇追憶與懷舊文字中,我們漸漸失去掌握現在與實有的能力。在新鄉土一再被提出時,正表示我們是多麼缺少新意的一代。
歷史歸來,文學奔向過去;哲學甦醒,文學才有真的魂魄。缺乏思考力的作品無法打動人心。沒有哲學的年代,各種靈異與迷信瀰漫,勵志小品充斥,當有一天我們在捷運上不是聽mp3,而是討論存在與定義的問題,也許我們的文學與心靈才會甦醒。
在七八年級作家中,我看到他們的清新與鬥志,文學是少數人玩得起的藝術,只有往更刁鑽挑剔的方向走,但喜感十足的他們知道如何幽默地作戰。
在眾多同質性高的七年級作家中,包子極好辨識,不管他如何會躲,有一天還是會被記住,他高而帥氣,害羞到講話常發抖,異性戀,滿腦子文學與哲學狂熱,文字極神,他會走出一條他自己的路。
這條路許多文學大師走過:杜斯妥也夫斯基、卡夫卡、卡繆、波赫士……,他只讀經典,不上網,手機放在機車箱子裡,每天都重新出發,對得獎、出書一點都不急,以致到三十整歲在許多人催逼下才出書。
雖然不是我夢想中的最佳選集,他的極短篇好看,短篇精巧,中篇深刻,最能代表他的個性的是首篇兼序〈夢中旅行〉,可比修伯里的《夜間飛行》:「就在那一刻,在暴風雨的空隙中,幾顆星星在他頭上發亮了,像是捕魚籠底部致命的餌,可是,他還是向上飛了,因為他如此渴望光明。」:
他在心裡對我說:「你還在等什麼呢?」
窗外一片墨黑,但我知道,世界就隱匿在這片墨黑之下,
正如流浪之心,往往以日常生活之果實的內核的形式存在著。
妳小心地咬一口,再謹慎地咬一口,不願觸及……。
但總有一天……。
但……總有一天……。
我轉過頭,接住小男孩的眼神,對他說:
「我們就要出發了。」
擁有流浪之心的包子,認真地交出他的第一本小說集,然而生命的果實才咬下第一口,有一天他會揭開那片墨黑,我相信,這也算是另一種「牛皮紙袋的約定」。
周芬伶
二○一二年十二月於台中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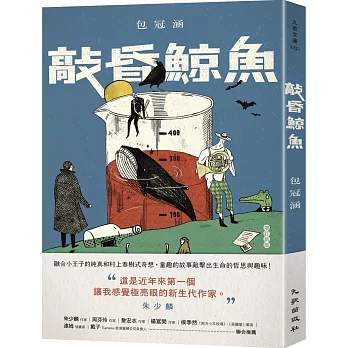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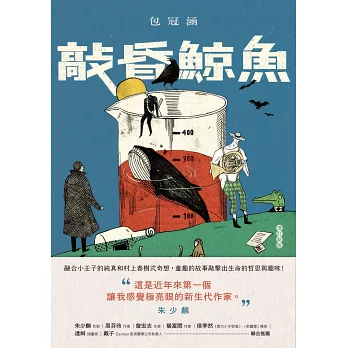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