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個詩學的追踪過程
香港新亞研究所
一開始是大學三年級,暑假回香港,到新亞研究所聽牟宗三老師的《易經》。從此,天地物象的嘉祥之氣,便永恆盤旋在我遭遇到的世情之上。
研究所教室只有一間,徐復觀老師晨早準時上課,課室才到了兩三人,他大聲將整理的筆記寫出,黑板字歪歪斜斜,一層疊上一層,那些用字超好啊!抄!上過《史記》、《漢書》、批評史、《文心雕龍》,所有古籍在徐老師口中筆下,都變成最有肌膚感覺的當代文學,猶如那一層疊著一層的字,每一次都因為灌滿了他的血氣,引我們努力辨識、內化、激勵、驚歎。
唐所長君毅先生,嚮往孔子的教學方式,他將「存在主義」新解,說老師與學生需要互相在對方心中「存在」。所以要小班小制,師生間要有理解與情感;堅持928孔子誕辰是校慶,當天要掛中華民國國旗。新亞追索的,是中國文化真正的存續精神,其實也無意政治,不過,香港政府不方便承認,這個堅持以文化抵抗強權的「基地」。
研究所擁有全港最豐富的綫裝藏書,但孤零零地立於熱鬧繁雜的當年「工廠區」土瓜灣。學生畢業沒有香港文憑,來的,就真正除了學問「一無所求」的人,這些人超容易大笑及快樂。我們早午晚一有空就聚圖書館,週末齊看電影高談濶論與吵架,記得一次,大家直挺挺躺到書桌上,還不停爭論《史記》某故事的微言大義。
名滿天下的三位新儒家,要教我們琴棋書畫,延攬出當年最有身份的老師,義務教學:古琴蔡德允、張世彬、唐健桓;二胡王純(電影《江山美人》作曲);書法唐君毅師母;丁衍庸教畫;牟老師每天下午挑釁學生圍棋。上課教室只一間,研究所只有一層樓(它附在新亞中學上面),我們就在香港這個普遍英語的金融城市,過著完全另類的精神生活。
朱利安先生到新亞旁聽三年,孺慕三位真正的「中國文人」,主動幫我們申請獎學金到法國。可能是牟、徐二位老師的督促授意,入見朱利安時,還問:「我研究的是中國文學,為什麼要到法國呢?」他說:「你可以學習我們研究文學的方法。」
就這麼說,我開啓了一生最重要的道路。
巴黎漢學
我的博士論文,是在巴黎寫,延續碩士論文《李白詩文體貌之透視》,永遠沒完沒了對詩學研究的不滿足。指導老師桀溺(Jean – Pierre Diény),是這輩子遇過,感覺最像中國「古人」的人物。他以研究「古詩十九首」成名,課一週一次,聽眾有些好老了,聽了十幾年。每年講課主題都不一樣,例如五經中「龍」出現的各種情節、不同顏色的訊息……,也研究《世說新語》女性形象、漢賦裡的鳥類、都市描劃等等……。他每年換一個搜索的主題,等於讀了無數遍我們的五經與上古文獻?
桀溺老師對學生盡是包容,他從不提要讀什麼法國詩學,任得我自己摸。還說:「其實中國的好與法國的好是差不多的。」直覺感知這是一句很深的話,當時不能明白。那時候,其實是:「不願意研究我所愛的事物」,但連這個想法都說不出來。只是終日浪蕩,無所用心,把所有時光去周遊巴黎市,愛上各種類的畫展。
終於定了題目:「李白詩中月亮的研究」,因為內在許多疑惑,就用一種最笨的方法,李白一千首詩內三百多首的月亮詩,逐句分析。還撒了一個廣大的網,自《詩經》、《楚辭》、漢賦,及各類唐朝之前總集分集內的月亮意象,我逐一爬疏、抄錄做卡片,分析月亮在每一首詩內的藝術效果,再將李白三百多個月意象,與前人及後輩(至晚唐)一一比較。同時,開始讀法國文學史、詩歌史,終於發現,法國人講文學的方式我很愛,例如莊皮亞李察(Jean-Pierre Richard)的《詩與深度》。
於是,每到巴黎漢學圖書館借書,工程浩大。有次請一位「書僮」好友幫忙,兩人抱著十冊厚厚《全唐詩》,拿一本掉一本。每天到「大學城」的央圖,佔一個窗口位置,有盞中古世紀桌燈,我在哪吃飯、游泳、看戲,下午與流浪漢喝咖啡,讀中國古典詩與法國詩學、一本一本字典。週末,大部分時間看各類展覽,常常跑到龐比度中心,玩一天。
龐比度現當代藝術與古文中的「字」
龐比度是法國現當代藝術展覽重鎮,它的建築要將支架鋼管等等「內臟」,全部暴露外面。自一樓通至五樓扶手電梯,有如血管又如肚中的腸子,每天成千上萬人緩緩上落,透明地,被四方看見。龐比度週圍,卻是幾百年永遠象牙色雕花的屋宇,一大片廣場整日是黑人、阿拉伯人、亞洲人圍坐,玩各種雜耍,唱歌跳舞。有一年,我們華人每日到龐比度排隊,一天看三場中國電影,五○年代最早的「小城之春」、周璇、趙丹、阮玲玉,一直至八○年之後「沒有航標的河流」、「老井」等等……。足足三個月的中國電影、來年又有阿拉伯電影、日本電影……。
我每週進出龐比度,其實不明白那些畫。當然也有羅浮宮大皇宮較古典的,小皇宮、奧塞美術館較「印象」的。看多了,說不出來,但美的顏色,好像會撫摸你,調整你的內臟。剛開始幾年,還是會找尋畫內的「象」,那些戰爭故事、愛神刺中心口的箭,或者星空、花卉仕女或草樹桌巾蘋果。直至有天,看到一位法國畫家巴爾丟(蒂)斯(Balthus, 1908-2001)的大展。那個纖弱的人形,灰暗墨藍的屋宇,是面無表情還是一直將內情佈滿周圍所有色塊與角落?第一次我看「懂」了畫中每一個筆觸都在「說話」,非常震動。那一年,記得在龐比度跑跳著出來,久久不能平靜。
巴爾丟(蒂)斯之後,另年又有俄羅斯抽象派康丁斯基(Kamdinsky, 1866-1944)大展,只有線條與色塊,已完全能夠選出那一張我喜愛,喜愛的原因;之後是科幻的智利畫家馬塔(Roberto Matta, 1911-2002),被他引入太空的迷惑;再來是幾乎感覺有如自體內反射的西班牙畫家塔皮埃斯(Antoni Tàpies, 1923-2012),畫面只有整片整片的黑,偶然不同角落斑白與破裂,呼叫無門、荒涼天地,但美得不能言喻。
每天在「大學城」窗內讀的中國古典詩,忽然每一個字每一個字脫離固定的解釋,跑出來。翻看《左傳》,字裡行間,原來許多故事與心理,主角層次的豐繁,怎會那麼省略?空間那樣廣深?隱在裡面,完全留給讀者自由。而每一種詩,隨著詩人不同,詩內的字也可以跳出跳入。厲害的詩人,讓字交錯橫生舞動,卻還有一條極嚴密的線,有結構、有身體起伏的聲音。
這些起伏,猶如塔皮埃斯大片大片黑白的畫。德國康丁斯基畫內將「象」「抽」去之後,我對於中國象形字造成的詩,字與字間關係的訊息,忽然有了全新的領悟。巴黎最後一年,寫成一篇有關情感故事的長詩。人與人間關係,隨著時間移動,情感深長的,將連綿三界。詩成後,內心的字再不受任何法則束縛,它們跳躍飛動,自古至今,無終無始。只偶然因為動情的某人,將它們牽引出現;因為那人體內的律拍與聲音,吹氣成形。
四、「賦比興」思維與華文現代詩的各種句法
這是我第三本論詩的書,但正式追問自己:「我」有一種詩學嗎?應該說,是自本書開始。「間距」一詞,雖然借用於朱利安先生,該說,朱利安整頓了這個概念,令長久以來生活的狀況,藉以過濾而澄清。不然,我以前也擅用「賦比興」的「興」義。上聯景色「興」句,與下聯內情「應」句,情景並不交融,看似牛頭不對馬嘴,需待讀者將遙遠的雙方關係重新塑造。景與情各處一方,你看見或者你永遠看不見?!朱利安「間距」要義:「繞到很遠的他方,經歷一段歲月,再回到本來熟悉的事物,將有全新的發現。」這還是太邏輯,顯得太固定了,我喜歡《詩經》內任何「景」或任何的「情」,當它們偶然「湊泊」相遇,那種天地間界綫崩落的震動,是難以說的。猶如我讀《詩經》而懂了現代詩;還是因為長期研究現代詩,而更懂《詩經》?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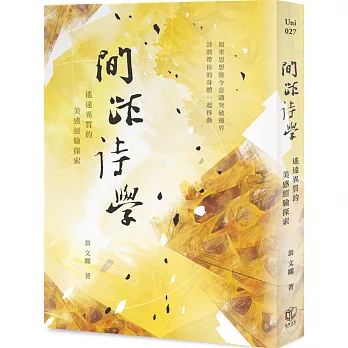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