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白
我幾乎以一個人的力量,來寫汪政權的這一幕往史。
為什麼再要有這一冊類乎蛇足的補篇呢?我有著太多的感想:
首先,我想對自己的寫作有所聲明。當我一開始撰述本書時,開宗明義就曾坦白地說過:「現在純憑記憶來追寫,相信一定會發生很多的錯誤」。果然,就有人出了專書,批評我為「向壁虛構」,為「公然說謊」。我檢討了我所寫的前文,十九被指為虛構為說謊的,我卻都有所本。惟英國對滇緬公路的封鎖,確是已在汪氏離渝之後,我不得不承認這一點記憶上的錯誤。但我並不是在蓄意造謠,假如我要以此來為汪先生辯解的話,對如此一件大事,我又何至留下這樣一個漏洞,以供別人的吹求?但是,雖然沒有被別人指出,而我自己卻發現了不無有些無心之失,這冊的刊行,就是為了要自動更正前書中若干的疵謬。
其次,最初我自己不敢對此書有能夠完篇的信心。在以煮字療飢的處境下,文債山積,不暇週諮博訪,故每出於倉卒成章。更加以我當年微不足道的地位,十分狹陋的見聞,而又以「知之為知之」的態度,大體上所寫出的僅限於我個人親見親聞的一角。若干重要情節的遺漏,自屬難免,我也以此引為莫大的遺憾。在這年餘中,我不斷訪問了現猶羈旅在香港而又確信其當年曾對某一件事曾身親的舊侶,以窮其隱微曲折。無如朋好凋零,半已作古,即或猶健在人間的,亦以幾經世變,百感縈懷,對此陳跡,形同隔世。更有以「往事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偶然」的心情,不願再有所贅述。這一冊的續印,原是為了補漏,而一鱗片爪,仍然遠難滿足我所祈求的願望。
戰後十餘年,在我之前,國人中似還不曾有人寫過對這一幕往史較為完整的記述。不意拙著一經問世,拋磚引玉,竟爾風起雲湧,似以寫汪政權為一時的風尚。就我所能見到的,已不一而足,對我有批評的,更實繁有徒。當我一一誠心誠意地拜讀之後,我有些驚詫,也有些慨嘆。在我所見到的許多鉅著之中,有些人並不在想供給史料,也並且不能供給史料。他們都對汪政權是全無關係的人,有些當年又並不曾處身在淪陷的地區,現在也不想發掘真實的資料。他們只是摭拾一些不經之談,加上自己神奇的構想,以大造其空中的樓閣。而他們卻有著一個共通的原則,是先挾了一個成見,立意要把這一幕時代的悲劇,儘量醜化,儘量歪曲。好像不罵汪政府,就不足以顯出作者的忠貞;不多指出幾個「漢奸」,也就不足以顯得中華民族史上的「光榮」!
有些人寫的不僅是小說,而且簡直是神話,異於我所聞,異於我所見,自不足為怪。但竟有與我同姓同名的人,在書中出現。若說是我,那麼他所描繪的情節,連我夢也不曾做過;若說不是我,何以對這同名同姓的人,我竟會無緣識「荊」!
也有人想以栽贓的手法,指主也和者即為漢奸,而主和的也僅為汪氏。不料他所剽竊得來的資料,處處顯得當年主和者卻另有其人,弄巧成拙,我只有憐惜他處境的艱難。
更有人指我前書中所寫,可信者不足一百字,其人且自命為「史家」,而居然一筆抹煞,乃有此像是苛論的妙論,我鄙薄他這無知的武斷。至於有人說:凡是參加過汪政權的人,都在可殺之列,我又代扼腕於他們的未能得居高位,得以誅盡異己!
真是夠熱鬧的!引來了各式各樣的「珠玉」,實非我始料之所及也!
我一直留心著有關這一幕的記載,有些他山之石,確足用為攻錯。在日本出版的書籍,與報刊上有些國人的著作中,也常常發現我所不克知與不獲知而認為可信的資料,不辭抄襲,標明出處,盡力搜羅,雜之本冊,以補我書之不足。
這一段近史,我前後難已寫了六十萬言,定知遺缺者尚多,而錯誤也定不在少,自己於校閱中,感到因初稿於匆忙中陸續寫成,太多辭意重複,層次凌亂之處,更安得以餘年重加整理呢?甚願讀者諸君的不吝指正,所有一切善意的批評,我自將樂於承教。
西元一九六四年元旦 著者金雄白寫於香港旅次
餘言
經過了四年時間,前後寫了一百八十節,五十多萬字。我感謝讀者對我的同情,鼓勵和原諒;而更難得的是承蒙讀者能相信我筆下所寫的都還不離乎事實。當年汪政權時代的許多舊侶,他們對於那一幕歷史的悲劇,同樣曾身親目擊,雖然每個人所站的角度不同,畢竟對本書也由懷疑而趨於諒解了。
有人說:我這本書只是要為汪先生翻案,也是為了發洩我個人的私忿,結果徒然成為討好了死人而得罪了活人。我不承認這點;我也不管這些。人微言輕的我,沒有力量,而且也不敢妄想對幾乎蓋棺已成定論的汪先生等諸人翻案;甚至在他們生前,恐就不曾有過求諒於後世的意思吧。
當然,本書中有些太率直的內容,或許會使有些人不高興的,而我卻相信他們也終於會對我諒解的。已經抄了家,吃了官司,又戴定了一頂漢奸帽子的人,在劫後餘生的十多年後,再渡著飄零的餘年,才訴出了滿腔哀怨中的一點一滴,書中只提供了事實,而且更儘量地為賢者諱,為活著的人諱,更為位尊者諱,這已經盡了我最大的可能。儘管人們仍會指斥我是滿紙荒唐言的,而在我,則無疑是一把辛酸淚也。有些人也應該回想當年,前塵歷歷,我不是在向壁虛構吧!既曾經逞過一時之快,今天,事過境遷,雖不喜也總應有些哀矜之意吧!
至於在國家存亡絕續之交,犧牲幾個小我,這已是微不足道的事。我認為只要犧牲得值得,也且樂於坦然承受。往事早已成煙,白骨何能復肉?更有何私忿之可言?
那末,我為什麼要寫這一本書呢?既然我生長在這一個時代;而又躬歷了這一幕變局,我應該為歷史作證,我應該向時代交代。無論我的見聞怎樣狹陋;我的文筆怎樣拙劣,既留此未死之身,讓它在掛一漏萬雞零狗碎中把這一段往事留傳下去,供後人的惋惜也罷!供後人的唾罵也罷!
我寫本書的另一目的,我要告訴所有炎黃的子孫,讓他們知道這一群被指為「漢奸」者們,並不如宣傳中想像中那樣地醜惡。陳公博說:「抗戰是對的,和平是不得已。」周佛海也說:「抗戰是為了救國;和平也是為了救國。」所以,我全書中絕沒有非議過抗戰,而且我也不至於為了小我,而昧著良心以左袒「漢奸」。我要以事實來告訴所有炎黃的子孫,假如一國而真有那麼多賣國「漢奸」的話,自將成為中華民族史上永遠洗不清的恥辱;儘管你不曾做過「漢奸」,而民族中會出現數十百萬「漢奸」的話,也就是整個民族的恥辱,任何一個人都不會有例外。現在,讀者們於讀完本書之後,是不是對汪政權中人會感到有些驚奇呢?所有汪政權重要諸人,在生之日,何以敢與敵抗爭?臨命之前,又為什麼會那樣地從容赴死呢?
同時,我更要讓當年與我們作戰的日本人知道,汪政權的這一幕,應該足夠給他們一個很大的教訓了。稍有良心的中國人,不會在威脅利誘下被收買,被壓服的;民族大義,也不會在中國人的心理上輕易消除的。日本有日本的霸道;而中國人自有中國人的權變。他們嘗到過堅軔不屈武裝抗戰的味道,也該嘗夠了曲線的和平抗戰的味道了吧?到今天,日本人是不是已憬然於有五千年文化的中華民族,並不太容易能加以欺凌收買吧?
此外,我迄今還有一個無法解開的疑點:究竟在對外戰爭時,如不幸有部份國土淪陷了,應否該只是為了所謂「紀綱」也者而讓人民被殘殺,元氣被蹂躪呢?還是應該有幾個不知死活的人,在人民生死不得之際出來擔當一下?汪政權這一幕過去了,這疑問,還是讓當年處身在淪陷區的人來解答吧!
一九六一年三月 著者金雄白序於香港旅次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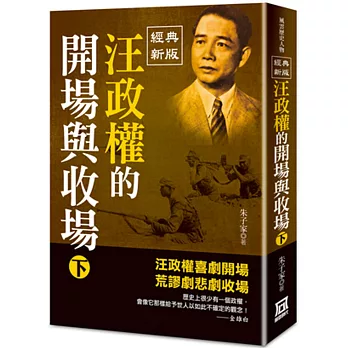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