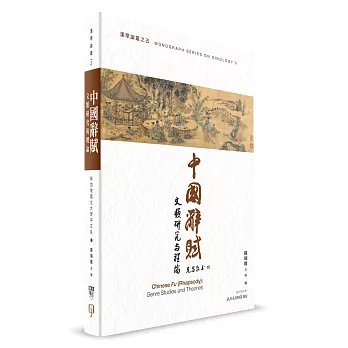序言
略談中國大陸辭賦研究和創作— 新加坡國立大學成立「國際辭賦研究會」開幕式發言
萬分感謝新加坡國立大學文學暨社會科學院、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為舉辦這次國際辭賦研究成立大會,學校專門撥款,花費大量人力、物力,並交由蘇瑞隆教授全力組織。對我們辭賦界同仁來說,這是一個國際性的高規格的辭賦專家會議,因而是一個轉變會風的會議,它關係到我們今後辭賦研究創作品質能否迅速提高的問題。我們大家一定會一心一意,利用短短的幾天時間,把會議開好,並提出我們今後奮鬥的目標。
賦,是中國古代文學中的四大文體(即詩詞、賦、戲劇、小說)之一,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和歷史地位,如清代焦循(1763–1820)和近代王國維(1877–1927)就分別稱讚漢代辭賦為「一代之所勝」(見《易餘龠錄》)和「一代之文學」(見《宋元戲曲考序》)。賦還是中國獨有的文體,為世界其他各國所沒有(日本、韓國、越南等國家也有人作賦,但那是從中國引進去的)。所以美國傑出漢學家康達維在為我赴美講學的英譯本講稿作序時,只好用拼音「FU」來代替。這是中国古代文人創造性的成果,凝結著他們的聰明才智,非常值得我們珍視。
但由於種種原因,最遲到「五四」運動開始,人們就不再理睬賦了,把賦視為社會進步的絆脚石。因為讀經研究國學不能讓國家富强,要從事科學技術,社會才能更快進步,所以從五四運動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三十年間,中國大陸大概只出版過陶秋英女士的研究生畢業論文——《漢賦之史的研究》,約三四萬字。同時也出版山東大學中文系殷孟倫(1908–1988)教授翻譯的日人鈴木虎雄(1878–1963)的《賦史大——要》。有矯枉過正之處,我們尚可理解。因為清末中國科學技術落後吃過太多虧,受到列强的欺淩,割地賠款,國將不國。
1949年之後,賦更被視為封建性的糟粕而遭人徹底拋棄。中國大陸的大學中文系基本不講賦。1957年反右,1958年全國大學「火燒」教學後,賦更淪落為人們臭駡的物件。最典型的是有一部文學史,書中一個大標題就標為《文學中反現實主義的逆流——兩漢辭賦》。作者認為「漢賦大部分是粉飾現實,對統治者歌功頌德的貴族化、典型化了的宮廷文學作品,是統治階級附庸的文士邀寵逞才的工具,是皇帝貴族的娛樂品,……內容極其空洞枯燥、虛僞造作、缺乏感情,缺乏現實生活真實的反映。」「漢賦給後代的影響是極壞的。從漢賦到魏晉的駢賦,唐宋的律賦、文賦,雖然內容有所擴大,形式有所變化,但是越來越趨向墮落了……。」簡單的一段話,就把中國古代兩千年人們聰明才智創作的數以萬計的賦篇否定了。這一點我們就不能接受了。這是極左思潮在作怪。
我們山東大學中文系師生當時也編文學史,書名是由校長起的,稱《中國人民文學史》。顧名思義,這部文學史只講《詩經》、《楚辭》、《漢樂府》等為人民呼號的和民歌民謠等作品,賦自然被拋到九霄雲外,詞也講得極少。有的地方比上面那本文學史還要「左」。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文革中,一些人更把極左思想推向極點,把古今很多作家都打倒,作品都燒掉,古墓、古建築被毀,古畫古書被燒。陳伯達指示北京紅衛兵到山東曲阜「破四舊」,把孔府許多圖書都燒了。他還明白指示:明代以後的碑刻都可以砸掉。許多教授、書香之家的書畫都付之一炬,許多古瓷器、古硯臺、古銅器等也都被砸掉,徹底與古文化決裂。當時上面說,大學還是要辦的,但說的是理工科大學。意即大學文科暫時可以不辦,於是文科系院被下放在農村,幾個學校合在一起。我們山東大學一分為三,中文、歷史、政治、外文學科合到曲阜師院。大家都下鄉勞動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好幾年不招生。後來開始招生是由工農兵推薦的,不用考試。結果小學生也能上大學。教學品質大為下降。總之,在1949年後的一系列運動中,大學文科受到極大傷害,古代文化受到嚴厲批判。在這種情況下有誰敢談論辭賦、研究辭賦。所以從1949至1980年三十年間,中國大陸沒有一篇肯定漢賦或歷代辭賦的論文。充其量是某領導人說〈七發〉好,「它的主旨是說明享樂腐朽的生活是致病的根源,而聽取『要言妙道』……是治病的最好藥師。」〈七發〉是「對腐敗的統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一開頭就痛駡上流統治階級的腐化。」「這些話一萬年還將是真理。」於是大家都鸚鵡學舌,都說〈七發〉好,跟著寫文章讚揚。至於上面不說的,誰也不敢說。當時中國大陸只剩下劉大傑一人有資格寫文學史。還有郭沫若(1892–1978)按某領導人的好惡,寫了一本《李白與杜甫》,大批杜甫,大讚李白,與劉大傑文學史成為文革十年間唯一兩部談論中國古代文學的書。我1962年完成的〈漢四大賦家初探〉,原是山東人民出版社要出版,自然也死於胎中 —— 並被迫燒毀了。
總之,在1949年後的三十年間,中國大陸沒有一篇研究漢賦、肯定漢賦或歷代辭賦的論文。至於對個別小賦的讚揚那是無關大局的。
由於我在六十年代研究過漢賦,研究生論文選擇〈漢四大賦家初探〉 ,對四大賦家做了肯定,有了一定的基礎。所以1981年初我在《文史哲》率先發表〈論漢賦〉,對漢賦作了充分的肯定。1984年我又出版《漢賦研究》,對漢代司馬相如等賦家作了較高的評價。這竟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第一篇、第一部肯定漢賦的文字。
隨後1987年馬積高的《賦史》,1989年萬光治的《漢賦通論》,1990年高光復的《歷代賦論選》,1991年康金聲的《漢賦縱橫論》等也相繼問世。
比大陸早幾年,臺灣張清鐘出版《漢賦研究》約二三萬字,此書是我1988年在西雅圖華大講課時,蘇瑞隆博士送給我的。根據此書提供的參考資料得知:在此之前還有盛世光發表〈漢賦研究〉,嚴秀娟的〈漢賦的分析〉,蘇雪林的〈賦的淵源與演變〉,何炳輝的〈辭賦分類略說〉等短篇論文。大概因為臺灣學術比較自由,個人可以隨意發表意見。
另外簡宗梧先生1980年前後出版《司馬相如揚雄及其賦之研究》、《漢賦源流與價值之商榷》,1998年出版《賦與駢文》。香港何沛雄先生1986年出版《漢魏六朝賦家論略》,1990年出版《漢魏六朝賦論集》。簡、何兩人的論著品質較高。這就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大陸、港、臺發表出版辭賦論著的大略情況。因材料不完整,只說這些。
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深入、思想的大解放,高校教師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了。在古代文學研究方面,也形成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辭賦研究熱潮。1990年我在山東大學主辦了首屆國際辭賦學術研討會。這個會百分百是在康達維教授的推動下召開的。我到美國講學將回國時,康教授提出和我訂一個合作計畫,他翻譯出版《文選》和我的講稿,我舉辦首屆國際辭賦學術研討會和評註《全漢賦》。我不假思索答應了。回國後不久康教授寫信告訴我,我們的合作計畫上報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上面同意了。我收到此信,如坐針氈。山大領導說按規定可資助會議二千元。作為一個普通教師,如何籌集鉅款開會。但事已至此,只好面對。天無絕人之路,經一年多奔走,終於籌到所需款項,舉行了一個備受讚揚的首屆國際辭賦學術研討會。
在會上,我說動香港大學何沛雄先生等主辦第二屆,後又與臺灣政治大學簡宗梧先生商討舉辦第三屆。召開國際賦會走上軌道,現已舉辦十屆。
國際賦會按時舉行,大大推動了辭賦研究的深入發展。現在中國大陸出版辭賦研究專著在百種以上,發表論文數千篇。當然其中主力是我們自己培養的年青博士生,他們已成為辭賦研究的生力軍,有不少人已出版好幾部專著。
現在主要問題是,研究重點還是集中在兩漢部分。大約已出版二三十部相關研究著作。我在首屆國際辭賦學術研討會上就提出要賦的研究年代向下發展,當時自己也寫三國賦論文,以後又寫「竹林七賢」等數篇論文,但我的呼籲作用不大。對魏晉南北朝賦的研究主要是程章燦和于浴賢等在關注。這階段賦多,好的賦也不少,研究需要加強。唐宋以後賦的研究主要只有韓暉、詹杭倫、劉培、趙成林等少數人涉足。元明清賦研究人數更少,只有詹杭倫、武懷軍、李新宇、孫福軒幾人眷顧。賦史只有兩種,而且是少數人在極困難條件下寫的,只能說是嘗試。我早有鑑於此,有意安排我的博士生們在選擇畢業論文課題時,每人研究一個歷史階段的辭賦。我想,他們人多,收集資料比較完備。一旦條件成熟時,可在各人論文的基礎上撰寫一部資料較完備、內容較充實、評價較準確的中國賦史。這個課題寄希望於我的博士生韓暉、劉培、武懷軍等教授。寫辭賦理略談中國大論史的有一人,也就是我的博士生冷衛國。但他只寫到唐代以前,該書已在印刷中。以後他應繼續寫下去,完成整個辭賦理論史,這個工作意義甚大。辭賦藝術史(講賦與音樂、詩、畫、雜技等關係)余江已寫到唐,並已出版,以後應繼續寫下去。這三部史,我相信我的愛徒都能很好完成。
我以後如有餘力,將繼續做辭賦評註工作,蘇瑞隆博士也參加。《兩漢賦評註》早已出版。《三國賦評註》也在去年夏季交稿,大概今年底能出版。一年前我們已開始《兩晉賦評註》的校註工作,蘇瑞隆教授和我的博士生武懷軍、鄭明璋、李丹博教授都參加此項工作。
我們這項工作對今後編輯歷代賦彙編會有所幫助。說到歷代賦彙編,原來是馬積高先生在做,但未能完成。因工程巨大,現在難有這樣氣魄,也難有這樣獻身精神,我們只好等著。相信各個階段賦都會有人詳細研究,會為這個工作提供有利條件。
人們常說,辭賦出盛世,這話大體是對的。這一點,我們只要看看為什麼漢賦在漢武盛世興旺起來,看辭賦所描繪多為盛世的氣象,就大體明白了。當然,賦也寫個人的心態,寫個人的不得志,或哀歎祖國被欺淩等等,如東漢趙壹的賦,禰衡、王粲的賦,庾信的賦,晚唐一些小品賦,宋初王禹偁的賦,蘇東坡的賦,明末清初一些抨擊閹黨,反對異族入侵的賦。又如清末有一批〈哀山東賦〉、〈哀臺灣賦〉就是對統治者的不滿,痛斥清王朝的賣國等。還有〈新疆賦〉、〈西藏賦〉等愛國賦。這類賦較少,描寫社會的另一面,極應得到我們的珍重。
但賦更適宜頌,且看漢代那些大賦,都是從歌功頌德出發,最後才輕描淡說幾句諷諫的話。所以才造成司馬相如寫〈大人賦〉,原意是要諷諫漢武帝的好神仙,可是因為賦「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钜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於是形成了勸而不止的後果。
由此也可見,以司馬相如為代表的大賦作家,寫賦原是為了歌功頌德,為了振大漢之天聲,包括以後揚雄、班固、張衡、左思等所寫的大賦,統統是如此,這是時代使然,也是賦的主要特徵之所在。
今天,中國正處於迅速發展的和平盛世,與其相適應的辭賦創作自然要應運而生。隨著對古代辭賦研究的迅速開展,經過近十年的努力,據我所知,現在有四個刊物在發表新時代創作的辭賦。即北京的《中華辭賦》(雙月刊),安徽的《中華辭賦報》,江西的《中國辭賦》和山東棗莊的《詩詞聯賦》。北京《中華辭賦》的社長、主編都是原中國文化部和新華社的領導人,作者也多是文化界學術界骨幹人物和省市領導人員,講原則有水準,辦得很不錯。這個刊物得到前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劉雲山(現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充分肯定,下鄉都要帶上此刊;中國國務委員馬凱(現為政治局委員)自己經常撰稿寫賦,他認為此刊是他看到最好的刊物之一。我是他們的顧問和專家組主要成員。
《中華辭賦報》是安徽某縣辦的,困於一隅,編輯人員不足。還遍封成員,什麼賦帝、賦王等。我不贊成這種做法。並在一篇文章中說,我們都是為人民創作,為人民服務,不能把自己淩駕於人民之上。但他們轉載我的文章時把上述勸說刪掉。事後我才知道關於《中華辭賦報》刊物還有不少同行都向我表示同樣態度。當然,此刊也發表很多好的賦作,推動了辭賦創作的發展。
在辭賦組織方面,以江西張友茂為首成立「中國辭賦家協會」,去年在北京舉行首屆會議。張友茂熱愛辭賦,竟辭掉原來級別不低的公務員身份,全力治賦辦刊物,組織不同層次賦會。聊城師大副教授布茂嶺,兩次在聊城主辦賦會,成績顯著。他聰明過人,詩賦張口就來,庶幾倚馬可待。他已創作詩賦成百篇。「魯南辭賦協會」核心人物韓邦亭是位作賦能手,先後已獲得數次全國性辭賦比賽大獎,近又獲十萬元的頭等獎。成都魏明倫是一位著名的戲劇家,兼任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他也是舉國聞名的辭賦家,完全是自學成才,聰明過人,人稱鬼才,十分難得。南通袁瑞良也是個聰明過人的才子,他下筆成誦,文字暢達,有大氣。新疆王宇斌是中國西陲的才子,作賦數十篇,每賦一出,人們爭誦。已故詩俠錢明鏘,老作家深圳顏其麟,淄博王金鈴,西安姚平,北京張心豪、王鐵,瀋陽孫五郎,深圳賈玉寶,溫州周小明,錦州陳逸卿,河南劉臻仲、孫繼綱、譚傑等等,不能一一細述,他們都是辭賦創作戰線上的生力軍,為辭賦的復興繁榮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
據不準確估計,在短短一二十年中,有數以千計的人寫賦,老人、青壯年、高級政府官員、部隊將軍、大學中學教師等都有人踴躍參加創作。略談中國大陸辭賦研究和創作比班固(32-92)在〈兩都賦序〉描繪的漢武盛世競相作賦的高潮還要熱鬧。創作辭賦總數在數萬篇以上。這是之前所無法比擬的。
在肯定辭賦創作繁榮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其不足。
一、主要是部分人學養稍嫌不足。
現在寫賦的作者多是民間人士,他們原來較少接觸古代辭賦,憑興趣願望就加入辭賦創作隊伍。須知,在古代諸文體中,創作辭賦是比較困難的,藝術準備要求是比較高的。明代山東臨清著名文論家謝榛(1495-1575)在《四溟詩話》裏就說:「漢人作賦必讀萬卷書,以養胸次;又必精於六書,識所從來,自能作用。」南宋沈作喆(約西元1147年前後在世)在《寓簡》裏說:「本朝以賦取士……惟詩賦之制,非學優才高不能當也。驅駕典故,渾然無跡;引用經書,若已有之……窮體物之妙,極緣情之旨,識《春秋》之富豔,洞詩人之麗則。能從事於斯者,始可以言賦家者流也。」試看中國古代著名賦作,哪一位作者不是飽學之士?這要求我們大家多讀書、多練習,不要以為作賦是件容易的事,要寫好一篇賦絕非輕而易舉。中國古代著名賦家,一輩子寫出佳作其實也只有那麼一兩篇。作品在精不在多。
二、對賦創作的艱巨性複雜性認識不足。
左思(約250-305)在〈詠史八首〉其一中說,他「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群書;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可見他自認學養是很充足了。他還有花一年功夫寫〈齊都賦〉的實踐。但為了寫〈三都賦〉,他藉其妹入宮機會移居京師(洛陽),向張載訪問岷邛之事,向陸機訪問吳國的事,還請求皇甫謐審閱他的初稿。他原任隴西王泰祭酒,又「自以所見不博,求為(賈謐的)秘書郎。」秘書郎掌管圖書,他便可以看到各地圖書,有利於修改他的〈三都賦〉。《左思別傳》說:「其〈三都賦〉改定,至終乃止。」嚴可均《左思別傳》註:「其賦屢經刪改,歷三十餘年,至死方休。」可見〈三都賦〉是花費了左思畢生的心血,以致原先嘲笑他、看不起他的陸機(寫給其弟書說:「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後來也絕歎服,「以為不能加也」,放棄了原先寫〈三都賦〉的計畫。這篇賦後來造就了「洛陽紙貴」的佳話。《西京雜記》載司馬相如寫〈上林子虛賦〉是「幾百日而後成」。《新論》謂揚雄作〈甘泉賦〉始成,「夢腸出收而納之……大少氣,病一歲。」張衡「研京」(指寫〈二京賦〉)「以十年」(《文心雕龍•神思》)。
在這裏,怎麼評〈三都賦〉等是一回事,但作者的嚴肅認真態度又是一回事。我們應該學習左思等賦家認真嚴肅的寫作態度。不像我們如今有些人,寫一篇文章往往一揮而就,不再進一步推敲、補充、修改。人有聰明遲鈍之分,但一個人腦子總不可能籠括客觀萬物。調查研究總是不可缺少的。隨意憑空率爾寫作是不可能有生命力的。
上面講過,我們現在寫賦可以說是八仙過海,什麼體式都有。但我們遠沒有創作出一種令多數人比較接受的賦體。古賦(指漢賦)太深奧;白話賦太散漫,缺乏形象;駢賦、律賦太嚴謹。文賦也有人不滿,說押幾個韻而已。我們應努力創作出一種新賦體,使之能更好地表現我們的時代,能獲得廣大讀者的喜愛。中國自戰國以後各個朝代多能創作一種適應當時的新賦體,我們怎麼就不能?通過成百成千成萬人的創作實踐,通過成百萬人的閱讀檢驗,我深信,我們將來總能創作出一種一般高中生就能讀懂、喜歡讀、具有生動形象、簡練、有高尚思想的新賦體。這是大家的期望,是時代的需要,也是我們的責任。
龔克昌
山東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