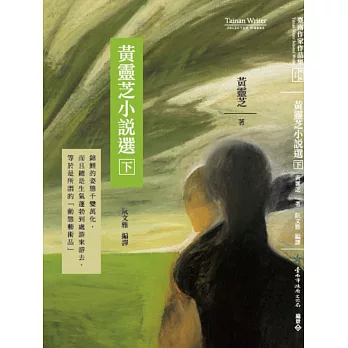譯者序
一切走來都是緣
一九九三年春天,我還是個大學生,在三村昌弘老師的引薦下到了中山北路通天閣,見習了台北俳句會,會晤了黃靈芝老師。當時的我,滿腦子都是現代詩中的傷感與滄桑,只覺得這個日語交雜的定型詩聚會,彷彿刻意與現實隔閡,復古的喜感中充滿了「異國」情調,煞是有趣。過了幾年出國留學,有機會拜讀了黃靈芝老師的日本語文學著作,才開始真正去思考什麼是文學;領悟了文學的重點不在於用什麼語言寫、不在於用什麼樣的美辭麗句堆砌而成,而在於寫了什麼。當我開始真正了解了什麼是鄉愁;這才驚覺自己從小讀著台灣教科書上的名家散文,讀著台灣各大出版社出版的小說,讀著台灣圖書館借來的書本;這些主流文學卻讓我一直童年著別人的童年,鄉愁著別人的鄉愁,滄桑著非在地的滄桑。
黃靈芝的小說可略分為中長篇及極短篇。中長篇偏重細緻的心境書寫,極短篇小說則構圖輕妙,是台灣文學中少見的形式。細緻的描寫映射出孤高敏銳的思維,冷靜的觀察裡蘊含著謙沖與悲憫的心懷。這份台灣的日本語文學,是黃靈芝不願隨著時代改弦易轍,為堅持自己的文藝信念自棄於主流之外,淡泊名利下淬鍊而出的稀有成果。一九四九年,文學青年一夜之間成了文盲,他的無奈,是所有台灣日本語世代的無奈。但他從不嘩嘩,默默秉守著自己的節操與道路,孜孜筆耕留下真實的台灣斷面。就像谷中獨自芬芳的幽蘭。
然而,在動輒以政治解釋一切的台灣戰後,不難想像黃靈芝一路受盡的冷言冷語。也許是為了明志,戰後台灣人頻繁出遊日本,他從不為所動;一直到二○○四年受邀,才以七十六歲高齡首次前往日本,受頒正岡子規國際俳句賞。甚至日本天皇頒佈旭日小綬章,表揚他對推廣日本文化的貢獻,他卻苦笑表示自己甚是困擾,因為他自一九七○年創設並主持台北俳句會以來,從未意圖想要推廣日本文化。在日本朝日新聞社對受獎者的訪問中,他也直言不諱,直白表明自己從來不曾是個親日家,只是親日本語罷了。然而親日本語,其實也非黃靈芝所願,對他來說,這也許也是歷史變動、造化弄人的結果,卻在他耕耘、灌溉下,文學的沃土收成了這些珍果異卉。
曾有人評論台北俳句會的俳人,至今用日語創作俳句,只不過是執著對日語的一份鄉愁。即便如此,歷史產出的文藝都是生命歲月的真實凝聚,都值得崇敬,欣賞與尊重。日本語世代的前輩們,因時扼聲之後大多選擇自費出版自己的文藝作品。沒有出版社,沒有ISBN,至今仍有許多不被台灣正規圖書館所承認或收藏。想想,我們對台灣文學的定義有多麼狹隘。黃靈芝日本語文學的問世與流傳,相信也有著解構主流框架的重要意義。歷史的鑿痕造就了黃靈芝的日本語文學,也繽紛了台灣文學,更開拓了台灣文學的另一個面向,增添了台灣文學的多樣性。
我何其有幸,能得到恩師首肯著手翻譯著作,將黃靈芝文學廣傳於世間。因而在有限的預算中,若鶯教授和我仍執意爭取增幅為上下兩冊,雖然因趕譯不及憾留數篇小說及童話作品未能收錄,師若有靈當知我已盡力,感謝台北俳句會、黃靈芝文字研究者岡崎郁子、下岡友加的先進鑿路,因了黃靈芝文學的因緣,我們的人生除了與黃靈芝老師,也與彼此有了溫暖的交織;翻譯過程中,也曾多次作為課堂教材,與學生一起閱讀、討論,恕我無法一一致謝;匆促間想必疏漏不少尚祈指正。
阮文雅謹序於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