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成為孩子守護者的開端
四也文化出版公司總編輯 張素卿
那天,我的孩子五歲,穿著直排輪鞋和另外九個小小孩列隊站在廣場上,當教練的哨聲響起,全部的孩子一腳一腳往前緩慢滑動,只有我的孩子動也不動,任憑教練和我如何鼓勵,他堅持「不想跌倒」。一小時後大家都回家了,只有他和我還站在廣場上。我說:「除非你溜出去,否則不能回家。」他磨蹭了很久,帶著淚,慢慢溜了出去。「你要多練習,剛剛大家都溜很久,只有你沒有。」又過了許久,他哭著說:「媽媽,我好累!」我才意識到他已經十分疲憊,隱約中感覺自己好像做錯了什麼。
但「我是為他好啊!」、「希望他喜歡運動『跟其他孩子一樣』,勇敢的溜出去。」回到家,我依然理直氣壯。我姊姊微笑問我:「妳是真的希望他會溜冰?還是覺得面子掛不住?」這才驚覺打著「為孩子好」的漂亮大旗的背後,是我貪婪於「好家長」的名聲、比較孩子的虛榮,孩子因而被「物化」,甚至依附在大人的社交需求上。「親子關係」落入成人的優越與交易,交易結果不是「滿溢的幸福」,而是「聲勢與社會關係」,「孩子」這個「人」完全不見了。
於是,我開始練習把孩子當作一個獨立的公民個體,試著去了解他,才明白他是自我保護型的孩子,到任何地方都要先觀察,才決定下一步。我漸漸接納孩子他原有的樣貌,上團體班鋼琴課時,接受他坐在位子上觀察了兩堂課,直到第三堂課才參與律動。十幾年後,我的孩子獨自一人扛著行李去美國上大學,我知道他會保護自己,心裡十分安心。
這幾年,我因為兒童文學研究和出版工作關係,大量接觸各族群的大人和孩子,開始從事「兒童本位」和「兒童權利」相關的文化平權工作,深刻體會,願意「把一個在能力上還未臻成熟的人,當作有資格成為具『權利主體』的人」,並且不用優劣、能力或任何效度衡量,單純「重視每一個『存在個體』的意義和價值」,來與之相處,著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於是當知道了日本「兒童學」學界權威的本田和子教授著作《百年兒童敘事――從「二十世紀的兒童」到「兒童權利公約」》,針對這被稱為「兒童世紀」一百年的兒童生活的變遷、兒童∕成人關係的拉扯、以兒童為對象的商業戰爭,乃至於網路世界的住民人格等等精闢討論,提供了一個觀看並實踐「兒童∕成人」新關係的開端時,便決定出版並邀請兒童文學評論家林真美老師翻譯,期待未來能出版更多研究兒童的專業書籍,給尚在路上摸索的大人們一個嶄新的視野。
當我讀到書中這段文字時,異常感動,這一段話是這樣的:
「一九八九年頒布的《兒童權利公約》,將『兒童』界定為未滿十八歲的人,他們全體都是公約的適用對象,條約呼籲的,乃是原本就應該歸還給他們的各種權利。此公約承諾為了地球上所有的孩子,要禁止歧視、保證人人平等,以及以兒童的最佳利益做為考量。而最重要的是,條約認可了這是『所有的兒童』『與生俱來的權利』。不論種族為何、能力多寡、障礙之有無,他們同樣都是『自身權利』的擁有者,也是行使此權利的主體。」(原文/本田和子,翻譯/林真美)
雖然,這些被訴諸文字的權利,尚未被大部分人認真對待、付諸實行,但對我來說,卻是希望「成為孩子守護者」的開端。我想,如果我能早個幾十年,甚或在身為兒童時便知道自己有不被歧視、有著跟他人一樣與生俱來的平等權利,肯定會相信「自己存在的本身就是有意義的」,而珍惜自己、看重生命。當遇到挫折失敗,或他人有所比較、建議評論時,將不會先全面否定自己,而是好好思考,把自己的感受說出來討論,人生一定會有不同的風景。
因為,一個「人」存在的本身就是有意義的,就像陽光,就像愛,不需任何條件,受難中的孩子、平凡的一般孩子,同樣享有陽光,享有愛與被愛的權利。
譯序
有光的距離——我與本田和子老師
兒童文學評論家 林真美
1985年,我正式進入本田和子老師的門下,成為日本國立御茶之水女子大學兒童學科‧兒童文化研究室的一名研究生。
現在回想,那算是我人生中第二次的「牙牙學語」階段。一開始,我用著破碎的日語,艱難的在老師、同儕的面前拼湊出自己初探「兒童學」的想法,也在「兒童學」這浩瀚的學中,在自己所能企及的範圍內,試圖抓取各個不同領域的教授的思想精華。
也不確定自己學了多少?總之,我像個赤子般,因為無法細細密密都知曉,便也對接觸到的新世界滿懷好奇,除了咿咿呀呀學語,也張開了所有的觸鬚,召喚出要與之直球對決的決心。那時,坐在課堂上的我,有如面對一個混沌初開的世界。我聚精會神東張西望,有時是整體把握,聽出了一些端倪;有時則是鴨子聽雷,頂多,就只能在瞬間隨機接住幾個天外飛來的「關鍵字」。而我好像是被那些接連不斷的「關鍵字」打到後,才漸次開竅的。走出校區,攤開書本,這才開始隱約發現,自己正帶著新的視角,以「兒童」為切入方向,試圖展開我的「第二人生」。
對我而言,「兒童學」無疑是門非常有趣的學問。從比較動物學、兒童發展、兒童心理、兒童文化、兒童社會到兒童福祉……等等,舉凡與兒童相關的,幾乎可以無所不包。換句話說,那是從科學的、生理的、心理的、文學的、文化的、社會的……等各個切面,去理解「兒童」這位「他者」。由於選取的角度豐富,不僅活絡了關於「兒童」的各種論點,也讓我們最終得以追本溯源,看懂了有血有肉的兒童園地,甚至,還獲得了觀看「人與世界」的一種新視力。
在我的「第二人生」中,本田和子老師是我最重要的啟蒙者。
門下三年,由於對她又敬又畏又愛,使得我們的師生關係,始終維持在一個帶著冷峻、又彼此默默關懷的「臨界」距離上。當然,這也和老師的個性有關。在情感上,她稱不上是個熱絡的人,但她彷若洞悉所有,知悉每一位學子的特點,通常,她就只用提點的方式,讓我們自己去找尋研究的路徑。基本上,她從不干擾,只是默默的等待我們各自行走的速度,以及我們在踽踽獨行中所累積出來的成果與發現。記得,我曾因為書寫論文的苦悶,在如火如荼期間,深度懷疑起學位的價值與意義。本田和子老師看出來了,在讀完我那一階段所寫成的論文報告後,除了要我繼續努力,就是用淡定的語氣說道:「就把它當成是妳的一段『成長儀式吧!」
我用這樣的心情,完成了我的論文〈『虎姑婆』考〉。畢業典禮那天,我以到箱根獨旅,默默慶祝我通過了一段極具考驗的試煉。對於我在重要時刻的缺席,本田老師未置一語,因為一直以來,她多多少少懂得我的孤僻個性。就這樣,師生一場,除了學問上的討論,我們之間的對話其實不多。不過,在回國前夕,她為我寫了重磅推薦信,雖然之後未能派上用場,但我認為那是老師送給我的最好的禮物。
返台之後,我一直在「體制外」遊走、工作。我當過日僑幼兒園的教師,也與台灣最早的「發展遲緩兒早期療育團隊」工作了一段時日。1990年我開始到清華大學開設「兒童文學」的課程,也因而在我的職涯中開出了一條教書的軸線。因此機緣,我又陸續在輔仁大學、中央大學、文山社區大學、永和社區大學、新莊社區大學……等地開課,課程以「兒童文學」、「兒童文化」為主。1992年我試著把在留日期間所親自參與的「家庭文庫」移植到台灣,在屢仆屢起的過程中,終於摸索出符合台灣風土的「小大讀書會」。為了推動「小大」,1996年我開始涉足出版,首先是引介國外的經典繪本,後來是慢慢爬梳與繪本有關的理論和作家資料,並分別在2011年和2019年完成了兩本我對繪本的論述。很自然的,我把我的第一本著作《繪本之眼》獻給了本田和子老師。因為,在我心中,她是督促我勇往直前的最大推力,而我的「兒童觀點」以及做學問的態度,也都深受老師的影響。雖然,從頭到尾我都是一名拙於表達的學生,但至少,我鄭重的、無言的,向老師致上了我的最大謝意。
做為日本「兒童學」學界的第一把交椅,本田和子老師的著作不僅生動刻畫出「兒童」此一不變的主題,也經常穿梭在歷史間,來回探問兒童在社會與文化中所閃過的光和影。我回國後,繼續藉由閱讀相關文獻與老師爾後的著作,樂此不疲的探究著這個多變、深不可測的領域。當然,不同於老師在學術殿堂所持續深掘與廣拓的成就,我所能做的,就是把在其字裡行間所悟得的思想,帶到現實的世界,在與兒童的互動中,不斷的檢視自己,在凝視與兒童相關的事務時,對於兒童的多義性以及整體結構的複雜性,也會審慎思慮。對我而言,談論兒童,既不能簡化,也非形而上的闡述。我在每個時刻對兒童的看待,都深受周遭各種條件的牽動。畢竟,兒童除了是自身生命的主體外,也是社會建構下的產物。兒童所處的時空、經濟條件、文化背景······,以及多數成人所抱持的「兒童觀」和他們自覺或不自覺的對待,都攸關兒童最後會長出來的樣子,甚至,也因而形塑出在類似條件下成長的兒童的整體特徵。所以,又有誰能夠對他們「蓋棺論定」,說兒童只能這樣,不能那樣?說兒童是什麼,不是什麼呢?
由於不輕易對兒童下結論,所以我對歷史中盤根錯節的兒童命運,便一直充滿了好奇。如今想想,這樣的探究之心,主要仍是來自於本田和子老師的「無聲教誨」。留日期間,我們在研究室與老師一起共讀了阿利耶斯的《〈兒童〉的誕生》,也探究了日本江戶時代的育兒觀點,另外,在論及兒童文學的發展時,我們也談到從「童心主義」到「無產階級主義」到「資本主義」下的「兒童不在」現象。即便當時還有許多的一知半解,但本田老師所投下的那些問題意識,卻深深影響著我返台至今未曾中斷過的「兒童」探究之旅。
尤其,在2000年拜讀本田和子老師的當年大作《百年兒童敘事》時,於我,更是有著醍醐灌頂的感受。那是針對二十世紀兒童的一場重要回顧,是踩踏整個西洋、東洋歷史後,對百年兒童所刻畫出的縝密解剖圖。另外,思古鑑今,即使這本書的中文版遲了20年才在台灣問世,它也依然值得我們跟隨作者的腳步,帶著「複眼」般的視力,去思索在歷史中,做為人類社會一員的「兒童」,是如何留下屬於他們的坎坷足跡?還有,我們要如何藉由穿透內外,好讓兒童與成人那剪不斷理還亂的宿命糾纏,可以從現下慢慢得到解脫?甚至,可以因為成人對兒童的理解與尊重,而掀起一場屬於地球規模的大變動,讓兒童做為一個人的權利與價值,不僅得到彰顯也能被真正看重。
本田和子老師這一切有關兒童的論述,其實都埋藏著她做為一名「兒童研究者」的終極願望。那就是透過百年來的沈澱,去對兒童生活的變遷,以及「兒童∕成人關係」的拉扯,做出整體的觀察與批判,好讓讀者看清這錯綜複雜、緊密相連的脈絡,最後再透過進一步的反思,去重新檢視、建構自己的「兒童觀」。而當我們都願意從兒童的視角出發,去瞭望他們的未來時,那每一個降生於世的孩子,也才有機會走出千年百年的魔咒,不再受到來自成人世界的任何一丁點的傷害······。雖說,這樣的人間淨土彷若癡人說夢,但做為一個一生都在探究「兒童」此一主題的學者來說,面對越來越難加以忖度的未來,本田老師所念茲在茲的,無非就是我們的孩子要如何長大?要如何被成人世界好好的對待?
我之所以會「斗膽」接下《百年兒童敘事》一書的翻譯工作,除了回饋師恩,就是想讓台灣的讀者也能有幸一睹本田和子老師既犀利又全方位的兒童觀與世界觀,另外,也希望這本書能在台灣這塊土地落地生根,一點一點的改變我們看待兒童的角度。只是,我完全沒有料到,翻譯的過程有如攀爬一座險峻的大山,其艱難的程度,遠遠超出了我的想像。本田老師的旁徵博引,固然讓我疲於奔命;但最困難處,其實是在於如何將她那潛藏在優美日文背後的迂迴深意,轉化成既不偏離其文采特質,又兼具其厚實原意的中文。蹣跚的腳步,曾讓人耗盡力氣又戰戰兢兢,不過,也因為在書頁間那數也數不盡的曲折徘徊,而讓我有了與老師數度「神交」的機會。這不免讓人暗暗感激,雖然歷經焚膏繼晷的苦戰,卻也帶給了我無數撥雲見日的盈滿時刻。
就在譯稿完成時,我的眼前浮現出一個永誌心中的畫面。那是2013年的夏天,在日本的輕井澤。
很意外的,從御茶之水女子大學校長職位退休的本田和子老師,在我訪日期間,邀請我到她的山中小木屋做客。這是我畢業二十餘載後,與老師的第二次闊別,也是我們師生不曾有過的近距離接觸。「居家」的本田老師,看起來非常平易近人,其熱絡的招呼更讓早年的那個「冷冷的距離」忽焉消失。在兩天一夜的短暫時光中,我們好似成了一對不知彼此年紀的忘年師生,很愉悅很放鬆的,就像玩丟接球那樣,川流無礙的聊了許多。
傍晚時分,我帶著驅熊的鈴鐺,到林間散步。本田老師則留在家中,為我準備晚餐。我循著附近一條潺潺的溪流往上行走。一邊大口大口的吸著清新的綠色空氣,一邊搖著手上的鈴鐺,跟著那悅耳的節奏,飽覽錯落在山裡一間又一間的漂亮建築。不知不覺間,我錯離了小溪,一等要折返時,我發現我迷路了。
天色漸黑,經過幾番折騰,我終於又找到了那條小溪。此時,驅熊的鈴鐺聲,不再顯現慌亂,我隨著篤定的節奏,快步往下走去。而遠遠的,就在要拐進老師家的路口處,我看到一個手上搖晃著手電筒的身影,站在那裡等我。
我由遠而近,細細領受著那有光的、溫暖的距離。而隨著鈴鐺聲漸進,我也看到了本田和子老師對著我笑開了的慈愛容顏……
林真美 寫於2020.10.16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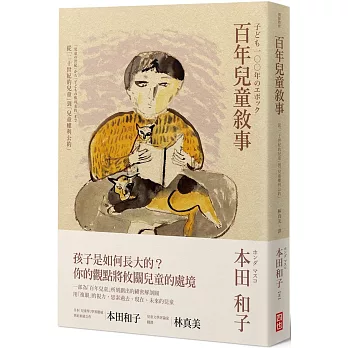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