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獲獎理由
二○二○年十一月一日,週日,寒風蕭瑟,樹葉即將落盡。我寫完這一天要寫的段落來到後園將這一年最後的鮮花剪下來插瓶,大捧的桔梗便用輕柔的淡紫色、冰藍色妝點了前廳。然後,走出前門,用小掃把清掃簷下懸吊著的暗綠色的「小燈籠」,帝王蝶的蛹。
鄰家的五歲小女孩瑪芮帶著小狗貝貝正站在人行道旁我家郵箱下那一叢普羅旺斯薰衣草前。她喜歡用手輕撫這香草,不但放到鼻子下面聞個不停,還伸手讓貝貝聞香,狗兒搖搖尾巴,並不領情。
瑪芮常來,曾經親眼看著帝王蝶在花叢中飛舞,在乳草馬利筋上產卵;卵變成幼蟲,拚命加餐,將乳草青翠的葉子吃得乾乾淨淨;然後,這些毛毛蟲就沿著植株、牆壁爬上我家門廊,僅憑著一根細絲懸吊在簷下。瑪芮常常驚恐地指給我看,說是蟲兒要掉下來了,怎麼幫牠們一把才好。我總是安慰她,帝王蝶絕頂聰明,牠們能夠克服任何艱難險阻。果真,成排的小燈籠順利地懸掛起來了。兩週之後,從那小燈籠裡面成功脫身出來的帝王蝶只有一位。我和瑪芮親眼看著牠從比牠小得多的蛹裡掙扎出來,舒展一下身體,然後就振翅飛走了,飛向三千英里之外的墨西哥。瑪芮淚眼模糊地問我:「牠什麼時候回來?」我跟她說,只要我門前的乳草健康茁壯,帝王蝶就會回來,只不過,不是現在飛走的這一位,而是牠的孫兒們。瑪芮的眼淚流下來了,她跟我說:「帝王蝶是世界上最漂亮、最勇敢的物種。」何止如此,大自然以怎樣柔韌、堅定的力量造就了這麼偉大的物種。
這一天,瑪芮親眼看著我把那些已經乾癟的小燈籠收拾乾淨,沒有掉淚,只是很嚴肅地跟我點頭問好,帶著貝貝回家去了。我知道,帝王蝶的壯麗行程感動了這女孩,她在這幾個月裡長大了。
回到房裡,電話鈴響,老友的聲音:「下午一點鐘,你方便嗎?要送個東西給你。」非常時期,友人送東西不是放在門外就是塞在郵箱裡,哪裡還需要打電話約時間?除非是善本書。老友不但是政治家、經濟學家也是藏書家,難不成機緣湊巧遇到了珍本書要跟我分享?於是喜孜孜答應了老友,回書房查核資料,準備第二天的寫作,完全忘記了老友在白宮任職這回事。
準時,門鈴響,手裡提著白宮的大紙袋,眼睛裡滿是疲憊的老友到。原來,疫情煎逼、選情緊張,日理萬機的白宮主人卻還掛念著默默耕耘的文化人,要頒個獎給我。週日,老友為了這件事竟然親自開車來。似乎讀懂了我的心思,未等我開口,老友已經摘下口罩:「你哪裡有什麼週日?還不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上班』。」這倒是實話。
沒有隔著六英尺遠的距離,老友從紙袋裡取出已經裝裱好的大獎狀送到我手裡,打開手機讓我看到總統為獎項簽名的照片,把一枚沉甸甸的金質獎章掛到我胸前,拍照存檔。最後是一頂白宮的棒球帽,充分展現白宮主人的幽默感。我從來沒有過這麼一頂舒適、漂亮的帽子,忍不住笑了起來。老友也笑了。
正事辦完,我問:「我可不可以請你喝杯茶?」老友搓搓手:「太好了。」半年多來,這可是第一次,有人走進家門,不僅摘掉了口罩而且樂意坐下來喝杯茶。
捧著熱騰騰、香噴噴的天仁蔘茶,我們坐在書房外的陽光屋,遠離了殘酷的政治,遠離了艱難的經濟,我們談文學、談文藝復興,從義大利談到西班牙談到克里特談到德意志。看著方桌上有關杜勒的一大堆書,老友問:「下一個不眠不休的旅程?」我脫口而出:「不計生死,就像帝王蝶。」老友點點頭:「國家與社會對你這樣的人表達禮敬是應當的。」告別時,精神已經大好,疲憊已經一掃而空,老友又說:「文藝復興當然非常重要,也絕對值得你全力以赴;不過,你有多久沒有出版散文集了?你的散文很好看的,海闊天空驚喜連連,就像跳躍著的光焰。人需要光焰照亮內心,順便照亮腳下的路。」可不是,我的出版雖然從未間斷,卻真的有足足十二年沒有出版散文集了,那種飄逸不定自說自話的肺腑之言,我心裡想。老友點點頭說:「我等著看。」
幾天以後,地方報紙記者來電:「恭喜獲得總統獎,請問獲獎理由是?」
獲獎需要理由嗎?我一時怔住。對方說:「寫一條消息,獲獎理由是需要的。」
我同老友的相知相惜自然是不方便暴露的,於是只好顧左右而言他,不了了之。
夜深人靜,捫心自問,支撐著自己耕耘文字三十八年的動力究竟來自何處?說到底,是對世間美好的無比珍惜。神說,要有光。我心底裡的光焰便是對人性至美的無懈追求。我相信,口罩、六英尺間隔、鎖國、封城都不是最終戰勝邪魔的利器。歐洲文藝復興的輝煌粉碎了瘟疫、戰爭帶來的漫長暗夜,給我們留下了豐沛的文化遺產。我們能不能像帝王蝶那樣不畏任何艱難困苦,將吉光片羽留在世上呢?念及此,豪氣頓生。
將五十幾篇文字挪到電郵窗口,按傳送鍵。我知道,臺北無所不能的編者定能將其化作一本美麗之書。這本書大概也就可以成為「獲獎理由」的最佳詮釋。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寫於美國北維州維也納小鎮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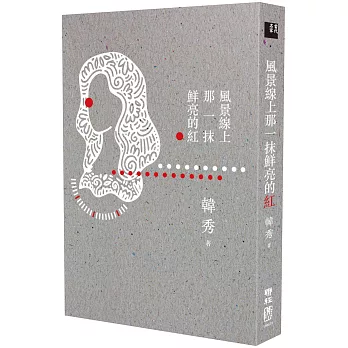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