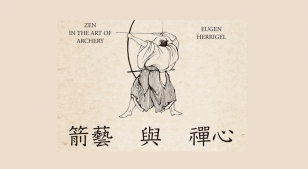序
鈴木大拙
在箭術中,事實上在所有屬於日本及遠東國家的藝術中,最顯著的一個特徵是,那些藝術並不具有實用或純粹欣賞娛樂的目的,而是用來鍛鍊心智;誠然,使心智能接觸到最終極的真實。因此,射箭不僅是為了要射中目標;劍手揮舞長劍不僅是要打倒對手;舞者跳舞不僅是要表現身體的某種韻律。心智首先必須熟悉無念。
如果一個人真心希望成為某項藝術的大師,技術性的知識是不夠的。他必須要使技巧昇華,使那項藝術成為無藝之藝,發自於無念之中。
在箭術中,射手與目標不再是兩個相對的事物,而是一個整體。射手不再意識到自己是一個想要擊中對面箭靶的人。只有當一個人完全虛空,擺脫了自我,才能達到如此的無念境界,他與技巧的完美成為一體;然而其中蘊藏著十分奧妙的事物,無法藉由任何按部就班的技藝學習方式來達到。
禪與其他所有宗教、哲學、神祕法門的教誨最大的不同是,禪從未脫離我們日常生活的範疇,儘管它的作法實際且明確,卻具有某種東西使它超然獨立於世界的混亂與不安之外。
在此我們接觸到了禪與射箭之間的關係,以及其他的藝術,諸如劍道、花道、茶道、舞蹈,還有繪畫等等。
禪是平常心,如馬祖禪師(卒於西元七八八年)所說;平常心就是「餓了就吃,睏了就睡」。一旦我們開始反省,沉思,將事物觀念化後,最原始的無念便喪失了,思想開始介入。我們吃東西時不再真正吃東西,睡眠時也不再真正睡眠。箭已離弦,但不再直飛向目標,目標也已不在原地。誤導的算計開始出現。整個射箭的方向都發生錯誤。射手的困惑心智在一切活動上都背離了自身。
人類是會思考的生物,但是人類的偉大成就都是在沒有算計與思考的情況下產生的。經過了長年的自我遺忘訓練,人類能夠達到一種童稚的純真狀態。在這種狀態中,人類不思考地進行思考。他的思考就像是天空落下的雨水,海洋上的波濤,夜空閃爍的星辰,在春風中飄舞的綠葉。的確,他就是雨水、海洋、星辰,與綠葉。
當一個人到達了如此的精神境界時,他就是一個在生活藝術中的禪師。他不像個畫家般需要畫布、畫筆和顏料;他也不像個射手般需要弓箭、箭靶和其他用具。他擁有他的四肢、身體、頭和其他部分部分。他的禪是透過所有這些「工具」來表現自己。他的手腳便是畫筆,整個宇宙便是畫布,他在上面描繪他的生命七十、八十,甚至九十年。這幅畫叫做歷史。
五祖山的法演禪師(卒於西元一一○四年)說:「此人以虛空做紙,海水為墨,須彌山做筆,大書此五字:祖-師-西-來-意。對此,我鋪起我的坐具,深深頂禮敬拜。」
有人會問:「這段奇怪的文字是什麼意思?為什麼有如此表現的人值得最高的敬意?」一個禪師也許會回答:「我餓了就吃,睏了就睡。」如果他喜愛大自然,他也許會說:「昨日天晴,今日下雨。」然而,對讀者而言,問題仍然存在:「射手在什麼地方呢?」
在這本奇妙的小書中,海瑞格先生,一位德國的哲學家來到日本,藉著學習射箭來體驗禪,生動地報告了自己的經驗。透過他的表達,西方的讀者將能夠找到一個較熟悉的方式,來面對一個陌生而時常無法接近的東方經驗。
美國麻瑟諸塞州伊普斯衛鎮
一九五三年五月
前言
1936年《日本》(Nippon)雜誌發表了我在柏林日德協會關於「箭藝」的演講。我對這次演講極為慎重,因為我想要說明「箭藝」與「禪」之間的密切關聯。由於這種關聯是難以描述與真正界定的,我很清楚我的嘗試只是權宜之舉。
然而我的演說還是引起了極大的興趣。講稿在1937年被翻譯為日文,1938年翻譯為荷蘭文,1939年我得知也計畫翻譯成印度文,但尚未證實。1940年刊出經過大幅修訂的日文翻譯,還加上了小町谷教授的見證陳述。
庫特‧威勒(Curt Weller)先生曾經出版鈴木大拙重要的禪修著作《大解脫》(The Great Liberation),仔細計畫要出版一系列的佛教書籍,詢問我是否同意重印我的演說,我很愉快地同意了。但由於過去十年我都持續練習箭藝,我相信我在靈性上有了更多的進展,對於這項「神祕」的藝術有更好的瞭悟,我決定把我的經驗用新的形式來陳述。在箭藝課程中無法忘懷的回憶與筆記是很大的幫助。所以我可以很確實地說,本書中沒有一句話是老師沒有說過的,沒有任何意象或比喻是老師沒有用過的。
我也試著讓我的語言盡量保持單純。不僅因為禪的教導強調最精簡的表達,也因為我發現若無法單純表達或必須使用神祕話語,就會變得不夠清楚與具體,連我自己都無法接受。
寫一本關於禪的本質的書,是我未來的計畫之一。
譯後記
魯宓
市面上關於禪的著作不算少數,但是談到禪總是會提到「不立文字」。這可能是有心學禪的人會遇到的第一個疑問。如果不立文字,我們看這些書能得到什麼?禪到底是什麼?
在最早的時候,禪這個字是一句印度話的音譯,意思只是靜心去慮。但是後來禪傳到了中國,已經不僅是打坐靜心了。在禪宗的種種公案與傳奇故事中,禪似乎是對於生命中的困境,有一種超越對錯二元的態度。禪師們似乎在面臨無可解的矛盾時,卻能夠從中迸出一種全新的東西,稱之為作法或觀點或解答都有點勉強,於是被稱之為悟。禪宗故事最讓人心動的,往往就是「頓悟」。
因為有了頓悟,禪宗彷彿成為了一條求道的捷徑。彷彿只要悟了一則公案,就立刻到達修行的最高境界,從此自在解脫。難怪追求速成的現代人對於禪都心生嚮往。
問題是,從禪宗公案或傳奇故事中通常只看到悟的那一剎那,而看不到在所謂開悟之前,或開悟之後的種種過程,因此給人一種修真捷徑的印象。也許這就是禪宗不立文字的用意:文字描述不了開悟,也難以傳達禪修的種種過程,反而容易被簡化或扭曲,造成誤解。
正因為如此,這本《箭藝與禪心》才尤其難能可貴。德國哲學教授奧根‧海瑞格,為了追求在哲學中無法得到的生命意義,遠渡重洋來到東方的日本學禪,處處碰壁之後,透過了箭術(在日本稱為「弓道」),他體驗了禪的真義。這雖然是他個人的追尋,卻具有重要的文化意義:一個具有西方理思想精髓的學者,客觀的態度,親自深入探究東方的直觀智慧,並能以平實的文字加以報導分析,沒有誇大渲染。這種來自於異國文化觀點的第一手心得報告,沒有經過時間或口耳相傳的扭曲,也不用背負任何傳統的包袱,往往比種種故事傳說或甚至經文公案更真實,更具參考價值。
海瑞格教授說他身為歐洲人,有困難直接學禪,所以不得不藉助一項外在的運動。其實他這樣做很符合禪的精神,一舉跳過了宗教傳統的種種包裝,以行動來直接切入禪:禪是活生生的體驗,不存在於任何言語文字之中。
體驗什麼呢?在此冒著誤導讀者的危險(請自行斟酌),簡單說,就是當下的真心。我們這些凡夫俗子之所以無法解脫煩惱,拋開業障或輪迴等等說法不談,純粹以意識的觀點來看,就是我們的意識幾乎永遠被困在自我的投射之中,如果不是對於未來的憧憬或擔憂,就是對於過去的緬懷或悔恨,而無法真正忘我地活在當下。「當下真心」的狀態,如果勉強地加以描述,可以說是不帶絲毫貪求,也不帶任何憎惡的平衡心境,對一切事物都平等無分別地全然接納。如果要引伸到日常生活中,說起來很簡單,譬如「餓了就吃,睏了就睡」,可是對於我們這些頑冥不靈的凡夫俗子而言,實在很難參透其中的真義。但是在《箭藝與禪心》中,透過了箭術的學習,讓我們對於當下的真心有更實際、更清楚的概念。我們看到一個初學者因為缺乏了當下的真心,於是學習射箭的每一個階段都是一個困境,彷彿是一則則似乎無解的公案。海瑞格教授很清楚地描述了這段過程:
首先是拉弓的困境:拉弓時如果用力會發抖,但是那些弓又非常強硬,不用力怎麼拉得開?然後是放箭的困境:放箭不能出於自己的意識,有意識的放箭都會造成箭的顫動,但是無意識又怎麼放箭?最後是擊中箭靶的困境:老師一再告誡射箭時不要有射中目標的欲望,不要瞄準,那麼要如何射中箭靶?每一個困境在知上似乎都沒有合理的解答,學生沒有其他的辦法,只有信任老師的引導,全心全意的繼續努力,逐漸放下更多的自我投射,變得無所求與無我,於是就在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情況下,突然就水到渠成,體驗到了箭術中的禪心,以最自然而無痕跡的方式完成了困難的動作。事後看來,每一個困境的解決其實都是一次「當下真心」的顯現,都是一個悟。
不管是透過箭術,或禪定,或參話頭公案,如果悟是當下真心的乍現,在開悟之前,禪師必須先完成漫長艱辛的準備工夫,才能夠逐漸消解自我的投射,在意識中清理出空間讓當下真心能夠出現。有了開悟體驗的禪師,也只不過是對生命的實相電光火石的一瞥而已。在開悟之後也還有更多的進境,更多的挑戰必須克服。他仍然需要持續的努力,使當下真心的出現越來越平常,或許終於有一天,他的意識能夠徹底擺脫所有瞻前顧後的妄想與根深蒂固的習性,永遠留住當下的真心,從此不再有悟與不悟的分別;姑且不論這是否就是最終的證道,單就人生的痛苦與煩惱而言,這種狀態應該算是自在解脫而無可置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