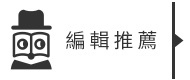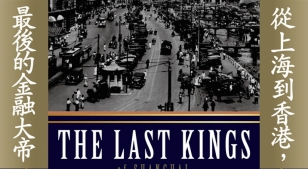前言(節錄)
幾十年來,中國共產黨的統治者一直掩蓋著沙遜和嘉道理兩家族的故事。這兩個彼此競爭的外國家族在十九世紀來到中國,並且建立了各自的王朝。從一八四二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到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掌權這段期間,政府用大量的政治宣傳,粉刷了由兩家族所塑造的這個世紀。他們抹去歷史,然後動用國家神話和故事爭取人民的支持,就像全世界的政客一樣。中國各地的小學教室裡都有一張海報,上面寫著「勿忘國恥」──永遠不要忘記國家的恥辱。共產黨領導層希望學童記住,像嘉道理和沙遜家族這樣的外國人,生活是如何奢華,如何剝削中國工人階級,又是如何把中國公民囚禁在骯髒、無知和鴉片煙霧之中;直到毛澤東和他忠誠的共產黨游擊隊推翻這些貪婪的資本家,中國才得以重新站起來。隨著中國實力增長,與美國的競爭加劇,理解中國自己說出來的故事是很重要的。這些故事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中國運作的動力是什麼;挖掘它們背後的真相,也可以提供我們和中國打交道,以及中國和世界打交道的不同方式。
中國共產黨版本的歷史中,有很多是事實,但還有其他事實存在。上海是中國的大熔爐,所有形塑中國的力量──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帝國主義、外國人和民族主義──都匯聚在這裡。一八九五年,上海已經有了可以和倫敦匹敵的現代有軌電車系統及煤氣廠。到一九三○年代,在大班維克多.沙遜的領導之下,這座城市的摩天大樓和天際線已經和芝加哥不相上下了。那時的上海,是世界第四大城市。當世界其他地區陷入大蕭條時,蔣介石政府與沙遜家族合作,穩定貨幣,並創造出口榮景。上海成了中國的紐約,是金融、商業和工業中心;它也成了中國的洛杉磯,是流行文化之都。上海的出版社出版了一萬多份報紙、雜誌,上海的電影製片廠製作了數百部電影,當中許多都是以這座西化城市為背景。大學蓬勃發展,政治亦然。上海的國際租界在管理上,就像個商業共和國。一個由商人組成的七人委員會,包括沙遜家族的代表,共同管理這座獨立於中國法律之外的城市。矛盾的是,這形成了一種相對自由的政治氛圍,得以保護中國的運動人士;改革者和激進分子免於受到國民政府對言論自由、共產主義和抗議活動的限制。後來毛澤東成為共產黨領導人,黨內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是在上海召開,地點離沙遜與嘉道理家族的商業總部和宅邸只有幾公里。
沙遜家族和嘉道理家族共同協力,打造出一座讓他們成為億萬富翁的城市,也激勵了一整個世代的中國商人,讓他們成為成功的資本家、企業家。在他們的協助之下,上海創造出一種蓬勃發展的企業文化,而這種文化在一九四九年被共產黨消滅了。維克多.沙遜使上海和香港成為「壯遊」(Grand Tour)的一站,向全世界的上流人士打開中國的大門。他在華懋飯店宴會舞廳舉辦的假面舞會吸引了諾維.考沃、查理.卓別林和美國社交名媛華里絲.辛普森,據說幾年之後,她用以引誘英國國王放棄王位的性技巧,就是在上海學到的。
在「咆哮的二○年代」(Roaring Twenties)和一九三○年代,中國中產階級與富裕階層集體湧入上海,他們深受這裡的經濟機遇以及中國其他地方沒有的生活所吸引:迷人的百貨公司、飯店、夜總會和賭場。在比英、美、法及其他國家提前經歷了幾十年的停滯和倒退之後,許多中國人相信,上海正在打造一種全新的、充滿活力的中國文化──開放的、國際化、準備迎接二十世紀的文化。沙遜和嘉道理家族幫中國打開了世界的大門,也幫世界打開了中國的大門。
當日本入侵中國,並加入德國陣營成為軸心國時,沙遜和嘉道理家族聯合起來,創造了二戰的一項奇蹟。一萬八千名歐洲猶太人為了逃離納粹,從柏林和維也納出發,經歷八千公里的旅程湧入上海,當納粹代表要求日本占領者將猶太難民裝上駁船,並沉到黃浦江心的同時,維克多.沙遜卻和日本人達成了祕密協商。沙遜和嘉道理家族一起達成了歐洲、巴勒斯坦,甚至美國猶太人都做不到的事情:他們保護了每一個來到他們這座城市的猶太難民,其中還有數千名兒童──包括後來成為美國財政部長的麥可.布魯門塔爾(Michael Blumenthal)、藝術家彼得.馬克斯(Peter Max)、好萊塢高階主管麥可.梅道佛(Michael Medavoy),以及哈佛法學院教授勞倫斯.特萊布(Laurence Tribe)。
當共產黨占領上海,奪取了嘉道理和沙遜家族的飯店、豪宅和工廠之後,嘉道理家族撤退到中國南端的英國殖民地香港,沙遜家族則逃往倫敦、巴哈馬群島,甚至德州的達拉斯。但他們對上海的思念從未停止。
這本書裡的世界,就像我們今天的世界一樣,是由創新、全球化,以及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和政治動盪所定義的。早在馬克.祖克伯(Mark Zuckerberg)、史蒂夫.賈伯斯(Steve Jobs)、微軟和谷歌努力應對中美雙方政治壓力的很久以前,沙遜和嘉道理家族在上海、香港、孟買和倫敦的辦事處就已經掌握了全球經濟,並且在與中國合作的道德和政治困境中掙扎過了。沙遜和嘉道理家族都讓我們看見,企業(尤其是開明的企業)能做出多麼偉大的事。他們去了政府不願意去,或不能去的地方。他們的決定改變了億萬人民的生活。一九三○年代,當世界各地陷入大蕭條,沙遜家族協助穩定了中國的經濟。他們在全球資本主義中培養出一整個世代的中國人,為中國今天驚人的成功鋪好了道路。嘉道理家族為上百萬香港人帶來電力,改變了那些生活節奏幾百年來都沒有改變過的地區。一九四九年後,身在香港的嘉道理家族決定與逃離共產主義的上海工廠老闆合作,這個決定打開了全球市場,並刺激香港的發展,也為二十一世紀的出口繁榮奠定基礎,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
然而,儘管沙遜和嘉道理家族在政治和經濟方面都很精明,卻錯過了正在他們辦公室和豪華客廳外醞釀的共產主義革命。令他們錯愕的是,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勝利,沙遜和嘉道理家族失去一切。然而,他們遺留的影響,至今仍在中國、美國及世界其他國家的關係中揮之不去。不管是參觀博物館、遊覽中國、舉行商務會議或外交談判,都必須提及中國受到外國剝削和帝國主義的歷史、所遭受的屈辱,以及絕不讓這些事情重演的決心。從對鴉片貿易的憤怒,到上海外灘引人注目的天際線,再到香港未來的緊張局勢,今天中國所做的每個決定,幾乎都籠罩在這兩家族的歷史和遺緒裡。
讀者可能會注意到,雖然中國是這個敘事的中心,其扮演的角色卻往往處於邊緣,這反映了這兩家族所居住的那個特殊殖民世界。即使是生活在上海那段時間,由於語言、財富和殖民地的刻板陳規,他們和中國人的關係也很疏遠。證據顯示,他們在中國生活的近兩百年時間裡,從來沒有一名中國人能打進兩家族的核心圈子,也不曾有過一名沙遜和嘉道理家族的人費心學過中文。同時,他們與大多數中國人的距離,使中國,特別是共產黨領導人和歷史學家,很輕易就對兩家族草率對待或加以諷刺,並且極力弱化他們的作用和影響力。這本書的其中一個目標就是納入這種複雜性,幫助我們理解嘉道理和沙遜家族所做的種種選擇。他們有許多行動是與時俱進,或者先於時代腳步的,即使當時的理由是利益驅使或家長式領導(paternalism);但在其他例子當中,他們卻接受了當時的殖民地作風,對後果視而不見。他們本身的猶太背景,使他們在不同世界穿梭這件事,變得更加複雜。接下來的故事,並不是一八四○年後的中國故事,而是還原中國歷史的一塊拼圖。
當中國將學生、企業和遊客送往海外,進入許多人認為的「中國世紀」時,中國領導人迴避了歷史的複雜性。他們喜歡把中國描繪成歷史上的受害者,即便中國正在崛起。如果中國依然貧窮、弱小、與世隔絕,那麼上海、沙遜和嘉道理家族的故事可能會成為一件奇事、一段可能發生的另一種歷史。但中國今天面對的問題──和外國人合作;不平等和腐敗;在這世界找到一席之地;在民族主義和開放、民主與政治控制、多樣性與變革之間取得平衡──都是當時塑造上海會面對的問題,也是嘉道理和沙遜家族每天都要面對的問題。和兩家族一樣,上海的成長、發展,以及這座城市的鬥爭與矛盾,也是本書的重點之一。
能有「第二次機會」的國家很少。中國在二十和二十一世紀的故事,是一個大國在內部腐敗、在西方殖民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推動下走向衰落,然後奮力重新崛起的故事。如果中國成功了,不僅僅是因為它仿效了北京精神,這個中國政治權力中心擁有一群擁護專制、鎮壓異見的領導階層;也是因為它仿效了上海,一座優雅、勤奮、老練、開放、國際化的城市,還有一群曾經幫助中國進入現代社會,如今已經被人遺忘的王孫巨賈。六十多年來,上海和中國一直把這段歷史藏在壁櫥和碗櫃裡,藏在老辦公室保險箱的發黃文件裡,也藏在拉上了百葉窗、坐在廚房桌邊喝茶時低聲講述的故事裡。
二○一四年,一家中國飯店公司聘請了費爾蒙飯店集團(Fairmont)來修復維克多.沙遜那家曾經優雅俯瞰著外灘的華懋飯店。在這之後不久,我回到那裡,被領著走上一段窄窄的樓梯,離開大廳,來到一個擺滿玻璃櫃和展示架的小房間。買下這家飯店不久後,新業主在當地中文報紙刊登了一則小廣告,尋找這家飯店一九三○年代輝煌時期的古董和文物。他們以為大概會找到幾份舊菜單,或是紀念菸灰缸。結果,好幾百位上海人響應。他們帶來的浮雕餐盤、水晶玻璃杯和雅致的印刷菜單淹沒了飯店。在他們送來的照片裡,有穿著及地合身旗袍的中國女人,有穿著西裝的中國男人,他們在飯店宴會廳慶祝婚禮和生日;背景的維克多.沙遜爵士戴著單片眼鏡,拿著手杖,十足的英國貴族派頭。五十年的共產主義歲月,讓中國經歷了革命、飢荒和文革。然而,就像我在小吃攤遇到的那名每晚睡在西式大床的女人一樣,幾百個中國家庭把這些過往碎片保存在遍布全上海的公寓壁櫥裡──像是一段回憶,一個曾經承諾會有個不一樣中國的上海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