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長青咀華,詩人有選
詩人有選,一如家有喜事,蓋若非詩作有足夠累積,同時詩作有其質地,否則難以成選。讀長青詩選,想其如何擇選自身詩作,勢必也重溫了那寫詩時,那些經歷的、反省的時時刻刻。
而我也不免回想起與長青的朋友之誼。我在2009年左右至台中南區中興大學任教,那時還住學校宿舍,對台中人生地不熟。已住在台中南區旁大里區的長青,不時會相約出來聊天談詩,談文學。那時在學校下課,學生問老師等會去哪?我回答,準備跟詩人聊天去。
詩人,因為我與長青的友誼,顯得如此日常,不像書本紙本那樣有隔。讀長青詩作,特別是台語詩作部分,往往能再加上長青的口吻語音,更顯親切深刻。詩作的文字,一旦被語音恢復,便能得到一種音量的支持,聲音更能凸顯為一種詩的修辭。如此之聲音美學經營,臺灣前輩詩人楊牧可為代表。然則,長青所走的詩聲音路線,顯然是楊牧所未行之的台語詩實驗。
我特別以台語詩實驗稱長青之台語詩寫作,因為目前台語詩書寫的發展,主要建立在一個母語非法/不能的歷史前提;亦即:在戰後臺灣戒嚴背景下,對於族群母語的壓抑,將國語/北京話知識化與政治化為公眾話語,進而建立一個國語共同體。因此,寫母語詩,使原本被壓抑的言說得到舒展同時,也具有其將非法而成當然的政治戲劇張力。
但詩終究是詩,其語言美學並非單純建立在「可言之」的部分,而更在「如何言之」,乃至於實驗性上,由此才能擴張語言之可能,以及對應語言的意義幅度可能。相對一些語言直白,或者題材限制在鄉土親情題材的母語詩,長青的母語詩是能看到一種現代主義的嘗試,甚至帶有一種後現代的可參與創作性。語言之為用,不只在指事,更供以人予以想像,探勘想像,即便是母語,亦不違此道,因此母語詩書寫,也應成為獲知、想像的工具,如此母語,乃至於母語詩方能成活。
韓愈〈進學解〉有言:「沈浸濃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咀者,細細咀嚼體會;英華,則精華也。如今詩人長青將其歷年刊行之詩作,再擇取為選集,無疑正是其詩作精華中之精華,為讀者提供詩人詩作中的名山勝景,亦足以為將來臺灣現代詩史與詩學論述之品取,是為序。
解昆樺
2020.8寫於臺中柳川畔
序二
攏是人生的條件——讀李長青《我一個人》
《我一個人》是李長青創作生涯的重要詩作自選集,收錄的作品出自《落葉集》、《陪你回高雄》、《江湖》、《人生是電動玩具》、《給世界的筆記》、《風聲》等書,漢語與台語兼具,總是用最鮮明的意象來傳達最內藏的感受,在語言、腔調方面試盡了各種可能。有時候,李長青在詩裡面會用直白的、粗線條的方式講事情,有時則吞吞吐吐讓詩充滿曖昧。不論明朗還是曖昧,都有一股厚道踏實的力量。
中年回望,對這個世界,李長青總是說「好哀傷哪」,然而他的哀傷終究還是成為了詩,而不是流向絕望。偶爾相聚,聽了無數次「好哀傷哪」,我總是想著艱難的現實生活令人過敏,大部分的人默默忍受也就得過且過了。只是寫詩的人,治不了自己的敏感已經夠累,還要去描述最敏感的那些事情,尤其累上加累。李長青說:「我們在遙遠陌生的詩句裡翻騰,試圖釐清世界,所有愛的淚痕。」用流過淚的眼睛看世界,詩大概就是李長青愛的淚痕吧。
我常問長青,關於最珍貴的體液的某些事(其實就是為之流淚的那些事)。他偶爾說個幾句就不說了,更多時候是笑而不答,然後轉移話題用幽默感化解我所造成的尷尬,繼續稱讚我是個天使。每當我察覺自己過度尖銳,我會翻一翻長青的詩集,以此調伏不穩定的情緒,讓自己沉靜下來。大部分的台語詩,讀出聲音來的時候,讓我彷彿置身高雄。或許,那就是鄉音,土地或心理的鄉音。
重新整理、盤點二十年來的作品,對每個作家來說都不是件輕易的事。在時間裡,我們會發現有些事物該捨該留,「攏是人生的條件」。人生免不了交換,有些人交換比較赤裸顯得有些醜陋,有些人即便是在交換也能創造出優雅的秩序。或許長青跟我一樣,是希望生活裡有多一點優雅的人,盡可能避免不必要的交換,在有限的交換裡仍然可以維持一份純真。
Alone,獨自,一個人,那都是「我」的本來面目。「好哀傷哪」,我有時也會用長青的口氣這麼感嘆,然後不自覺笑了出來,Alone但是又不Alone。我們在語言裡彼此作伴,大概是上天對人類最幽默的施捨了。李長青式的哀傷是這樣的——
黑暗之中
有風,輕輕流過
在自己裡面的
我,就這樣一個人
獨自擁有
清澈的淚痕
我揣想,珍貴的體液,清澈的淚痕,愛就是愛的證據。
凌性傑
註:標題引用李長青詩句
序三
日子裡的皺褶,還是有一些什麼存在著的
書桌桌面角落,一直躺著一張稿紙,寫著工整的一首詩,題名是〈盡責〉,內容是:
但他們一直過去╱一直過去
他們對於一直過去這件事╱一直非常盡責
這詩親手的抄錄者與創作者同人,就是李長青。記得那日,我們享食了一頓好吃的晚餐後,他送給我一則從生活中私釀的驚喜。與長青吃幾頓飯後會發現,他對餐廳選擇的要求,自有他的規格在;所以,每次小聚時的餐廳幾乎他選的,而這餐廳也必須要有很厲害的甜點,才圓滿。我跟長青真的非常不一樣,即使落腳住在台中多年,理當有一張私藏的美食味蕾地圖,但我的飲食習慣總還是圍繞在「方便」與「隨便」的吃食上,印象中真無為了某一餐廳特別的「美食」或某一「甜點」,從海線塞車到市區。但我幾次舌尖上的驚喜,就是由長青為我寂寥的日常添了酸甜。
李長青對美食的要求與嗜甜的喜好,可能是詩人的浪漫吧。他詩人的浪漫不止於此,盤飧間必不剩食。他總說,生活時有困境,只好用美食創造日常美好,但不要浪費食物。那次,在杯盤間,長青慢慢地從包包拿出一張稿紙。那是一張撕去了一半的稿紙,稿紙上,用鉛筆寫下一筆一畫極是工整的文字,與其說,那是一張稿紙,不如說,那是一張回收的稿紙。雖是半張稿紙與半首詩抄,但那就是長青常給我既浪漫又充滿真實感的感受。
我們現實情境的生活感裡,總充滿著真實的困境、泥淖與反抗,但卻又挾藏著一些溫暖與甜蜜感。長青詩作裡的語境,就充滿著這種真實的生活感。長青的詩常常藏不住自己內在的意識,想在現實與理想間的皺褶裡,尋找自己的身影,如〈目的〉寫道:「終於意識到,我是多麼蒼老的目的。/這裡曾經躺滿各式各樣的,詩體:標點,斷句,典故,天氣,以及刪刪改改的暴風雨。」又如:「我一個人/靜靜躺在這裡/在自已裡面/尋找/一個人……」。我常常在他的詩裡想望著他高瘦的身影,歎想著此人真的是好認真地在生活啊。
當然,創作者對於現實生活的反思與覺察,是徹底且幽微,詩人對現實生活語境的敏感度,是如此,對於長青而言,更是如此。《我一個人》所收錄的詩作,皆來自長青過往《落葉集》、《陪你回高雄》、《人生是電動玩具》、《給世界的筆記》、《江湖》及《風聲》等詩集。透過《我一個人》及其過往詩集、詩作可以看見長青創作的軌跡,《落葉集》的詩作文字密度含金量不但高,且在詩的形式上盡量到極大化。這現象是必然,也是每個創作者進攻文壇基本招式;但,長青的創作很快地超越形式主義,進入到內容向度的張力,他在創作的虛實之間找到了兩個書寫的脈絡,如在《陪你回高雄》及《風聲》二本詩集中所展現的語言風格及關懷議題的姿態,便一再貼近台灣這塊土地的靈魂,透過詩的穿透力與台灣這土地裡的母體進行對話,這些對話,充滿溫情與溫暖。如在〈1975〉這樣寫著:
母土高雄,我的╱誕生地,如果我不曾╱返回,不曾游入你╱光燦的水波
1975這一串奇妙的╱密碼,永與無法嵌入
青春的屬地╱親情的版圖
除了貼近土地的溫度進行書寫外,李長青的詩作不在華麗辭藻裡找自己,而是以有聲的詩句回應著日常的真實,《人生是電動玩具》及《給世界的筆記》裡的創作脈絡,就是環繞著這樣的頻率。如〈水龍頭〉一詩中,就流洩著這樣的生命音頻:
回到家,扭開水龍頭,看自己的眼淚在水槽跳舞,啊!我已經這樣活著40年了。
水龍頭釋出悲傷的流質,是我的還是房子的眼淚?「我已經這樣活著40年了。」水龍頭對我說。
這詩,既悲又濃,多麼真實的日常呀。
我不是詩人,僅喜歡讀詩,詩裡透顯的光度,常讓我感到生命裡大喜大悲的那一剎那暈眩感;同時,我也不認為我是長青最貼近的友人,但兩次被邀請為其詩集寫些祝福,或許,或許,也因他在台中近山城的那一端,我在海的這一邊,山與海,既是距離卻又各自擁有自己一片的壯闊與日常。繼續期待長青詩魂裡下一次的壯闊與日常。
黃文成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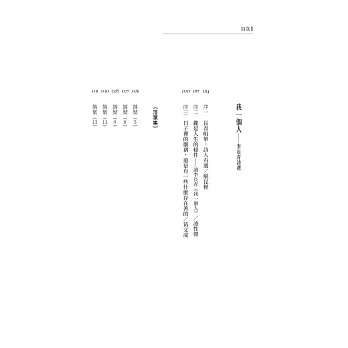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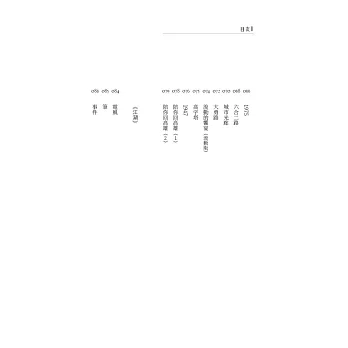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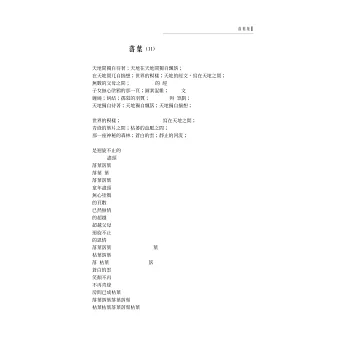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