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後記
繁霜盡是心頭血,革命自有後來人
2020年1月17日淩晨,我接到父親打來的電話,告知我的祖母王益才女士終於與分別整整五十年的愛人──我的祖父韓溫甫先生在另一個世界相會,離開了這個給她帶來痛苦、幸福、悲傷與希望的塵世。在享壽九十六歲、一生波瀾壯闊的祖母面前,我們每一個人都如此渺小,之於我而言,祖母的身份當然不只是一個家裡德高望重的長輩,而是我精神的引路人,當中很大一個原因,在於我對於抗日戰爭乃至中國近代史的興趣,源自於我的祖母。
她於1925年出生於東北奉天(今瀋陽市),父親王金榮(字作贏,原名王滿倉)先生是一位極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通曉日語與鐵路技術,是當時東北「鐵路王」張作相的深縣(今河北省衡水市)同鄉,因此深受張作相器重,被推薦至當時日本人經營的安奉鐵路奉天站任職,該鐵路雖然由日本人控制,但卻有大量中國人參與要務,當中許多中國人是具有愛國情結的知識分子,在東北易幟之後,他們都暗中為國民政府提供許多情報。因當時東北尚處於國民政府的管轄之下,這些地下抗日的英雄好漢又有張作相保護,日本當局亦無可奈何。
但是好景不常,「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徹底控制了東北,像外曾祖父這樣早已為日本當局所忌恨的人物,當然在拔除名單之列。我祖母曾回憶,在「九一八」之後,他們全家與許多人一起湧出瀋陽城,乘坐列車抵達大連,並乘坐海船到達天津。目的地是她之前從未去過的家鄉──河北深縣。
我在〈一個家族的抗戰史〉一文當中如是寫道:
東北淪陷不久,《塘沽協定》《秦土協定》相繼簽訂,華北又淪陷。東北舊部抗日者甚眾,包括我祖母後來的同事閻明光女士的父親閻寶航、齊邦媛先生的父親齊世英、潛伏敵營的知識分子梁肅戎與王德威老師的父親王鏡仁,以及愛國將領呂正操、黃顯聲等等,他們都是東北抗日的中堅力量。
這個流亡的場景永久地印刻在祖母的記憶中。多年之後,在齊邦媛先生的巨著《巨流河》中重現了這一歷史危機時刻。《巨流河》是祖母臨終前拼著最後一點眼力讀完的書。她未向我談及讀這本書的感想,只是在2010年的某個夏天,我發現她獨自一人坐在床頭,望著遠處落山的晚霞,手裡拿著《巨流河》,面色凝重,悵然若失,我沒有打擾,因為我知道,雖然八十多年過去了,但那個慘痛、流亡、無家可歸的悲苦記憶,一直都在。
祖母對日本侵略者有著刻骨的仇恨,並不只是國土淪陷帶給她的流亡記憶,更是因為她的父親在1937年被華北日軍委派的兩名殺手殺害,這曾是我們家族史當中的一個謎案,我一直希望知道,外曾祖父究竟是如何死於日寇之手的。作為一個已經解甲歸田、手無寸鐵的讀書人,哪怕有過收復失地的夢想,但也未曾帶過一兵一卒,日本人為何苦苦追殺不放?對於上述疑問,祖母曾三緘其口,並囑託我一定在她病逝後燒掉她與其父母的早年合影,當然一個可以說明的理由是因為她希望永遠地與自己的父母生活在一起,另一個不便說明的理由是因為外曾祖父的死另有隱情。後來我追問不放,祖母便告訴我,是因為外曾祖父在當地被民選為「抗日村長」,拒絕向日軍繳糧,因此遭到當地日軍與偽政權仇恨,被兩名僱傭的殺手暗殺──傳聞當中還有一位是日本人。
直至祖母病逝之後,我申請查閱祖母生前檔案,才發現這段使我震撼的歷史遠非我想像或祖母口述的那麼簡單。外曾祖父流亡至華北後,一直從事地下抗日工作,也希望可以組織一些鄉間力量抗敵。但無奈個人勢單力薄,眼看鐵蹄南下,縱然悲憤,難免也只有觀望,有時在家中發發牢騷。最多在擔任民選村長時,用自編的歌曲鼓動村民們做好抵禦外侮的準備,誓死不當亡國奴。
華北完全淪陷之後,在家鄉擔任民選村長的外曾祖父忽然對當時的局勢有了自己的判斷,認為與日寇拚死一搏的抗戰決戰時機已到。一是此時再不抗戰,神州陸沉是指日之事,二是目前一些東北舊識還擁有一些軍事實力,如今日寇雖長驅直下,但亦是誘敵深入,在中原一舉殲敵甚至收復失地或有希望,於是他自行給曾有過從、駐紮在冀察地區的陸軍六十九軍軍長石友三(而且外曾祖父有一位遠房表弟是長春人,曾在石友三部擔任副官)寫信,曉以民族大義,希望當時觀望時局的石友三出山抗日──這是我先前並不知道的一段家史。
這個舉動再度證明了,外曾祖父只是一個簡單的讀書人,空有一腔報國熱血,並不諳熟當時的政治角逐與軍事鬥爭,在手腕上更非石友三這樣軍政通吃的老牌政客的對手。祖籍吉林長春的石友三,雖曾在張學良將軍麾下短暫效力,但卻毫無東北人的血性,在民國軍界以「三姓家奴」而聞名。當時他表面上「不親日、不親共、非中央軍」並非刻意保持氣節,而是出於擁兵自重、待價而沽的考量,無非妄圖拉高價碼,哄抬自己身價。外曾祖父個性耿直、待人單純,並未深究石友三的卑劣用心,而認為其猶豫不決,無非對於抗日必勝沒有信心。在如此複雜關係博弈下,這封信竟然輾轉落入日軍之手──仔細想來也不排除石友三借出賣故交來表達自己立場,這或是使外曾祖父遭受殺身之禍的緣故。
因為要為父報仇,祖母踏上了抗日救亡之路,她通過我祖父這位同鄉兄長的介紹下,毅然從軍,成為了第十八集團軍的一位女戰士。在冀南八年抗戰硝煙中,她親眼目睹了日寇的殘暴兇頑,同時也如外曾祖父一樣,相信抗戰過程雖然充滿苦難,但中華民族最終必勝。在多次戰鬥中,祖母接連獲得表彰,無愧於一名傑出的抗日女戰士。
眾所周知,石友三後來變節投敵,並殞命於部下高樹勳之手,被活埋於黃河岸邊,是國民政府與共產黨共同聲討的叛將。在1960年代,中國內地政治運動風起雲湧,與石友三這樣的人物相識,必是彌天大罪。因此祖母對於外曾祖父的死因,一直諱莫如深,多年之後,即使有重要人士曾在祖母檔案中批示「即使(王作贏)真的聯絡石友三(抗戰),也罪不至死。」祖母亦從不言及外曾祖父的這些人際交往。
祖母是我的啟蒙老師,與其他同齡人相比,我更瞭解抗戰這個離我出生已有半個世紀之遙的往事,抗戰中的烽火硝煙構成了我人生當中極其重要的知識底色。祖母曾告訴我,在那個時代下,抗戰從來不是哪個黨派或是哪個人的事情,而是全民族的任務。即使祖母未曾告訴我關於外曾祖父的完整歷史,但她為我講述的那些故事,足以讓我對這場全民族的戰爭有著極其特別的體會。正如祖母檔案中所披露的那樣,抗戰中湧現了許多像外曾祖父這樣的「志願者」,他們只是單純地想做一些地下抗戰的工作,但可惜出師未捷身先死。在抗戰史上,像外曾祖父這樣的無名英雄必然還有許多。
十五年前,我決心挖掘抗戰文化史,這部《血火之舞:抗戰文學期刊與中國社會思潮(1931-1938)》就是對相關問題的一些思考,當然我近年來還在做一些關於抗戰文化產業、文化活動的考證、研究工作,這些都是目前與今後重要的學術事業。
這本書命名為「血火之舞」,意味著瑰麗壯闊的抗戰文化史實際上是一部血與火的壯烈交響樂,借王德威教授之語,乃是「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血」在當中是主旋律。這正是無數願意驅逐倭寇、收復河山的中國人矢志不移的史詩。我們作為新世代的年輕學人,對於這樣一部可謂「繁霜盡是心頭血」的歷史,當然要以「革命自有後來人」的精神來繼承。
這部書從撰寫、修訂直至今日在臺灣出版,歷經反覆斟酌,此文最早由我申請武漢大學博士學位的論文所脫胎而來,撰寫期間得益於張隆溪教授與樊星教授的耐心指教,而趙毅衡教授、楊聯芬教授與許祖華教授曾為拙作的修訂付出良多,在此由衷致謝。已故漢學家阿里夫‧德里克教授、王德威院士、李金銓教授、陳子善教授、吳秀明教授、令狐萍教授、鄺可怡教授等前輩學者不但為拙作的完成提供了重要的指導,亦為此書出版撰寫了抬愛之語,讓敝著增色不少。只是遺憾的是,德里克先生生前未能看到拙作出版,我深以為憾,但先生對我的鼓勵與支持,我將永遠銘刻於心。當然,這部書的問世還得益於秀威資訊科技宋政坤、蔡登山二位先生的提攜,以及鄭伊庭、許乃文兩位編輯老師的費心努力,當然還包括周妤靜、劉肇昇二位裝幀設計老師的辛勞付出,我在這裡向各位同事敬表最誠摯的謝意。
與德里克先生一樣,我敬愛的祖母也未能看到此書正式出版,這之於我而言,都是無法彌補的遺憾。但她生前一直知道我在做抗戰史研究。這本書當然是獻給她的禮物。她一生自強,凡事求諸己,她也要求我在治學的道路上做一個有著獨立判斷力的學者。如今東亞再無硝煙戰火,「抗戰」已非全民族的精神洪流,而是成為了學人案頭研究的一個專業領域──雖然它並非時下年輕人所熱衷的學術課題,但對於我而言,卻能感知到追尋問題的樂趣與繼續深研的動力,我想這應是對外曾祖父以及祖父、祖母的精神賡續使然。
韓晗
二○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於小茗堂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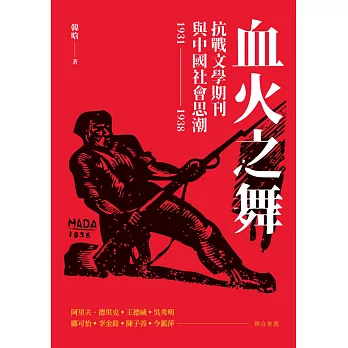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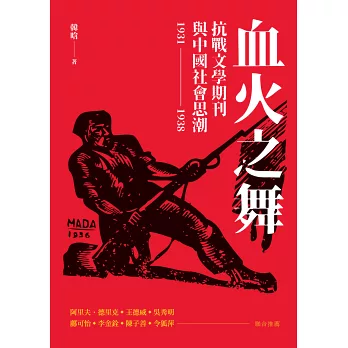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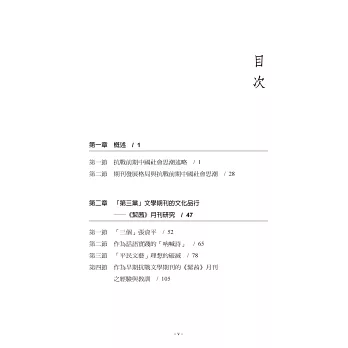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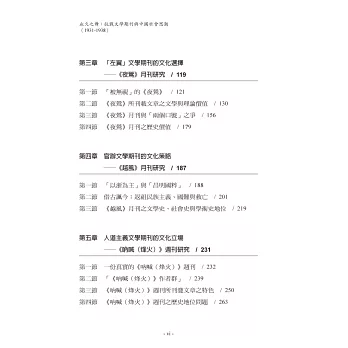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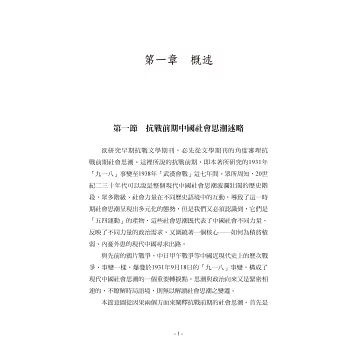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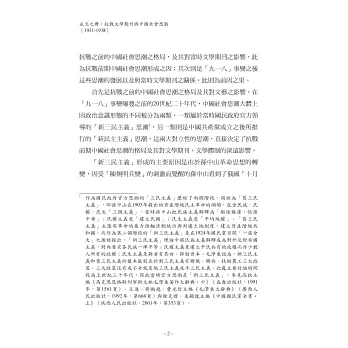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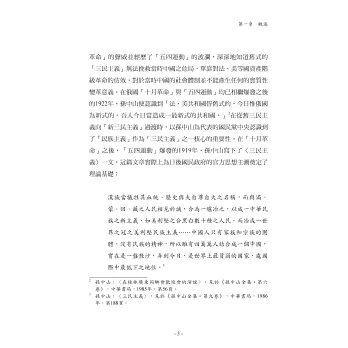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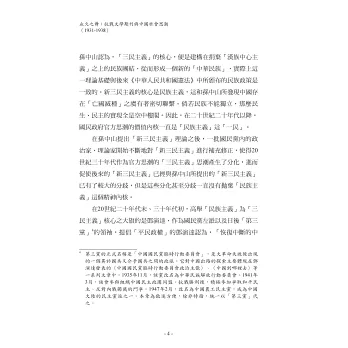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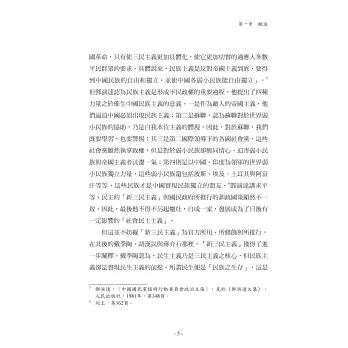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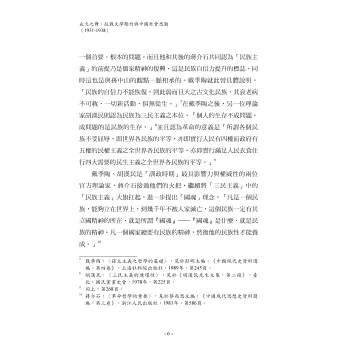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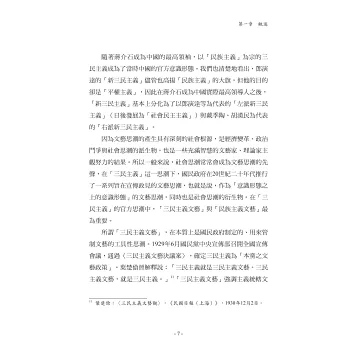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