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1 與神結伴 一個普林斯頓大學的博士班學生問道:「世上還有什麼從來沒有探討過的論文題目呢?」愛因斯坦回答:「去研究禱告,必須有人去研究禱告。」
我選錯了時間造訪俄羅斯的聖彼得堡。我在二○○二年十一月到那裡,正趕上聖彼得堡為了慶祝來年三百週年的大肆修繕。每幢重要的建築物都搭上鷹架,古色古香的鵝卵石街道上,到處都是碎石瓦礫,使我每天的晨跑險象環生。我低著頭,摸黑而跑(在那個緯度,太陽很晚才升起來),一面躲避堆在一旁的磚塊和沙土,一面注意前面路上有沒有暗淡的反光,表示有結冰。
有天早上我一不留神,瞬間臉朝下仆倒在街上,頭昏眼花,全身發抖。我坐起來,隱約記得跌下去的時候把頭偏向一邊,才沒有撞到人行道邊緣突出來的鋼筋。我脫下手套,摸摸右眼,感覺溼溼的。我的整個右臉都是血。我站起來,拍掉身上的雪花和泥土,看看有沒有其他損傷。我慢慢抬起腳、抬抬手,試著讓發出陣陣刺痛的膝蓋和手肘活動一下。
我嘴裡也有腥味,直到過了兩條街,才發現一顆門牙不見了。我只好折回去摸黑找,卻找不著。
我走到繁忙的涅夫斯基大道,發現大家都盯著我。俄國人通常不會直視陌生人,我想我的模樣必定很嚇人。我一跛一跛回到旅館,說服了滿臉狐疑的警衛,終於來到房間門口,敲門說:「珍奈,讓我進去,我受傷了。」
我們夫婦倆早已聽聞俄羅斯醫療照顧的恐怖故事:你很可能只是為了外傷去就診,卻感染到愛滋病或肝炎。所以我們決定自己料理傷口,從房間的小酒吧找到幾瓶小小的伏特加,用來清洗臉上的傷痕。我的上唇裂成兩半,我咬緊牙關,把酒精倒在傷口上,用一包德航班機上的濕紙巾,把臉擦乾淨,再拿一塊OK繃將兩邊嘴唇緊緊黏在一起,希望復原後嘴唇不會變歪。此時我的眼睛周圍已經腫成一大片紫紅色,幸好視力似乎沒有受到影響。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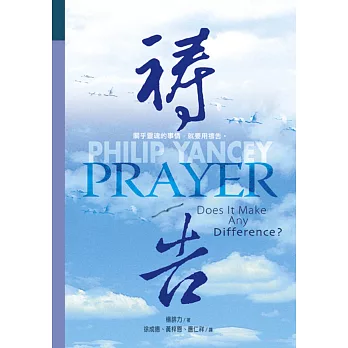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