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畢德生若不是隸屬於長老教會,很有可能會是個修士。他最為人熟知的幾本書,從《天路客的行囊:恆久專一的順服》(A Long Obedience in the Same Direction)、《生命真正的自由》(Traveling Light)到《翱翔的禱告:從自我到群體的十一個練習》(Where Your Treasure Is),探討的內容都與基督徒靈性操練有關。
畢德生的模樣也的確很像修士。他蓄留鬍髭、頭頂圓禿且身形瘦削。他的嗓音沙啞低沉,像是度過許多心靈黑夜的人才會有的聲音。他沉靜而安舒的神態,來自面對並克服人類內在對寂靜和獨處的恐懼,因此當他開口說話時,那些質樸且溫柔的話語,像是由衷地發自靈魂深處。
但是,撇開修士的氣質不論,畢德生可是個徹頭徹尾的新教徒,足以擔任美國馬里蘭州貝萊爾市(Bel Air, Maryland)「基督我王長老教會」(Christ Our King Presbyterian Church)的牧師。他在剛開始牧會時,就決定不要牧養人數過多的教會,以免他無法記住每個會友的名字。他和妻子珍(Jan)在基督我王教會已服事了二十六年(編按:此篇前言寫於一九八九年),會眾約有三百人。
自一九八○年《天路客的行囊》一書出版以來,畢德生就以思慮縝密清晰、深諳屬靈操練之道,並且能清楚傳達和實踐的牧師形象,受到廣泛(但力求低調)的認識。他在牧會和寫作上饒富學養,精通聖經原文,並曾與該領域權威學者奧伯萊(William F. Albright)一起做過博士等級的研究。然而,他在學術上的成就並不是為了炫耀;事實上,畢德生對於人們一再詢問與他的書有關的問題感到不自在。他強調,自己的身分與一生的目標,僅是作為一位可信賴的牧師。在這個標榜誇大不實的浮華世界,他默默努力於推廣正直、簡樸與踏實。
一九八七年九月,我和畢德生夫婦共處了三天的時光,但不是在貝萊爾市,而是在他已故父母位於蒙大拿州西北邊的家,當時正好是他的安息年(畢德生對這一年的反思,參見本書第十三章)。這幢房子坐落在平頭湖(Flathead Lake)的湖灣附近,屋後湖水倒映著寬闊的天空,彷彿一面藍色鏡子,一路延伸至十英里遠,覆蓋白雪的洛磯山脈環抱著這片湖泊。畢德生對這個地方顯然喜愛有加。一天傍晚,他站在廚房凝視窗外,即將落下的太陽將閃爍的湖光投射到天花板上,他雙手插在牛仔褲口袋裡,喃喃自語道:「這地方真是美極了。」
畢德生夫婦在蒙大拿州一直待到十月,他們利用餘暇禱告、到鄰近山裡健行、一起朗讀、越野滑雪。畢德生寫作時,珍則替他草擬的兩本書稿打字。他們獨自相處的時間—對任何牧師夫婦都是彌足珍貴的時間—偶爾會被三位子女凱倫、艾瑞克、萊夫(Karen, Eric, Leif)的到訪打斷。
九月是進行採訪的理想時間。畢德生已從安息年恢復活力,興致勃勃做好準備要返回事奉崗位,也樂意和我會談。我們花了好幾個小時做錄音訪談,偶爾也會起身到屋外山間漫步,他好整以暇地和我討論這裡的地質結構,提及印地安人冷杉毬果的傳說,點出一長串的野生動物名稱。但無論話題如何多變,總會一次又一次回到和靈命有關的主題:所在之地的重要(the importance of place)、創造力的任務(the role of creativity)、群體的中心地位(the centrality of community),以及基督徒式顛覆的必要(the necessity of Christain subversion)。我問他,是什麼將這一切牽繫在一起, 畢德生引用貝爾納諾斯(Georges Bernanos)《鄉村神父日記》(Diary of a Country Priest)書中的最後一句話來回答:「無處不在的恩典。」這時一隻魚鷹正好飛越湖灣,從他身後掠過。
靈性和所在之地的關係
如果有人⋯⋯期待在善行播種之後立即看到成效,
他會失望。假如我希望明天晚餐可以吃到馬鈴薯,
今天晚上才出門去菜園栽種,並沒有多大用處。
栽種和收成之間隔著漫長的黑暗、不可見和寂靜。
在持續等待期間,我們仍然需要耕作、除草、施肥,
和繼續栽種其他種子。—《 生命真正的自由》
問:如果就用詞來看,你的書中充滿了大地氣息,其中有不少與農業相關的比喻,譬如《土地和祭壇》(Earth and Altar;編按:英文書名再版時更名為Where Your Treasure Is)這樣的書名。儘管我們活在一個頻繁移動的社會,你似乎仍然具有強烈的地方性,非常強調一個人所在之處的重要。
我很喜歡讀詩人農夫溫德爾.貝里(Wendell Berry)的作品。他在肯塔基州有一小塊地,他對這塊土地心懷敬意、悉心照料,就像藝術家委身於創作素材一樣。每當書中提到「農場」和「土地」,我都會自動加上「牧區」。他所說的農事,也是我試圖在會眾之中實踐的東西,因為牧會工作的巧妙處之一,在於所在之地(locality)。
牧師需要面對的問題是:「這些人是誰?我要用什麼方式和他們相處,使他們可以成為神所要塑造的那個模樣?」我的職責就是身在其中,盡己所能地教導、傳講聖經,誠實地面對他們,不做任何會妨礙聖靈在他們身上所要形塑的工作。神是否可能正在做某些我未曾想過的事?我是否願意安靜等待一天、一週,甚至一年?我是否願意像溫德爾.貝里一樣,願意花五十年的時間開墾這片土地?並且,是和這些人在一起?
基督徒的靈性生命,意味活在整全的福音之中。這表示我們要以信心的行動去經歷生活中的一切,包括孩子、配偶、工作、天氣、財產,以及人際關係。神希望使用我們生活中所有的一切素材。
問:以信心的行動去經歷生活中的一切,這是什麼意思?
意思是,我的責任就是在我所在之地,留心聽從神的語。靈命的前提是:神總是在我明白之前,就已經著手在進行那件事了。因此,我的職責不是要神去做我認為必須要做的事,而是意識到神在做什麼,以便我能夠回應祂,參與其中,並以此為樂。
當我全心投入我的牧區,並在一天工作完回到家後,經常對人們生活中發生的事感到驚奇。他們依然是罪人,生活中依然犯罪、悖逆,也做蠢事,但是幾乎每一天也都有關乎勇氣和恩典的事發生。當我做我該做的工作(也就是我不是超然地站在一旁,而是投身於我所屬的環境中),通常在一天結束時,我最常會有的感受,就是因著神在這些人身上所做之事,心生敬畏。
問:哪些事讓你對此有深刻的感受?
我想到莉和喬(Leigh & Joe Phipps)的故事。莉是我小兒子小學一年級的老師,當時內人珍是她教學工作上的助手。有一次,珍問她要不要來教會?莉說好,但是她不想要穿正式服裝,因為星期天是她的牛仔褲日。珍告訴她,她可以穿牛仔褲上教會。
從那時起,一種打趣方式在她們之間形成。珍會在百貨商場看到莉時說:「別忘了洗妳的牛仔褲。」只是莉還是一直沒來教會。幾年後,我們的女兒凱倫修了一門陶藝課,莉也在同一班,於是她也認識了凱倫,然而來教會一事仍然沒有任何進展。但是,我們都還是住在同一個社區。直到兩年前,奇妙的事發生了,經過二十年的禱告和等待,莉成為了基督徒。
故事還沒完。莉和喬相識於學生時代,莉那時就已喜歡上他。他們斷斷續續地交往,但是喬的人生可說是一團糟,他沉迷於吸毒,最終因走私被捕。到了中年,他希望能夠有所改變,前來找莉尋求幫助:「我不知道人生有什麼意義。」
莉跟喬說,她認識一位牧師,於是將他帶來找我。最後,莉和喬結婚了。他們邀請我在婚禮上彈奏斑鳩琴,請我以及珍一起獻唱讚美詩〈更加向前〉(Farther Along)。莉和喬以及他們的婚姻,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因為喬仍在服刑,但是當他寫信給我時,信上會署名「更加向前」的喬.菲普斯。
問:也就是說,身為牧師,你會在看似不可能的情況中看見恩典?
是的。我的工作原不是要解決人們的問題,或者讓他們開心,而是要幫助他們看見恩典運行在他們的生活當中。這並不容易,因為我們的整個文化都與此背道而馳。
人們常說,如果你夠聰明,並且得到適切的幫助,你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事實上,聖經中沒有太多快樂的人,有的卻是在生命中經歷喜樂、平安,並體會基督受苦意義的人。
靈性的功課在於認清我們身處何處(我們每個人所生活的特殊處境),並在其中認出神的恩典,進而說出:「你是否認為,神與我同在的方式,並非透過改變我的配偶,或是讓我擺脫配偶或孩子,而是神希望改變我,並在我的生命中做某些事,而且倘若沒有經過這樣的痛苦和折磨,我將無法經歷?」
有時候我會想,我作為牧師所要做的事,就是在尚未有人提及、也沒有人察覺神同在的處境下,提到「神」的名字。「喜樂」正是人們聽見神的名字並感到祂的同在時,所帶出的能力。我們會因為神正在動工而感到欣喜,即使是件很小的事,在當下就已足夠了。
靈性和創造力的關係
饒恕罪人、幫助受傷的人、擔負起個人的責任等, 從這些日常生活行動中,都可以瞥見恩典深具原創 性的工作⋯⋯而且這些創造持續在發生。街道和田 野、住家和市場是一座藝廊,其中展示的不是文 化,而是在基督裡的新創造。 —《生命真正的自由》
問:您曾寫道,過一個有創造力的生活,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能力;但是,我們許多人都做不到,這是為什麼?
主要的原因是懶惰。要過一個有創造力的生活,其實是不容易的,當你行使創造力,等同於是憑信心生活。你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因為按照定義,創造的產物原先並不存在。因此,你是處在沒有太多把握的事物邊緣。你可能會失敗:事實上,幾乎可以肯定,你會失敗一段很長的時間。所有我認識從事創作的人,幾乎都會扔掉他們大半的作品。
問:也許我們無意過有創造力的生活的另一個原因,在於我們對創造力的理解很狹隘。我們認為只有藝術家和小說家才具有創意。
事實上,大多數的創造力並不明顯可見。例如,大多數人並不是生來就有運動員的體格或畫家的配色能力。但我認為每個人都有創造力,只是創作素材有別:我們的素材是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
沒有一個人的生活裡是完全沒有恩典的。我剛讀完一封從西雅圖寄來的信,那是朋友露絲(Ruthie)寫給珍的信。他們夫妻有個一歲大的寶寶,去年出生兩三個星期後,他們發現寶寶看不見,幾近全盲。
我在露絲還是青少年時就認識她了,所以我為他們夫妻感到心痛。露絲的先生戴夫(Dave)是個充滿活力、喜歡戶外活動的人,全世界各大洲超過一萬英尺高的山峰,都有他的足跡,他的身上流露出一種深沉、安靜的生命特質。他們是一對很棒的夫妻,卻生下一個看不見的孩子,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感受到深沉的傷痛和難過:「這樣的事為什麼發生在戴夫和露絲的身上?」
但是,昨天我和露絲通電話,她卻說:「我的人生有過很多很棒的經歷,但沒有一樣比得上作為一個母親。」她又說,我們應該看看戴夫和寶寶愷恩(Cairn)在一起的模樣。愷恩才一歲多,然而她已經去過奧林匹克半島、喀斯喀特山脈、落磯山脈和大煙山的山頂。戴夫每次登山都會帶著她。
愷恩牽引出他們夫妻倆最好的一面,無論從哪方面來看,她都是神所賜的一份禮物。這就是以充滿創造力的方式在生活的一對夫妻:他們接受神賜予他們的任何事物,將其帶入具有恩典和救贖的人生。
靈性和群體的關係
成為教會的一員,這是我們信仰基督的必然結果。我們不能只是一個基督徒,卻與教會沒有關係,就如我們不能只是一個人,而不屬乎家庭。⋯⋯教會是救贖結構的一部分。—《天路客的行囊》
問:美國基督徒傾向看重個人的禱告,更勝於團體禱告或在崇拜中禱告。你在寫作中提到,你對這種傾向感到不安?
的確,我為此感到不安。基督徒具典範意義的禱告,應當是在群體中,而不是個人單獨進行。聖經的基本脈絡就是崇拜,這就是為何對我而言,崇拜就是禱告的所在,唯有在這樣的脈絡之下,我們才能恢復福音的深度。
問:這是否表示,我們應當在群體中學習如何禱告?換句話說,我們個人的禱告其實是根源自群體的崇拜?
這正是我的意思。假設有人來到我面前說:「請教我怎麼禱告。」我會回他:「星期天早上九點鐘,請到教會來。」那裡就是你學習禱告的地方。當然,你獨自一人的時候,你可以有不同形式的持續禱告。但是美國人經歷的順序是顛倒的。在源遠流長的基督教靈修史中,群體禱告是最重要的,然後才是個人的禱告。
問:我們在群體禱告中,可以學習到哪些事?
其中一件可以學習的事,就是在禱告中接受引導。我們很容易將禱告視為由自己主動發起的行動,當我意識到自己有某種需要或感到高興時,我就禱告,重點都在自己身上,所以當我禱告的時候會感覺自己是發起人。
但是,若是我來到教會,會發生什麼事?我坐在那裡,然後有人站在我前面說:「讓我們一同禱告。」我不是發起禱告的人,而是回應的人。這使我謙卑下來。我的自我不再顯大。這正是禱告的基礎要素,因為禱告是應答的語言。
禱告必須是對神話語的回應。為了崇拜而聚集的會眾(聆聽神的話被誦讀、被傳講、在聖禮中被尊崇)成為我學習如何禱告和實踐禱告的地方。這是我禱告的中心,我的禱告由此迸出。我從那裡離開,回到自己的密室或到群山之中,繼續祈禱。
另一件有關群體禱告的事,就是當我在群體中禱告時,我的個人感受不在考慮範圍內。當我參加聚會時,沒有人會問我:「你今天感覺如何?你有什麼事情需要禱告嗎?」
因此,我在聚會之中逐漸學習到,感覺不是禱告的的條件,禱告也不需要靠感覺來印證。當我開始用感覺來評判我的禱告,甚至認為,為了禱告,我必須擁有某種特定的感受、某種屬靈的專注和平靜,或者完全相反,要感到痛苦,其實再沒有比這更具破壞力的想法了。
這些功課幾乎不可能靠自己學會。但是,我若身處在群體之中,就會一次又一次學習到,無論我想不想要禱告,或即使我全程都在睡覺,禱告都會持續下去。
靈性和顛覆的關係
禱告是一種具顛覆性的活動。它多少有公開反抗當前體制任何主張的意味⋯⋯〔當我們禱告時,〕即使看似緩慢,但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是文化、家庭、政府、工作,甚至是蠻橫的自我,都無法對抗至高神主權下的沉靜力量和富創意的影響力。家庭和種族之間的血緣連繫、對個人和國家的委身,最終都將臣服於神的統治之下。—《翱翔的禱告》
問:美國基督徒是否太過自以為是,總認為他們周遭的文化就是基督信仰?
沒錯。聽聽從其他文化來到我們國家的人怎麼說,留心觀察這些人所聽到和看到的美國,這會對我們有幫助。我的經驗告訴我,他們所看到的並不是一個基督教國家。如果你聆聽索忍尼辛(Solzhenitsyn)、屠圖主教(Bishop Tutu)或來自非洲、南美洲的大學生怎麼說,你會發現他們看到的並不是一個屬乎基督信仰的國家,甚至有時見到的是完全與之背道而馳的文化。
他們看見很多的貪婪和傲慢。他們在基督徒群體當中,幾乎看不見任何出自聖經的美德,像是捨己的生命和彰顯的愛。相反地,他們目睹我們對感官和情緒的放縱,還有對享樂的無止境追求。
重要的是,他們已經看穿了我們虛有其表的語言,那些我們用來妝點外觀的基督教術語。美國對外來者的吸引力在於物質,而非靈性。聽聽剛進入這個國家的難民所說的話,你會得著啟發:他們想要的是汽車和電視。他們不是追隨我們的福音而來,除非我們將福音解讀為獲取財富和安舒的保證。
問:你會向你的會眾傳講這樣的信息嗎?
我會。
問:你是怎麼做的?我相信這不是容易的事。
我也是他們之中的一分子。我跟他們住一樣的房子, 開同款的車,我和他們在相同的地方購物。所以我和他們 一樣。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
的確有少數人想要擺脫社會自成一群,以突擊隊的方式向社會發出挑戰。但是,那不是我的呼召,我也不認為在教會中訴諸分離主義的說法,具有什麼說服力。因為我們都在社會中有各自的工作,又都在社會上嘗試以門徒的身分找到定位,並在其中盡己所能。如果我也只想過一個離群索居的生活,那麼我會失去眾人的信任。因為我會在星期天講的是一套,週間做的是另一套。
所以,我首先要試著在自己身上養成顛覆者的精神。顛覆者是一個具有文化色彩的人,並將自己揭示在眾目睽睽之下。當他不再具有文化色彩,也就失去了效力。顛覆者用安靜、隱蔽、耐心的方式工作著。他委身於在文化上已得勝的基督,願意從事各樣細微瑣事。從未曾有顛覆者做過任何大事,他總是帶著祕密的信息,在文化遽下斷語之處,種下懷疑。
問:基督徒式的顛覆有哪些具體的行動?
其實都是基督徒平常會做的事,像是捨己的愛、行公義、心存盼望等,當中並沒有新事。我們的任務是發展出基督徒身分的自我認同,然後不是偶爾去行,而是以忠於自我的態度,在每天的生活中行出來。透過彼此鼓勵、一同讀經、一起禱告,我們逐漸建立起共識:這些事確確實實是我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同時我們也會認清,無論世上有多少和基督教有關的文化對談,但世人的生活重心並不會在此。
如果我們可以逐漸讓捨己的愛、公義和盼望,成為我們基督徒認同的核心身分—它們每早伴隨我們去工作,每晚伴隨我們回家—那麼,我們其實就是在做顛覆的工作。你必須明白,基督徒式的顛覆與血氣之爭毫無關係,顛覆者並不是要在血氣上打勝仗,他們所做的一切就是鋪平道路,一點一滴地改變世界的基調,使之往相信和盼望的方向稍微挪動,使人心漸漸朝向基督,等候祂的到來。
問:顛覆(sub-versive)一字的字首有由下而上之意,我們是否應當正視這個意義?
我想是的。我們的工作涉及事物的至深核心之處。福音具有從地底成長的意象,就如同一粒種子在土壤底下進行顛覆。
我有個年約三十三歲的牧師朋友,他的身材高大、外型搶眼、性格鮮明,是那種適合出現在電視螢光幕上或者和知名教會合作的人,但他卻自願從這些成功階梯下來,如今遷居到蒙大拿州維克托(Victor)小鎮上。或許我們需要更多像他這樣的牧師,也需要更多教會歡迎像他這樣的牧師(一個願意委身在一個地方、認真看待一個地方的牧師),以及願意成為一個使用當地簡單素材的教會群體。
至少,這就是我對牧者生涯的理解。我在「基督我王長老教會」已經服事二十六年了。作家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終其一生所熟知的區域,不過是密西西比州方圓兩到三平方英里的地方而已,這就是我想做的事。我想要熟識「基督我王長老教會」兩到三平方英里的地方,單單認識它,並且持續不斷地去認識它。
羅德尼.克拉普(Rodney Clapp)
《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雜誌副主編
寫於一九八九年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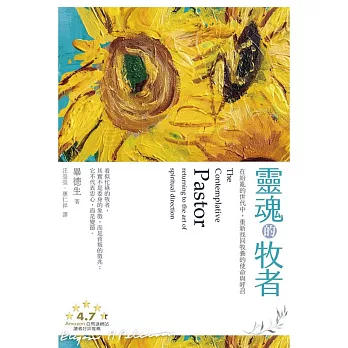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