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當一顆擁抱恐龍的星星
嚴毅昇
初讀這份詩稿,覺得有一種童稚的趣味。
而後細讀、漸漸進入想像世界,那裡白天和夜晚是地球的兩半同時存在,被鐵軌連接起來,山像牙齒咬住鐵軌,恐龍一直在上面奔跑,家有時候是船,會跟著恐龍跑起來。那些畫面,讓我看見Watan、Ali奇想的世界觀。
將〈男孩喃喃〉幾個段落放在一起閱讀,Watan帶我們看見「恐龍」身影,原先看似沒有關聯的喃喃短語,這時想像力帶動出了畫面感,彷彿太陽沿著鐵軌「奔跑」重新回到人間,回到大地,重新摸到太陽,幸好白晝是喜歡愛人的,雲朵會拼成恐龍,也會下雨,詩人們要一直寫下去,發出彩虹顏色的光亮。
在Watan明亮的想像世界中,偶爾也有心情不美麗的一面,讓一個孩童寫出「孤單,是一個人/自己陪伴自己」或「這是孤單的人在哭,黑色。沒人在跟他玩」。這些句子有種超齡體悟。
Ali和Watan的文字有明顯對比,白晝與夜晚、太陽與星星;一個「恐龍在鐵道上一直奔跑」、一個「星星在上面發亮/白天在睡覺/晚上出來玩」。一起寫作,想法卻沒有被彼此干擾,有各自想寫且重複的主題,創作也偶有呼應,當女孩說「花像路。」而男孩說「我的花那麼快快長大,又那麼快死掉。」而Ali的文字有一種疑惑、詢問的說話方式,這是一種文字魅力。
讀〈女孩啾啾〉時,以為Ali喜歡晚上,經常寫黑色的元素(殭屍、魔鬼),但在Ali的眼裡,或許不是我想像的顏色,我讀到Ali在不同詩作重複敘述類似的話,但是有趣的,例如:「白天在睡覺/晚上出來玩」和「把晚上當作白天,白天當作晚上」Ali似乎喜歡這種對比寫作的方式。
〈男孩女孩創作集〉揉合兩人想像,在誤讀《流浪的狗》繪本的過程中,第二首詩〈流浪的狗〉惡狠狠地蹦出來,牠是羊,也是狗,牠用想像咬人,大家記得狗,卻遺忘羊,牠因為孤單所以溫柔,或許詩就是一頭流浪狗。
從〈大人小孩創作集〉開始,出現Makao的引導語,有種接龍的互動感。
在詩中提到「洗腦」一詞,在之後詩的註解讀到:「2016年討論該年鄭捷槍決一案」,這兩首詩簡單的談論權力關係,有明指的對象,論政府、論議題,誰造成人禍,我們為什麼對生活感到疑問?小孩也是能討論嚴肅議題的。
Makao寫給學生的祝福,她帶出了「芬蘭」,談到「夜色是芬蘭的」,Makao曾旅居芬蘭,經歷冰天雪地面對巨大孤獨,黑夜似乎淹沒過一切,第二句:「星星是自己的」有種溫柔篤定感,前述不少詩作描述過星星,這裡談到的星星像一種標的或指向──我們彼此在異地卻一起看著同一顆星,「你好嗎?」向遠方或身邊的朋友打個招呼,如果生命經驗因詩相連,或許可以說是件幸福的事,一種守望。
「生命可以為詩存在。只要有詩就好。傷口都可以縫合起來。」之於Makao而言,Ali和Watan或許就是詩,生命的詩,詩已注入生活的Atayal孩子。
2021.4.12
導讀
詩篇和對話錄,是平地老師和部落小孩在山林教室的日常夢囈。平地老師遊走各部落並旅居芬蘭,經歷冰天雪地和面對巨大孤獨,返台在家鄉的山上部落帶領孩童讀詩寫詩,共同創作,詩領著生命靠近彼此,與大地同在。
兩名小孩來自台中雙崎部落,男孩女孩當時僅七歲,識字啟蒙,指物命名,以詩為始,開啟每日校園生活和國語課。老師採集小孩詩集,為期一年,並約定日後詩集出版,分享小詩人的創作。目前小詩人即將完成小學學業,出版七歲時的創作當作成長禮物,祝福人生探索從山林部落到世界角落。
每日唸詩唱歌,用聲音去指認文字,以此親近文學,小孩的回應除了無厘頭,也有詩意,沒有框架的互動,我振筆疾書採集起小孩的日常囈語,成為詩篇。
寫詩,作為一天的開始,男孩提出聽詩畫畫,再從畫作產生詩,如此完成一年級的課堂日常。詩集呈現原漢互動,師生共同創作與校園日常,以小詩人創作記載兒童哲思歷程。
原住民詩人瓦歷斯諾幹的故鄉雙崎部落,讀詩朗朗縈繞在文學原鄉,期待師生共創出版後,能邀請部落詩人世代對談,並以泰雅語和漢語雙語朗讀,且以此詩集作為小詩人的成長禮物。
自序
Makao馬告
七歲時,我們寫詩。
開始讀詩是在旅居芬蘭之後,我想是那一年面對了巨大的孤獨。世界隔著一層膜,生活周遭很近卻摸不著。我讀起大量的詩,像是和那一年憂愁的自己對話。所有的詩,再也沒有門檻。讓閱讀撫平這層膜的矛盾,那就來讀詩吧,而且這是有詩的部落。我想朗讀(不知道是誰說詩就要唸出來),此時,我有最好的聽眾,男孩與女孩。
識字啟蒙的年紀,初來乍到新世界──學校和課本,指物命名以詩為始,進入體制學習。男孩提議聽詩畫畫,再從畫作產生詩。孩子浸潤在一年級的儀式感,聽詩、讀詩、寫詩。用聲音去指認文字,以此親近文學,我採集小孩的日常夢囈,師生共同創作的校園日常,紀錄兒童哲思歷程。
女孩和男孩都有泰雅族名字。男孩漢名──吳子荃,泰雅族名,Watan瓦旦。Watan自我介紹的時候,女孩接著說「瓦旦,完蛋」,女孩笑得開朗,男孩臉紅害羞。男孩臉紅有時是不好意思,有時是感受到讚美,他經常害羞,而我們不是很確定每次臉紅他感受的是哪種。
女孩漢名──朱祐慈,Ali阿麗。在還沒學到屬於她名字的文字,我並不著急她寫正確,時間會走到學會的那天,那天就好好認識自己的名字。文明來臨前,字是塗鴉繪畫,每位小孩學習寫字的過程類似人類文明演化的縮影,沒有規則只有無窮的想像力,小孩從半獸人過渡到文明時代(咦?),寫他們以為的字,模仿而生的字體,歪曲拼湊還夾雜插圖。我們先學ㄅㄆㄇ,我第一次教而他們第一次學,我們是彼此的新生。
時間緩慢,終於學到「心」這個字。女孩說「我的名字裡面有『心』耶!」,她在自己的名字裡找到心。以字識字,找字過程逐漸拼湊自己的模樣,彷彿遊戲。我們一起完成這遊戲,或者說,女孩教會我如何玩遊戲,找到名字裡的心時,心臟真實地跳動,怦然鮮活。我們認識彼此的第三天,女孩說了四則鬼故事,她以各種方式遇見鬼。爾後,她的殭屍、她的鬼,有時指向我,有時是她強大力量的來源。直面人的陰影,小孩比大人更容易。
我也有泰雅族名,尖石養老部落長輩給的,Makao馬告。雙崎部落(Mihu)距離豐原三十分鐘路程,我每日順著河道往返,甜根子草佈滿大安溪,銀白紛飛,Mihu山丘小小的映在石岡水壩的湖裡和天空在一起。三十年前部落的詩人到豐原的小學任教,多年後我從豐原去部落,時間化成詩的養分。和瓦歷斯諾幹再遇見,是因為原住民文學營,瓦歷斯真的是瓦歷斯,再也不是體育老師。我去詩人的故鄉教一年級,偶然成為必然。
唸詩和畫畫在一起。有時想畫畫,我們就來唸詩。
一年級小孩,每日的生活行動像是夢遊,活在夢裡,如夢活著。小孩的存在本身就是夢。日常囈語,夢般奇幻飄渺,有些真實,有些想像。男孩如詩地對日子絮絮叨叨,沉浸在自己的小宇宙。充滿詩意的開頭,我馬上拿起筆,一面寫,一面問道「然後呢?」。果如其然,我們得到一首詩,與孩子對話,我獲得的更多。孩子用自己的話解釋詞,以生活情境開展詞的生命。有些詩句,是男孩定期喃喃自語,我順著他的時間流在旁抄錄,不同時間的三段植物呢喃,成為一首完整的詩。這一刻,詩完整了也可能再延續。
小孩對話的同時,我經常匆忙抓起紙張和筆,記下覆述又覆述的童音,無法確知下段對話但錯過此刻無法回追,而不斷探問皆是甜美。他們觀察我的舉止好一陣子。有天對看,然後笑著說「老師又要寫下來了!」。小孩一邊講話,我一邊撿拾。小孩所到之處都是詩,生活氣息成詩入歌,乾涸的土地注滿潤澤。話語飛走之前,我快筆寫下小孩腦中浮現的夢幻世界,我們浸泡在聲音的流動裡,小孩沉靜,我們的世界只有詩。
跳舞的聯絡簿,我跳舞著看,我唸著有音樂的句子,依著小小朋友的世界,想像的詩誕生。唸完陳黎的〈聽雨寫字〉,男孩從中擷取『消失』成為自己的詩句。他所在意的,他所用力的,在詩裡反映男孩生活的另一面,顯露他靦腆的內心。可是,當我唸谷川俊太郎的〈小鳥在天空消失的日子〉,低頭對著畫冊猛畫的男孩,突然抬起頭來說「我不會畫消失,這太難了。」。畫筆帶動他理解世界,而我理解了他。男孩喜歡畫的是恐龍和拿刀的小孩,任何詩的發展都會長成這樣,他對自己的畫作相當有自信。女孩偶有抗拒或者退縮,但學期末時,她也愛上畫畫,她盡情地畫城堡,小女孩的頭頂上都會有頂皇冠。
出版計畫是後來的事情,接近離別。回到最初,讀詩是延續我的閱讀習慣。無意之間唸詩唱歌成為教室班級經營的策略,穩定班級氣氛,雖然加上我只有三人,而這本來只會是我教學手札的一部分。我把詩作分享給友人,朋友詢問是哪名詩人的創作。無法辨識創作者的年齡,僅是七歲孩子的日常呢喃,小孩是天生的詩人呀,與詩共同生成,眼睛閃閃,生命透著光。徵詢小孩的意見,他們願意分享有趣的課堂日常:
想,
想給人家看,
我想和人家分享,他們會知道我們的事。
讓他們看到我們的ugi蟲蟲,還有大便蟲蟲,屁股蟲蟲。
圖和鬼要在書裡面。
小孩的詩能帶著我們看到不同的世界,讓他人和小孩的世界相逢。此事的確立和推進,同時把我帶向我的未來,和詩同在。
時隔五年,七歲的詩是一份成長禮物,禮讚當年的彼此。山裡的孩子,詩裡有山也有海,他們的小宇宙,即將和世界相遇。 Lokah!
註1:ugi泰雅語音譯,意指男性生殖器
註2:男孩和女孩表達出版意願的對話,指定此為第一首詩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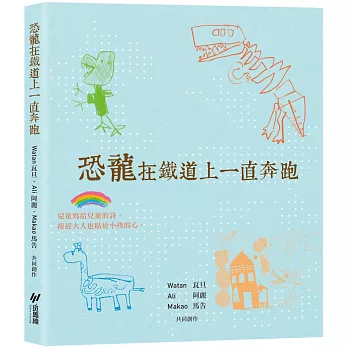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