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民國二十年秋,余膺國立北京大學史學系講座,開始撰寫講義兩種。一為近三百年學術史,一為秦漢史。越一年,秦漢史寫至王莽,近三百年學術史寫至李穆堂,皆未完編。自後乃專力撰寫學術史。二十二年秋,又開始講通史,計劃為通史編講義。而秦漢史一稿,遂竟擱置,未獲續成。二十六年,奔亡湘滇,秦漢史講義舊稿,亦未攜帶,蓋視同敝帚,不屑以自珍矣。
三十八年,再度奔亡來香港。越年冬,去臺北,北大舊同學張君基瑞來謁。談次,袖出秦漢史油印講義一冊。曰:此書於流離中常置行篋,迄今且二十年,吾師殆已忘棄。願為題數字,聊作紀念。因率題數行歸之。
四十年冬,重去臺北,越年春,清華舊同學陶君元珍來謁。談次,復及此稿。曰:昔在清華研究院,聽吾師講秦漢史,油印講義,尚留行篋中。此稿已越二十年,吾師曷不刊而布之,以惠學者。余曰:此稿未終編。即西漢一代,亦尚多重要節目,須續寫東漢時再牽連補及。且此稿歷二十年,始終未再加整理,當時編寫匆促,殆不足復存。陶君曰:不然。師此稿,實多創見。《國史大綱》論述秦漢,有語焉不詳,不如此稿之暢竭者。復多絕未提及者。此二十年來,雖不斷有關於秦漢史之著述問世,然師此稿所創見,實多並世學人所未及。且師此稿,其行文體裁,亦屬別創,堪為後來寫新史者作參考。著述行世,各有影響,何必一一求如精金美玉,絕無瑕疵,乃可刊布乎?越日,陶君持油印講義來,曰:以此相贈。師返港,可即付梓人也。乃余膺奇禍,幸得不死。秋返港,即創始屬草宋明理學概述。此稿插書架,未暇理會。友人某君見之,曰:暫借一讀,不日可歸。事隔有年,渾忘借者何人。遍詢相知,皆曰未借。則此稿雖在人世,固已杳如黃鶴,一去不復返矣。
四十五年夏,重去臺北,偶與北大舊同學數人談此事。或曰:張君基瑞有此稿,當囑其送來。越日,張君果攜來,赫然見舊題,乃頓憶前事。余笑曰:余於此稿,初不自珍惜。自陶君一本失去,乃若人面桃花,倍滋眷念。今重獲此本,真是自由天壤間惟一孤本矣。此亦二十五年前一番心血所注也。子當以此相贈,吾歸,必亟刊行之。張君曰:此固某等之所望也。然此本流竄相隨,越二十年,師付印後,盼仍保此原本見歸。余諾之。然為張君此一語,彌感於陶君有歉然。抑陶君所贈本,乃由清華油印,尚在此本之後,或於此本文字有異同,今亦漫不記省,無可再校核矣。
秋返港,乃始開卷細讀,恍如晤對二十餘年前故人,縱談秦漢間事,雖不能一一盡如我意,要之此君所言,如出我肺腑間,真所謂相視莫逆,心悅而解,其為快何如耶。因遂校其譌文,稍稍補申其語氣未足,而一仍其內容舊貫,以付梓人焉。
排字既竟,因備述付印經過,而復有一事,必鄭重告讀吾書者。蓋此書僅是一講義,備便講述。學者就吾所講,退而循誦馬班兩史,庶有窺乎秦漢兩代史跡之大概。即有精治馬班原史,涉獵吾書,亦足供討論鑽研之一助。若讀者嬾窺舊史,謂治吾書,即是讀秦漢史,此則吾罪滋甚,決非余刊行此稿之用意也。
中華民國四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錢穆自識於香港九龍鑽石山庽廬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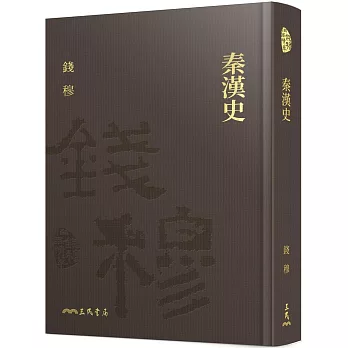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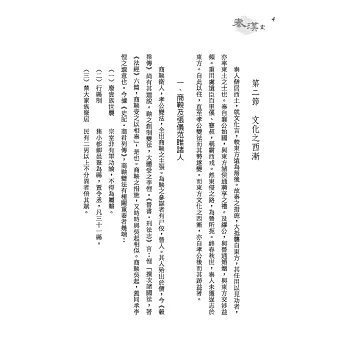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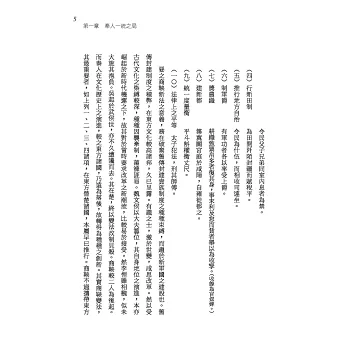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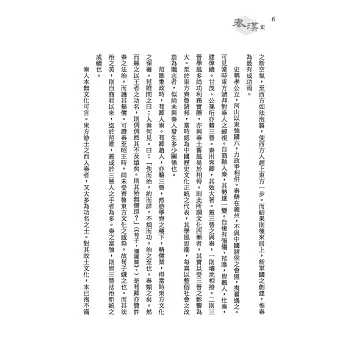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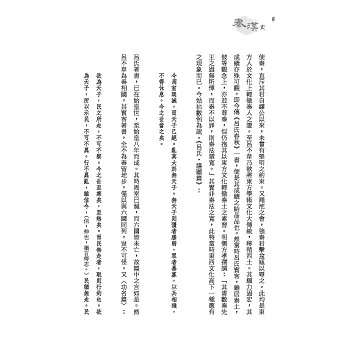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