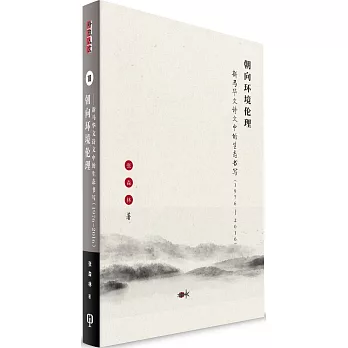序
超越人類中心主義—— 序張森林《朝向環境倫理:新馬華文詩文中的生態書寫(1976–2016)》
張松建 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博士生導師
生態問題與人類的歷史一樣悠久。但在古代社會和前現代時期,這個現象的廣度、深度和規模,並沒有達到一定的程度,尚未變成人類社會的結構性危機,所以沒有引起自覺廣泛的注意。近代以來,隨著科技進步、殖民主義的擴張、商業金融的發達、社會流動的頻繁、都市化進程的加劇、全球化和跨國資本主義的崛起,人類的生活方式從此發生了巨大的改變,這導致了生態問題的日趨嚴重。從西方到東方,從發達國家到第三世界,從北半球到南半球,生態危機無所不在。這引起了人類的高度重視,從觀念意識到公共政策,都出現許多變化。借助於文字、影像、聲音等手段,世界各國的知識分子對生態問題進行了強力的表現,在學術研究和文學藝術領域也出現了一些醒目的變化。
從1970年代以來,“生態批評”(ecocriticism)國際學術界有異軍突起之勢,相關的理論概念有綠色研究(The Green Studies)、綠色人文(Green Humanities)、環境倫理(Environmental Ethics)、自然史研究(Studies of Natural History)、自然書寫(Nature Writing),等等。這方面湧現出不少有代表性的論著,例如,Alfred W. Crosby的《生態帝國主義:歐洲的生物擴張,900–1900》,James C. McKusick的《綠色書寫:浪漫主義與生態學》,Scott Knickerbocker的《生態詩學:自然的語言,語言的自然》,Cheryll Glotfelty與Harold Formm合編的《生態批評讀本:文學生態學的里程碑》,Lawrence Coupe 編輯的《綠色研究讀本:從浪漫主義到生態批評》,Pierre Hadot的《伊西斯的面紗——自然的觀念史隨筆》,Glen A. Love的《實用生態批評:文學、生物學及環境》,Rachel Carson的《寂靜的春天》。數十年來,生態批評一躍而成為國際學術界的新寵,並且結合歷史學、地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生物學、文化研究、文學等各種知識源流,走向跨學科研究的方向。
根據生態批評的理論視野,我們回望世界文學史,就會發現一些習焉不察的文學現象展示了新含義。《瓦爾登湖》的作者、美國作家梭羅在當時籍籍無名,現在被公認為“生態書寫”的先驅之一。英國工業革命時代小說家狄更斯的作品——例如《霧都孤兒》《艱難時世》《孤星血淚》,描繪倫敦市環境污染的嚴重景象——也顯出生態書寫的明顯特徵。18世紀英國詩人約翰•克雷爾(John Clare, 1793–1864)醉心於英國鄉村風光的描寫,他的那些詩作如今被學者們重新研討,視之為生態書寫的典範;哈佛大學的著名文學批評家Helen Vendler還專門寫過一篇長文叫做〈綠色的詞語:約翰•克賴爾〉,向這位不幸的詩人表示敬意。美國作家Herman Melville的《白鯨》原來被當作海洋文學、航海小說的經典,現在也在生態文學的理論框架下得到重新闡釋。這些年來,我在從事教學和科研的過程中,接觸到不少東南亞、東亞的華語文學作品,其中就有大宗的生態書寫,例如新加坡的君紹、王潤華,馬國的吳岸、潘雨桐,臺灣的劉克襄、吳明益,中國大陸的遲子建、葦岸,無不展露出生態書寫的良苦用心。我曾試圖研究這個文學現象,惜乎由於手邊的科研任務太過繁重,只好廢然而止了。
2014年1月,張森林被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錄取為博士研究生,追隨我進行學術研究。關於博士論文的選題,他最初遞交的研究計劃書是“從愛國文學、建國文學到傷痕文學 —— 新加坡華文詩歌的本土意識演變(1957–2007)”。當時我覺得,這個題目已經勝義無多了,就建議他不妨考慮一下“生態書寫”的課題。森林是一個謙虛誠懇、從善如流的人,他愉快地答應了,又說他以前在這方面積累過不少資料,可以為進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礎,這讓我非常高興。後來,森林順利地通過了開題報告,修完學校規定的六門課而且取得了優異的成績,然後,他一邊在單位裡緊張忙碌地工作,一邊抽出時間寫作博士論文。出人意料的是,森林和其他的全職學生一樣,在短短四年內就拿到了博士學位。如今,我展讀這部修訂版的博士論文,想起森林在當年求學時的情形,往事歷歷在目,不免有些感慨。應該說,針對新馬文學生態書寫研究,本書並非著人先鞭,但是和此前的許多著述比較起來,本書有三大優點,值得一一說明。
其一是文本、歷史和理論的結合。我在學術研究中一直強調:不能把文本當作獨立自足的審美客體進行完全封閉的閱讀,而必須在文本細讀的基礎上,把文學現象進行理論化、概念化的處理,同時打開文本空間,不斷進行歷史化、脈絡化的解讀,旨在讓文本、理論和曆史形成一個三邊互動的辯證、開放的結構,展開多層次的張力對話,挖掘出文本的豐富性和複雜性,冀能出現一些批評性的、生產性的觀點。新馬華語文學中的生態書寫,貌似一個簡單的話題,其實涉及科技、商業、氣候、農林、醫學、政治等許多面向;所謂“生態現象”包括森林植被的破壞、河流湖泊的污染、動物死亡和物種滅絕、地表地質的損毀、流行疾病的傳播、惡劣氣候的出現,等等。森林既然研討這個課題,首先需要搜集大量的詩和散文作品,根據主題、題材進行編排歸類,進行深入細膩的解讀,讓關鍵性的問題慢慢浮現出它們的輪廓和蹤跡。單單是這個工作就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此外,為了掌握生態批評的學術動向,森林也在我的指導下,刻苦閱讀了中英文理論書籍,根據階級、種族、性別、國家作為敘述單元,從多個層面對生態書寫展開批評探索,所以,本書的一些章節顯示了跨學科研究的抱負。而且,森林也在行文當中巧妙融入了不少關於新馬、東南亞的社會—歷史資料,努力在區域、本土和全球的重疊語境中深入思考相關的主題。書中的章節設計得非常合理,它們彼此呼應,互相補充,深刻有力地闡述了一系列的重大問題,清晰透徹地顯示了森林的人文關懷。毫無疑問地,書中的不少篇幅未被前賢和時輩探討過,因此本書具有填補空白、增進知聞的的價值。例如,關於“光污染”的現象,關於瘧疾、沙斯、禽流感的文學再現,關於何乃健的轉基因農業實驗,關於陳蘭芝、高玉梅、李喜梅、張隆華、黃明恭、石君、夏心、朱海波、林川夫等華文作家的研究,關於新馬文學與生態女性主義,關於印尼“燒芭”的文學再現,此前從未進入學者們的研究視野。所以,森林捷足先登,算是這些問題的第一批思考者,他的扎實嚴謹的科研工作,大大地推進了這個領域的研究現狀。
其二是結合歷史記憶與社會現實,溝通文學作品與文化政治,兼顧人文關懷和公共政策。若干年前,在我研究王潤華詩的時候,就發現這位作家如何召喚歷史記憶、展開後殖民批評,他關於馬國的錫礦開採、橡膠種植園、豬籠草、萊佛士拓殖、植物園的精彩描寫,表達了他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嚴厲批判,這就是“生態帝國主義”的問題了。森林在這個方面的研究,踵事增華,更上一層樓。本書的研究時段從1976年延伸到2016年,既有殖民地時代的歷史想像也有21世紀的社會情形,兼顧歷史縱深和現實關懷。同時,森林不但在文學文化的框架內思考生態問題,他也在許多篇幅中處理了相關的社會議題,把兩方面成功結合起來,例如,關於傳染病的問題,關於印尼燒芭的問題,關於新加坡召喚樹權的公民意識,等等。此外,森林在人文關懷當中也補充了公共政策的制定,例如,他分析新加坡為植物園申請“非物質文化遺產”、新馬兩國政府的保育政策、新加坡河流的治理,等等,這些論述非常有說服力,使得本書的肌理綿密而豐厚。
其三是在地經驗和雙重身份。新馬文學,繁複多姿,生態書寫,茲事體大。但是森林研究這個課題還有其他一些有利條件。首先,他是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人,對於新馬和東南亞的生態問題有近距離的觀察。森林出生於1961年,是新加坡的建國歷程、城市化、現代化和全球化的見證人、知情人和參與者,他對本地的霧霾現象有切膚之痛,他經歷過2003年的沙斯風暴,他目睹了新加坡從甘榜到城市的飛速發展,所以,在地經驗對森林研究新馬文學具有重要意義,而這正是其他國家的學者所不具備的有利條件。其次,森林是勤奮用功的學者,他對百年新馬文學史如數家珍,他參編過不少文學作品選集,對相關的作家作品非常熟悉。再次,森林又是資深作家,他也在《十滅》等作品中思考過生態問題,感時憂國,令人動容。——以上這些綜合因素使得森林的研究避免了一些外國學者的常見缺點,而又突出了體貼入微的本土意識。
森林的求學道路比較曲折。他在初級學院畢業後,過早到社會上辛苦打拼,也培養了艱苦樸素、與人為善的品德。他在短短十年內,相繼拿到北京師範大學學士學位、新加坡國立大學碩士學位、南洋理工大學博士學位,真是“天道酬勤,功不唐捐”,“艱難困苦,玉汝于成”。如是,森林在“作家”的固有身份之外,又增添了“學者”的頭銜,成績如此驕人,令人刮目相看。現在,他的博士論文即將出版,出於師生之誼,他邀序於我,遂有我以上的閱讀感言。作為森林以前的導師,看到他取得的顯著成就,我深感欣慰,並表示祝賀!超越“人類中心主義”,宣導“星球倫理”,追求和諧世界、美麗家園,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的偉大夢想,在當前的危急形勢下,這個夢想顯得迷人而又迫切。所以,森林這本書的出版,可謂是應時當令,恰到好處;同時我也相信,讀者在終卷以後,一定會深有所獲。
2021年1月21日,序於星洲之停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