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馮冬
南隙詩集《果林夜話》誕生於明亮交錯的微縮地形,「我」,如小王子,坐在過小、多風的行星上,看著不遠處的星辰劃過那僅僅屬於一個人的夜空。偌大空間內,只有為數不多的「我們」陪伴著我,在這宇宙級的荒涼與孤寂中,我們試著生火做飯,相互照顧,講故事給對方聽,「互相借一些冷暖」。這從我到你,再返回至「一」之單獨狀態的時刻,這在我們之間循環的非閉合性時間,乃是世界敞開之原初機遇,也是詩人遊戲的場所,而那些或動人、或哀傷的生活場景,也正是詩人嘗試去理解、去棲居於這本質上與認識和感受並不合拍、甚或帶來傷害的世界。如此棲居嘗試,在南隙這裡,因其低於一般感知之語氣與色度,具有了「閾下」特徵。某些事物的碎片未經意識之整合就直接進入,如「雲影佈滿暗房」、「小學生在冷鋒中起飛」、「一個家庭推搡著擠進天空」等等陌異感知時刻,在此,意象脫離形象的凸顯,慢慢沉入背景。這向著暗處、向著基底、向著意識與物之交接地帶的喃喃低語以至喑啞無聲的決心,反而使南隙的詩句具有相當的辨識度,令他從眾多詩人中脫穎而出。
南隙的詩初讀如童話,然而越讀越像「黑童話」或「反童話」。正如藝術家夏卡爾將包括革命在內的各種現實持續浸沒入其畫作的童話夢境氛圍,南隙同樣把一切記憶與事件拋入一種看似童稚、卻可怕地真實的超現實語境——一個個微型爆炸。這些語言斷片透露出一個人最初遭遇世界時的驚恐,幼年之經驗;相較而言,成年人的日常經驗大多陳腐不堪,生活越是重複,遭遇也越為不可能,而孩童對痛苦和快樂更敏銳,孩子眼中的世界是常新的、時刻變化著的,離天國的福分更近。然而,南隙既剝離巨大的成年狀態之偽善無為,也向讀者表明,人在世必有所承擔,有所操勞,哪怕一日三餐,也暗含著食物的悲哀,也承受著難以下嚥或如鯁在喉之物,某種「非食物」的餵養。南隙很早就具備獨立的個體意識,一種智慧早熟的憂鬱語氣充滿詩篇。況且,與常人有異,詩人不僅承擔自己的生活,還要以童真之心去承擔整個世界,如神話裡的擎天神。「宇宙」詩化後進入日常,被納入城市、家庭、廚房,進入一個個具體化的情緒之中。
不難看出,南隙在此顛倒或改寫了童話的邏輯:幸福的允諾讓位於苦難的允諾,英雄主義讓位於反諷之英雄主義,天真之於經驗、善之於惡的精神勝利法讓位於一系列暗示性的非完整觀察,這在南隙稱之為「意象輯」(南隙是為數不多擅長營造不可複製之意象的漢語詩人之一)。以哲學家巴舍拉的方式,一切存在者,包括房子、器具、微縮之物、動植物,都有說話的權利,沒有哪一個聲音是壓倒性的,而這諸多客體之共同在場具現了巴舍拉所言的「內在浩瀚感」。南隙詩裡確有一種罕見的「物體的民主」,星星可以咬自己的籠子,屋頂的瓦片也可以沸騰,這些獲得生命與自主性的客體無疑極大地增加了「家庭」的範圍,而棲居也轉變成與萬物同在:「天地廣闊了/獨居就更難」。風雨雷電、地水火土等自然力量被詩人超自然地重新組合,與生命體感應,成為棲居的元件,而每一首詩都可讀作從某種「心的氣候」裡倖存。有時,星星離得比人更近,有時,一切飛入半空。童謠般語氣所透露的,乃是存在本身的臨時與巨大,以及世界自身的無目的性乃至多餘。對詩人來說,世界「太多」、「太大」。然而詭譎地,不可化約為意義的形體已四下出現,被抽離的東西又再次返回,而痛苦與快樂都時刻呼籲著自身的完滿,一切亟需重新講述。
越理性的人,往往越無法在理性中獲得安頓,他必尋求比理性更為猛烈且瘋狂之物。我讀南隙的詩,感到了內在的瘋狂,感到詩人欲出離「人性」而走向「它在」的慾望,這似源於理性在把握世界時想要僭越自身的那股衝動,如哲學家笛卡爾懷疑自己的身體可能是玻璃做的。南隙對哲學(康德、黑格爾)的一手閱讀,對辯證法之於生活的始終貫穿之領悟,再加上他對建築以及造型藝術的持久偏好,使他能夠以詞語構築一個個思緒與體驗的半透明殼,這既滿足了理性反觀自身的要求,也呼應了理性衝破自身的純粹而進入經驗領域,進入形而下乃至夢的領域的迫切慾望。一種可觸的、肉身化的辯證法瀰漫於整部詩集。哲學之於南隙,並非一種直接的寫作資源,而是勘察萬物之流變的那只眼,而同時,藝術又將這些流變形象化入諸多構型。可以說,哲學看穿了在世的幻覺,而藝術卻苦苦持守這幻覺,這特別的張力,從認識之盲點而來的觀看,使南隙詩作與同時代人的作品區別開來,也可見其不凡的才華。
真正的詩人如紅寶石一樣罕見,然而在公眾白晝般的目光中,他必然不可見,必然隱入暗處,惟在無人之處,他的詩句才會散發出異樣的光彩。我步入南隙的詩集,如步入另一個斑駁的記憶與生活,如握著一雙可與之交談的真實的手。
自序
寫一首詩是一件事,不斷地寫詩是另一件事,前者是構建,後者則更像在體驗一種解體——比如駕駛一輛逐漸散架的車,零件掉了一路,最後只剩一個人赤身露體,握著脫落的方向盤,用一雙肉腿奔跑——需要在乎的事情越來越少。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某種大道至簡、一切變得輕而易舉,寫詩仍然是件很難的事情,而且正在越變越難,這也是因為我們只能用身體奔跑,而肉身是脆弱的,會累,也會受傷。
概括這個集裡的東西是另一件很難的事情,因為它們不是某種原理、某種信念的演繹。勉強比喻的話,它就是一條道路,是那輛一邊前進一邊自行消解的車留下的一路殘片,或著蛞蝓爬過遺留的黏液―我赤腳去過很多地方,有的寒冷有的炎熱,有的柔軟有的堅硬,皮肉在哪裡受傷,哪裡就留下痕跡,我按自己的方式給這些地方一一起了名字,其中之一、我逗留得最久的一個地方,就是果林。
現在我也不在那裡了,也許以後我還會回去看看。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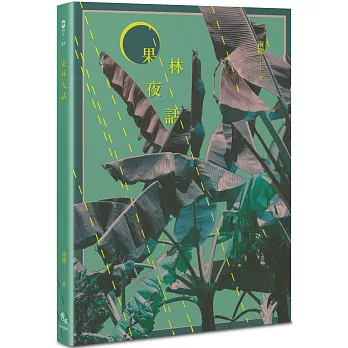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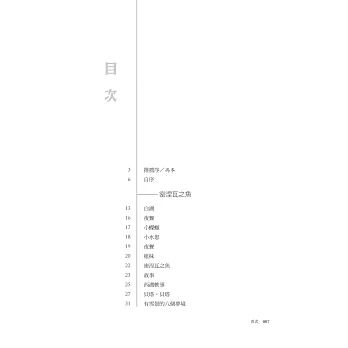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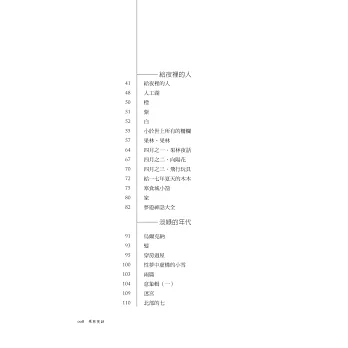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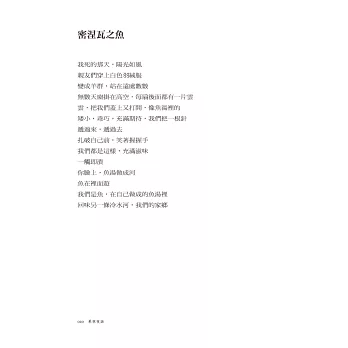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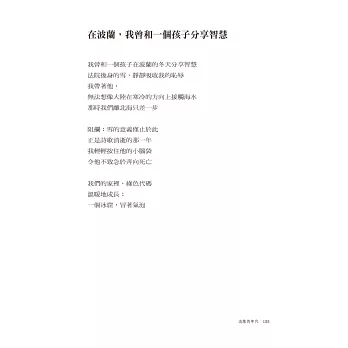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