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風中,尋覓,霧社事件的新書寫
李敏勇
歷史,他的故事,或她的故事。在事實與虛構之間,我常想起德國作家湯瑪斯.曼的《歌德與托爾斯泰》,兩位歐洲不同時代的作家,在巧妙的敍述𥚃相遇。日譯本序文,高橋孝義談歷史,説像是從考古的瓦片描繪已消失的過去。無論是History或Herstory,在性別意識之外,有更深沉的課題。湯瑪思.曼的歷史人物敍述被認為交織著文學與哲學的深度與力道。他的小說家之眼有深度的凝視。
霧社事件是歷史,是台灣的歷史,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台灣的歷史。戰後,國民黨中國類殖民統治台灣時期,以中國對視帝國時期的日本,霧社事件被操作為中國抗日丶反日的歷史,收取政治宣傳效果,強化或美化替伐的新殖民。歷史被賦予新統治者的進佔動機,忽略了人的精神,尤其是台灣原住民的精神。與吳鳯的虛構性教化正好相反的是,抗日的「虛構性中華民族主義」樣本。歷史被去歷史,而為政治權力所用,這是一個例子。
解嚴後,民主化,台灣逐漸鬆綁政治教條,霧社事件的歷史觀照和凝視,在文學和電影的面向展開多元的作者性。江冠明以報導文學與記録片工作者,呈現了他的視野,完成《跟著風往前走》的尋覓和刺探。七個篇章,從〈跟著風往前走〉到〈風的聲音〉,其間〈那是他自殺的地方〉、𡿨戰地日記〉、〈誰的歷史〉、〈遇見花岡一郎〉、〈奔向前方〉,正是他「不同筆調、思想、和文體」的敍述,兼及「報導、小説、散文」的形式風格,實現了他嘗試的某種意念書寫實驗、對歷史的另類詮釋和自由意念的創作。
霧社事件的歷史呈現了強烈的「人的圖像」:莫那魯道的家人們;花岡一郎和花岡二郎的命運;川中島餘生群落;太平洋戰爭時南洋參戰的高砂義勇軍。台灣歷史存留的某種悲劇原型,或說人性格局,在江冠明筆下隱含著尋覓自由真諦、生命情操的方向指針。帶有自我批評意識的書寫企圖觸及台灣民族性的反省,江冠明的鈙述不斷探照人物的格局、生命的意義。
島嶼的秋天之際,我拜讀江冠明從台東都蘭寄來的書稿,想起他在西部曾長期從事的報導、採訪以及紀錄片拍攝的那些年代,那些社會運動洶湧、政治抗爭頻繁的年代,想起他在東海岸的新生活,他的餐食料理和民宿成為某種書寫場域,在那裡他進行文學書寫文化生產。面向太平洋海域,以山嶺樹林為背景,他沉潛的人生,更深刻的歷史探索、社會觀照,更豐富的文學心靈,流露在他的書寫中。台灣的歷史觀照需要更多的文學性和文化性,需要真正的作家性。跟著風往前走,風中,尋覓,台灣歷史需要新的書寫,才能呈現精神的視野。《跟著風往前走》呈現江冠明的霧社事件新書寫,令人激賞。
推薦序
化謎成迷霧社事件
陳萬益
這是一部霧社事件的新文本。
冠明自序稱:原擬拍攝一部紀錄片,但是探訪過霧社事件的老人、古戰場、馬赫坡山的溪谷岩洞與川中島,閱讀了邱若龍、鄧相揚、台典泰雅族人的著作,從一九九○年代到新世紀漫長的時日後,醞釀出來的是「不同筆調、思想和文體」來敘述的七個章節,不能界定卻又兼具「報導、小說、散文」的詮釋文字。
霧社事件發生至今已超過九十年,事件的遠因近因、爭戰的腥風血雨、及其後慘絕人寰的自相殘殺、婦孺迫遷館至於川中島等等脈絡,即使經過日本帝國的封禁訊息,以及戰後國府以抗日為名立碑封神,在一團迷霧裡,也依稀顯現了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事蹟,尤其在解嚴以後,鄧相揚以長期的關注、親聆、與探查霧社泰雅族人在驚悸中殘存苟活的聲息,陸續完成了三部報導:《霧社事件》、《霧裡雲深》與《風中緋櫻》,更因其真實、深刻、感人,而促成電視劇集「風中緋櫻」和電影「賽德克巴萊」的攝製、放映,其轟動效應使霧社事件廣為社會各界所悉。
昔日的禁忌成為大眾的話題,壓抑與禁口終成眾聲的喧嘩:原來日本統治者採取「以夷制夷」的策略,使霧社部落群在脅迫下分化成「味方蕃」與「保護蕃」,「第二次霧社事件」的族人自相殘殺的夢靨,其間的恩怨糾葛,更烙印在泰雅族人的靈魂深處,在台灣民主化與言論自由氛圍下,族人終於無法忍受統治者帶偏見的詮釋,也無法接受和人隔靴搔癢的探看,從口述歷史到大字書寫,追求霧社事件的真相與主體性觀點,在這個立場下,不免批判前此的說法與定見,但是,這也就是冠明受霧社事件的題材吸引,卻又有諸多困惑,與面對爭議可能的困擾,而難以敘述的根本原因,其書寫的策略更不得不避開絕對的是非不辨,「從故事模糊地帶去發展一些可能的想像」。
霧社事件發生後半年,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就發表了新詩〈南國哀歌〉以詠嘆和激勵「我們山上的地主」(這是他對台灣民住民族的尊稱),開頭這樣寫:
所有的戰士已去,
只殘存些婦女小兒,
這天大的奇變!
誰敢說是起於一時。
人們所最珍重莫如生命,
未嘗有人敢自看輕,
這一舉會使種族滅亡,
在他們早就看明,
但終於覺悟地走向滅亡,
這原因就不容妄測。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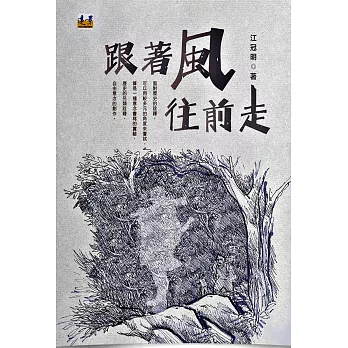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