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合境.平安
東海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潘怡帆
這幾年我的寫作開始朝向一種「自己」的建立,長久以來文學史料的爬梳,讓我意識到寫作不能不該,也不會只有「一種」。[...]《合境平安》處理的是我熟悉且寶愛的題目,一面賡續、裂變民俗敘事的模式,同時深化虛與實的技術。創作者一定要有自己的創作論。(《合境平安》,二五八)
《合境平安》結束在敘事者明白揭示的本作宗旨:通過賡續、裂變民俗敘事,深化虛與實的技術朝向「自己」的建立。然而,不強調坦誠相對卻充斥斷裂、丕變與虛實混淆將造就什麼樣的「自己」,或者,這是關於「自己」的觀念重新定義?朝向自己的寫作究竟該是白描,或總已自我重建而有別於原版?楊富閔的剖白甚至不寫在心照不宣說真話的後記裡,卻夾纏在深化虛實技術,強調文學多變,讀法多重的篇章之中。於是,作品最終揭曉的謎底蛻變為謎題,表面形構深淵,扣問著何謂創作者在創作論中生下的「自己」?那是《花甲男孩》、《我的媽媽欠栽培》、《故事書》等書的主題賦格,或由時間變奏孕育「物種起源」的差異系譜學?
馬塞爾.普魯斯特在《追憶似水年華》中創造了男主角馬塞爾;《合境平安》裡,一個名叫楊富閔的小孩在作品合境奔跑。他或駕單車沿溪流走勢晃盪,客廳廟口跑來跑去,尾隨開路鼓車、藝閣花車,或在流水的宴席中打游擊,搭乘父親的豐田追五王廟遶境,跟蹤索取銀兩的獅頭藝人,和土地公一起「拍無去」,隨大哥的馬自達在鹽分地帶兜圈再兜圈,給二爺騎車載到深山林內收驚……時而悠遊時而閃避,速度不等卻馬不停蹄的吋土踏遍,彷彿駐足便要生根纏繞,唯有拔地而起,全速奔跑才能護祐他寶愛的鄉境平安。
楊富閔不只一種年紀或順時長大,他的小學時代在逝去後總會再度光臨。三十幾的博士生穿過教會廟會轉眼便跑回「羊蹄甲發得好美」的小學春天校慶。「時間永遠是不固定」,楊富閔以寫作回憶,忽大縮小的身體與年紀縮脹出愛麗絲夢遊奇境。時間線相互吞食,前行其實是倒退。丙子、己卯、丁丑歲次跳接卻輪番鬧熱,像鞭炮一場炸過一場。丙子年開竅的小學生「眼睛漸漸看得清卻又看得更不清」,在即將登場的廟會前領受時間焦慮。天人交戰於迷人的夜間宋江操練與八點檔《第一世家》的追劇,短短五分鐘的廣告時間切換於神明爭鬥與人間條件,來回奔跑於連結二重空間的蟲洞。騷動的村子,連荒廢的白牆都布滿遶境塗鴉。廟會的終點是全村接龍的流水席,小學生騎單車挨家視察,「騎到最後也是最遠一顆平安紅燈籠的放光之處,騎到農曆三月的曾文溪河床地。那是鄉境的最外邊。告誡自己不可以再過去了,再過去就是興建之中、飛沙走石的福爾摩沙高速公路了。」
歡騰開場卻結束於「告誡自己不可以再過去了」,〈歲次丙子的鬧熱〉種下惘惘的威脅隨即兌現成〈歲次己卯的鬧熱〉中的事件。未來的寫作者在回首凝望甫從小學畢業的自己,道出盛大慶中大家還不知道的事:「己卯年這科香極盛大。從農曆年後喧鬧至端午節前,大家津津樂道長達數月。緊接而來九月的大地震與年底的曾祖母謝世。」開場所預告的終局為鬧熱的遶境蒙上陰影。草地裡的「羊戶閔」趕著長大,「我在趕路,我們全家都在趕進度,前方隊伍行過三個路口,二十世紀就要結束」;對於事後通過寫作回看的成人楊富閔,時間在前行中後退:「我的小學畢業,以及曾祖母的過世,全在對我倒數」。書寫搖擺於時間的兩端糾結成「前未來式」(futur antérieur)暴露了將臨的壞毀。儘管過程尚未知曉,事件全局尚無從浮現,然而,超前佈署的生離死別像白晃晃的刀,亮著口子,等在終點,再歡快的安排都隱隱作痛。
前行與倒退的雙向時間使楊富閔的敘事從純粹過去中脫軌,表面上是往日時光中的天真孩童,也順應相同的時序,知覺同一份經歷,實則開始總已是重新開始。伊索寓言的夏日蚱蜢盡情高歌是無知於冬日將臨的未來,嚴冬將攜同死亡一起抵定牠的悲劇。命運在末日揭曉,縱使震驚卻也無暇掙扎,畢竟受苦僅侷限於散場一瞬,眨眼就過。然而無盡痛楚無非源於預知未來卻無力煞停,睜睜看著命運直奔終局,蚱蜢的手舞足蹈與僵死,一目重瞳,痛快都不那麼痛快。
被預警的宿命未至卻先發,既一派天真又已千瘡百孔,合境走踏的羊戶閔摺疊著回首寫作的楊富閔,大街鑽小巷的尋鬧熱與迂迴避道「覓相找」,記憶在重溫中滋生新意故道犁深,敘事開始時亦總已重複開始。開始未知開始,唯獨結局現身才重識了事件不可見的開端,因而開始從(開始)結束後開始。唯有繞經〈歲次己卯的鬧熱〉才能重新領悟前篇〈歲次丙子的鬧熱〉裡宋江陣的熱血沸騰與技藝傳承將在三年後的增補新血中暴露人口的外移、老化與凋零。楊富閔字裡行間喧騰著各種鬧熱場所,將臨的秘密同樣如影隨形:「己卯遶境的香科,曾祖母還健在」。轟鬧鬧的親族闖入曾祖母的眠夢,遠方的高空煙火秀在沒有未來的時光裡竭力盛開,校準離別的走向。遶境隔日,離鄉的宋江陣少年北返回到工作崗位,急轉的速度直奔敘事終點。
楊富閔把死亡搶說在離別之前,先寫姑婆哭到肝腸寸斷,接近哀號,「而我站在騎樓看她從遠方匍匐而來,傻在原地不知如何應對,任由眼淚無端汨汨在流」,最終收束於青年離鄉打拼的鏡頭:「放我狠狠去飛,有事沒事,不要回頭」。兩種交織的離開,使死別歧義為離鄉,「送葬與遶境隊伍同時交錯大馬路上,我身陷其中不停脫隊又不停跟上前去」。語意錯綜,不要回頭是為了飛翔,謝世即刻跳接匍匐歸來,死亡不是終點反而使敘事活跳跳地進場。於是曾祖母不會真正離去,只是狠飛,「一支隊伍交錯另一支隊伍。一支隊伍長出另一支隊伍」,藏於時序顛倒裡的盼望茁壯成新敘事的枝椏,寫作調度了新生的事件現場。
寫作扭轉有所本的回憶成為推陳出新的未來,像〈晴天霹靂方法學〉裡提到「故事要風要雨,說風是雨,早就全都由你決定」。跟在己卯遶境後的敘事從世紀末前往/退回一九九七年的〈歲次丁丑的鬧熱〉,時間反摺,翻頁悲傷,「倒帶重新回到剛剛經過三合院的那顆鏡頭,仔仔細細,再看一遍,這次我就突然發現站在牆邊的母親,以及踩在盆栽,雙手撐在紅磚牆垣的自己」。楊富閔把自己從小學畢業寫回四年級生,「我的路線絕對呈現奇怪的迴路,看不出到底要去哪裡」。從已定案的過去不定向地往無從預料的寫作未來偏航,一九九七年的小學生鑽進人牆與回鄉參拜的台北市長握手一瞬,時間前未來式地再度馳向遠方,「這位市長幾年之後將會爬得更高,這個庄頭將會湧進更多民眾」。孩童與政治家掌心交貼裡湧現出言說創造的二重先兆,羊戶閔歡天喜地的回家炫耀,「不知為何大家全都相信了,他們又沒看到」,未曾親睹卻相信話語凸顯了口述的悖論,表面率真,實則勾勒著敘事創建的可能世界。《合境平安》於是並非小學生活(過去)的白描寫作或創作者(現在)的成長回顧,時態前馳後奔的寫作搭建了獨一無二的作品時空,像〈香條通告表〉層層疊疊重複拼貼,既預告著將臨的廟會亦記錄著眾神到此一遊,新舊香條斑駁錯落在通告版上,布置出嶄新的時間聚落,形構了絕無僅有的諸神交手與對話。
作品時空任由寫作者安置時序,小學生羊戶閔與寫作者楊富閔不斷更迭獻聲,單一敘事時空就此破局,多重音頻對剪對接。一九九九年的〈聖誕樹王公〉揭開作品序幕,印記著此繁茂宇宙的秩序法則,多年後的楊富閔隔岸觀火看自己遭遇卡片分配的困難,寫在卡紙上的Merry Christmas總會漏掉很多字母,彷彿當年的語言留下空缺,待日後差異時間裡的重說才能補綴鑲嵌成完整的祈福故事線。「這麼寫著、想著,我的腦袋清晰,思路更加通透」,寫作並非為了再現而是要長成一些新的人物與另一種思想,就像從七等生的〈老婦人〉裡長出楊富閔的〈談天的香客〉。楊富閔的寫作不只為了懷念或定格,因此有著〈藝閣花車〉裡愈看愈年輕的仙女姐姐。思想變貌讓停滯的過去如活水湧現,一個新觀點已然展開世界。
〈歲次己卯的鬧熱〉中過世的曾祖母將於〈重逢平安橋〉再度回歸,她在〈兒童戲:麻將紙美感練習〉給孩子們比手畫腳討麻將紙糊牆,在〈兒童戲:辣芒果成年禮〉持續發派過年紅包。「當時健在的人瑞」與「她是不是隨時會死?」仍會在恍惚間躍出,中斷笑到歪戈七剉的孩童遊戲,喚醒已知悉的預知死亡紀事。然而,接續的日常描述會繼續懸擱死亡,像突發奇想卻隨即散去的疑問、似曾相識卻遙遠的夢境,或那張曾祖母盯看了許久卻什麼都沒有的茶褐色麻將紙。死亡、離鄉、歸來與在地,這些曾被差異撕裂的兩地相隔在《合境平安》重新安置,形構了莫比烏斯環走不盡的同一直線,只要繼續前進就能退回故土所在。然而這裡不是麻豆,亦非府城,而是在敘事無盡變貌中生生不息的《合境平安》。於是,楊富閔說:
寫作是逆天的事業。我還在寫。寫作是我的對抗。(《合境平安》,二五九)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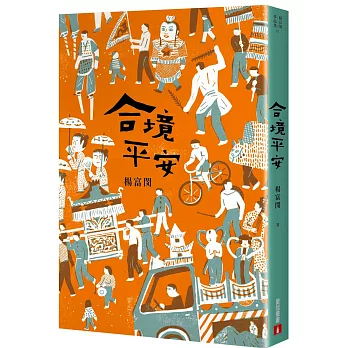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