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曾經用三個「業」字來歸納人一生奮鬥的三個階段,那就是學業、事業、德業。年輕時攻學業,壯年時闖事業,老年時修德業。老舍寫過一篇小說《我這一輩子》—我今年八十三歲了,可以說是「一輩子」了。這三個階段我發展得都不好,都欠缺,都有遺憾。有些開了頭停了,沒有堅持下去;有些限於個人稟賦,堅持下去也有限,事實上是警覺到有限才沒有堅持的。
曾經,我常對年輕朋友說一番話。好幾次,走到街上,對面來人大聲叫我:「王主編,王主編,你還認識我嗎?我是某某。你的一段話影響了我一生。你說過﹃世界上最大的悲劇是幸運之神敲你的門的時候,你還沒有準備好,沒有立刻跟他上馬。幸運之神沒有等人的耐心,他撥馬而奔,永不再來!﹄你這段話令我受益匪淺,影響了我一輩子。」的確,我鼓勵別人行,鼓勵自己不行,一直上不去。
到了我這個年齡,覺得世界上最大的悲劇,其實是沒有完成自己。記得楊牧詩中有一個句子,大意是:在維也納郊外的墓園裏,躺著一個完成了的海頓。是啊,完成了的海頓!弘一法師用「花枝春滿,天心月圓」來形容完成的感覺,最為貼切。是啊,完成很重要。而我就是一個沒有完成的人。周夢蝶完成了,商禽完成了,朱西甯完成了。海音大姐、潘人木、張秀亞、琦君、蘇雪林等等都完成了。我羡慕,我佩服。
余光中先生把我的生命內容依份量之輕重,分作四部分:詩作、編輯、評論、劇藝。余先生說,瘂弦寫詩,是揚己之才;編報刊,是成人之美,不但鼓勵名家、發掘新秀,而且培植繼任的後輩;評論則以研究新詩發展、為人作序為主;劇藝則以從事廣播事業、主演《國父傳》聞名。余先生並以〈天鵝上岸,選手改行〉為題,專文分析我的詩藝,頗多溢美之詞。我很感激老友的鼓勵、稱讚,愧不敢當。
我的詩實在是寫得太少。詩的創作是嬌嫩的藝術,不能停,停了就接不上了。世界上停筆最久的、最有名的詩人要算法國的保羅•瓦雷里(Paul Valery 1871—1945),梁宗岱譯作梵樂希。他二十一歲停止寫詩,沉默了二十五年後才重新出發,文學史上稱為「沉默之聲」。我停筆的時間超過了梵樂希。火山的休眠是為了再一次的爆發,人稱睡火山,睡火山會醒來,睡得太久,就是死火山了。詩人維持正常的寫作發表狀態,批評家和讀者並不作特別的觀察;停了太久再寫,就有人從新作中尋找停筆休耕的理由。停筆就是停筆,不寫就是不寫,哪有什麼理由?花枝春未滿,天心月未圓的我,就表白到這裏。詩友文朋、傳播界的老友們,知我諒我。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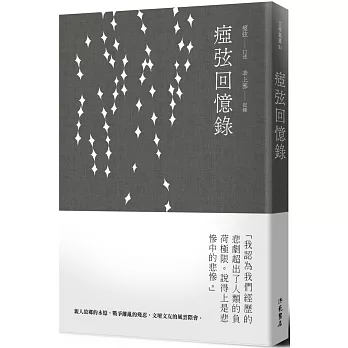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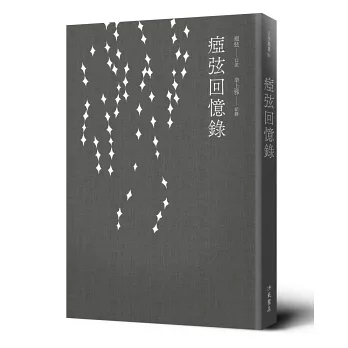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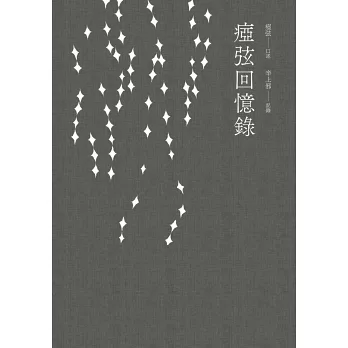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