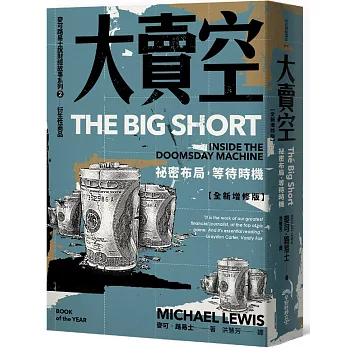前言
當莊家誤判賠率,快抓緊機會
直到今天我仍然沒搞懂,為什麼華爾街的投資銀行願意付我好幾十萬美元年薪,讓我為別人提供投資建議。
那一年,我才二十四歲,沒半點經驗,對於猜測哪支股票或債券會漲或會跌,也不是特別感興趣。
華爾街的基本功能,是分配資金──決定誰該獲得資金、誰不應該。我說我對金融投資毫無概念是真的,沒蓋你。我沒修過會計課,沒開過公司,甚至沒有積蓄可以理財,卻在一九八五年誤打誤撞地進了所羅門兄弟公司(Salomon Brothers),三年後的一九八八年又莫名其妙地賺了一大桶金後辭職。
雖然我已經把這段經歷寫成書,但這一切還是讓我覺得非常荒謬──荒謬也許是在華爾街那麼容易撈錢的原因之一。但我感覺這種荒謬情況不可能持久,很快就會有人看穿,發現很多同業和我一樣都在瞎掰,我們很快就會遭到「報應」,到時華爾街會覺醒,成千上萬個像我一樣拿別人的錢豪賭,或是遊說別人砸錢豪賭的年輕人,都會被踢出金融界。
老千騙局中,年輕人要懂得見好就收
當我坐下來,把自己這段經歷寫成《老千騙局》(早安財經出版)時,我是抱著一種「年輕人要見好就收」的心情。我就像隨手寫下一張紙條,塞進瓶子裡,好讓在遙遠未來踏上這一行的人也能看到。我心想,除非有局內人把這一切寫出來,否則未來不會有人相信真的發生過這種事。
過去,關於華爾街的文章主要談的都是股市。因為從一開始,股市就是華爾街多數人賴以維生的地方。不過這本書要談的是債市,因為現在華爾街靠著包裝、販售及胡搞美國越來越多的債務,賺進了更多鈔票。同樣的,我也覺得這種情況無法持久。
我當時打定主意要寫的是八○年代的美國,一個為錢失心瘋的金融國度。我以為讀者看到所羅門兄弟執行長約翰.古弗蘭(John Gutfreund)在一九八六年把公司搞垮後,居然還能拿到三百一十萬美元時,會非常震驚。我以為霍伊.魯賓(Howie Rubin)的故事(所羅門的抵押債券交易員,轉戰美林後馬上虧空了兩億五千萬美元),會讓大家覺得不可思議。我以為讀者看到當年的華爾街執行長對債券交易員涉入的複雜風險一無所知時,會大吃一驚。我大致上是那麼想的。
但我沒想到,讀者在回顧這些事或讀到我的特殊經歷時,竟然會覺得「有意思」。我真是太天真了。
我完全沒料到,一九八○年代金融界這些怪象,後來居然延續了長達二十多年。我也沒想到,華爾街和一般人之間的差異之大,儼然成了兩個不同世界。我沒想到當一個年薪高達四千七百萬美元的債券交易員,還會覺得自己被占便宜。我沒想到所羅門兄弟交易室發明的抵押債券市場,在當時看似一個好主意,後來卻造成史上的金融慘劇。我更沒想到,在霍伊.魯賓賠了兩億五千萬美元而成為家喻戶曉的醜聞人物之後,又過了二十年,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另一個也叫霍伊的傢伙,會以單筆抵押債券交易賠掉九十億美元,而且除了摩根士丹利內部一小撮人聽過他的作為或動機,外界一無所知。
同學們,別理高盛,勇敢航向大海吧!
我寫《老千騙局》時,除了想講述一個在我看來很不可思議的故事之外,並沒有什麼遠大目的。如果你灌我幾杯酒,然後問我希望那本書對世界帶來什麼影響,我可能會說:「希望大學生們可以讀一讀,明白一個簡單道理:為了擠進金融業而放棄對其他事情的熱情,或是假裝對金融有興趣,都是愚蠢的。」我希望俄亥俄州立大學某個想成為海洋學家的聰明孩子在讀過我的書以後,可以不理會高盛(Goldman Sachs)的錄取通知,堅定地航向大海。
但不知怎的,讀者似乎感受不到我要傳達的訊息。《老千騙局》出版六個月後,我收到俄亥俄州立大學雪片般飛來的信件,學生們竟然爭相問我:還有沒有更多華爾街祕辛可以分享?原來,他們把《老千騙局》當成了一本「華爾街生存實戰手冊」來讀。
離開華爾街的二十年間,我一直在等待當年預期的華爾街末日到來。然而,儘管金融體系一再爆出問題──高到離譜的紅利、多不勝數的囂張交易員、讓德崇證券(Drexel Burnham)崩解破產的醜聞、擊垮古弗蘭和所羅門兄弟的醜聞、我前老闆約翰.梅韋瑟(John Meriwether)的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虧損所引發的危機,還有網路股泡沫……,處於危機中心的華爾街大銀行卻仍持續壯大。他們聘請二十六歲的年輕人,做一些對社會沒什麼明顯效益的事,然後付給他們越來越高的薪水。美國年輕人不再質疑這樣的金錢文化,畢竟,當你可以把上一代打拚出來的事業買下,再一一分割出售,又何需費心去顛覆它呢?
於是,我也放棄、不再等待了,我心想,沒有什麼醜聞或逆轉可以大到足以拖垮整個金融體系。
想像一下,這些爛資產在跳樓大拍賣時值多少錢
然後梅瑞迪斯.惠特妮(Meredith Whitney)出現了。原本,惠特妮在不起眼的奧本海默金融公司(Oppenheimer and Co.)擔任不起眼的金融業分析師,但在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以後,她再也不是不起眼的無名小卒了。那一天,她預測花旗集團的經營糟到必須大砍股利,否則就會破產。
通常在股市裡,我們不會知道到底是什麼原因影響了當天行情,但我們可以非常確定在十月三十一日那天,是惠特妮讓金融股大崩盤。當天交易結束時,一個基本上沒人聽過、大家都認為籍籍無名的女子,讓花旗股價大跌八%,讓美國股市的市值蒸發了三千九百億美元。四天後,花旗執行長查克.普林斯(Chuck Prince)辭職。兩週後,花旗大砍股利。
從那時起,惠特妮突然變成了賀頓(E. F. Hutton,知名美國券商,該公司著名廣告金句是:「賀頓一開口,大家乖乖聽。」)——她一開口,大家真的就乖乖聽她說。
她要傳達的訊息簡單明確:如果你想知道這些華爾街銀行的真正價值,只要嚴格檢視他們用借來的錢所持有的爛資產,想像一下這些爛資產在跳樓大拍賣時可以值多少錢。
在她看來,這些銀行內所聚集的高薪人才,根本毫無價值。二○○八年一整年,每當有銀行或券商宣稱問題已獲解決(例如提撥了壞帳、增資等等)時,她都會毫不留情的反擊:不,你們還沒坦承自己把銀行搞得多糟,還沒承認你們在次貸債券上虧損了數十億美元,你們的股價就像你們的存在價值一樣虛幻。
有些同業批評惠特妮譁眾取寵,網路上有人說她只是瞎貓碰到死耗子。但不可否認的,她說的大抵上沒錯,只不過有些事情她應該是猜的。因為她不可能知道華爾街銀行內部發生哪些事,也不會知道他們在次貸市場中真正虧損的程度──畢竟連銀行執行長自己都不清楚,更何況是她。「真相要不是我說的那樣,就是他們都在說謊,」她說:「不過,我覺得他們其實搞不清楚狀況。」
如今看來,顯然搞垮華爾街的不是惠特妮。她不過是以最明確、最響亮的方式表達看法,只是沒想到她的看法所帶來的衝擊,竟然比查緝華爾街弊案的紐約檢察長更強大。
當然,如果光是醜聞就能擊垮華爾街的大型投資銀行,這些銀行老早就消失了。其實惠特妮並不是說華爾街銀行家們如何貪腐,而是說他們很蠢。這些人的工作是幫別人管理及分配資產,但顯然他們連怎麼管理自己的資金都不懂。
放馬後炮容易,但你敢不敢當別人眼中的神經病?
我承認,我曾經想過:要是當年我繼續待在金融業,這種災難搞不好就是我掀起的。因為造成花旗亂象的核心要角,就是當初我在所羅門兄弟的同事,其中幾位還跟我一起上過培訓課。
後來我實在忍不住,決定打通電話給惠特妮。那是二○○八年三月,就在貝爾斯登(Bear Stearns)倒閉之前,當時還不知道金融風暴將會如何收場。但如果她是對的,這一回也許真是重新整頓金融界的好時機。我除了想知道她的看法,也很想知道這位壓垮股市的年輕女子來自何方。
惠特妮是一九九四年從布朗大學英文系畢業後,進了華爾街。「我來到紐約,連這裡有研究部這種單位都不知道。」她後來在奧本海默公司找到工作,運氣又特別好,碰到一位不可多得的恩師,不僅帶她入行,也打開了她的視野。惠特妮說,這位恩師是史提夫.艾斯曼(Steve Eisman)。「我發表對花旗的看法後,最開心的就是接到艾斯曼的電話。」她說:「他告訴我,他以我為榮。」
當時我沒聽過艾斯曼這號人物,所以也沒多想,但後來我看到一則新聞,提到一名鮮為人知的紐約避險基金經理人約翰.保爾森(John Paulson),為他的避險基金賺進約兩百億美金,也為他自己賺了近四十億美元。從來沒有人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從華爾街賺進那麼多錢。他靠的,正是放空次貸債券,而花旗及其他華爾街大型投資銀行,正是被這種債券拖垮的。
華爾街投資銀行就像拉斯維加斯的賭場莊家,賠率是他們決定的。和他們對玩零和遊戲的玩家,偶爾會贏個一局,但從來不可能連贏好幾局,也不可能贏到搞垮莊家。但保爾森這位玩家,和惠特妮一樣看見了金融業者無能的一面,發現這些莊家嚴重誤判賭局的賠率。
我後來又打了一次電話給惠特妮,問她知不知道有什麼人預見了次貸風暴、預先押注,海撈了一票?有沒有人在莊家驚覺事態不妙以前,就發現了贏得賭局的竅門?有沒有人在這個現代金融黑盒子裡,看出了它的缺陷?
當時是二○○八年底,很多事後諸葛聲稱自己早就知道災難會發生,但其實真正預見危機的人並不多,有勇氣砸下資金的更是少之又少。要能跳脫市場的集體歇斯底里、明白財經新聞大都是錯的、看清多數金融界重要人物不是在說謊就是被蒙蔽……並不容易,而且通常,你還會被視為神經病。
惠特妮立刻給了我六、七個名字,大都是她曾親自提供建議的投資者。保爾森的大名,就在名單之中。
名單上排第一位的,是艾斯曼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