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文集編輯序言
余英時先生是當代最重要的中國史學者,也是對於華人世界思想與文化影響深遠的知識人。
余先生一生著作無數,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與文化史,對中國史學研究有極為開創性的貢獻,作品每每別開生面,引發廣泛的迴響與討論。除了學術論著外,他更撰寫大量文章,針對當代政治、社會與文化議題發表意見。
一九七六年九月,聯經出版了余先生的《歷史與思想》,這是余先生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也開啟了余先生與聯經此後深厚的關係。往後四十多年間,從《歷史與思想》到他的最後一本學術專書《論天人之際》,余先生在聯經一共出版了十二部作品。
余先生過世之後,聯經開始著手規劃「余英時文集」出版事宜,將余先生過去在台灣尚未集結出版的文章,編成十六種書目,再加上原本的十二部作品,總計共二十八種,總字數超過四百五十萬字。這個數字展現了余先生旺盛的創作力,從中也可看見余先生一生思想發展的軌跡,以及他開闊的視野、精深的學問,與多面向的關懷。
文集中的書目分為四大類。第一類是余先生的學術論著,除了過去在聯經出版的十二部作品外,此次新增兩冊《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與現代史篇,收錄了余先生尚未集結出版之單篇論文,包括不同時期發表之中英文文章,以及應邀為辛亥革命、戊戌變法、五四運動等重要歷史議題撰寫的反思或訪談。《我的治學經驗》則是余先生畢生讀書、治學的經驗談。
其次,則是余先生的社會關懷,包括他多年來撰寫的時事評論(《時論集》),以及他擔任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期間,對於華人世界政治局勢所做的評析(《政論集》)。其中,他針對當代中國的政治及其領導人多有鍼砭,對於香港與台灣的情勢以及民主政治的未來,也提出其觀察與見解。
余先生除了是位知識淵博的學者,同時也是位溫暖而慷慨的友人和長者。文集中也反映余先生生活交遊的一面。如《書信選》與《詩存》呈現余先生與師長、友朋的魚雁往返、詩文唱和,從中既展現了他的人格本色,也可看出其思想脈絡。《序文集》是他應各方請託而完成的作品,《雜文集》則蒐羅不少余先生為同輩學人撰寫的追憶文章,也記錄他與文化和出版界的交往。
文集的另一重點,是收錄了余先生二十多歲,居住於香港期間的著作,包括六冊專書,以及發表於報章雜誌上的各類文章(《香港時代文集》)。這七冊文集的寫作年代集中於一九五○年代前半,見證了一位自由主義者的青年時代,也是余先生一生澎湃思想的起點。
本次文集的編輯過程,獲得許多專家學者的協助,其中,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與中央警察大學李顯裕教授,分別提供手中蒐集的大量相關資料,為文集的成形奠定重要基礎。
最後,本次文集的出版,要特別感謝余夫人陳淑平女士的支持,她並慨然捐出余先生所有在聯經出版著作的版稅,委由聯經成立「余英時人文著作出版獎助基金」,用於獎助出版人文領域之學術論著,代表了余英時、陳淑平夫婦期勉下一代學人的美意,也期待能夠延續余先生對於人文學術研究的偉大貢獻。
序
本書所收的幾篇論文有一個共同之點,即都是討論文化問題的。前面幾篇是討論文化原理的部分,曾在「文明論」的總題目之下分別發表在《人生》雜誌上。關於文化哲學方面,我曾擬定了十幾個子目,準備陸續寫成一部分量較重的東西。可是由於我個人學力之所限,對於一些自己還沒有考慮成熟的問題便不敢遽下斷語,故有些觀念雖已在我的腦海裡盤桓甚久,我仍然沒有勇氣隨便寫出來。還有一些事實上的困難也值得談一談;首先是我自從入新亞研究所以後,主要的精神都集中在中國社會史的研究方面,一般寫作的工夫自然減少得多了,尤其是文化哲學所牽涉的範圍太廣,一個問題之提出至少要有相當時間的準備,這在我也是很難做到的,所以往往要隔一兩個月才能寫成一篇。其次是參考書的缺乏。以往討論文化哲學的人多偏重於「哲學」與「精神」方面,故不免有武斷不合歷史事實之處。在近代學者中祇有湯因比(Arnold Toynbee)、達尼列夫斯基(N. I. Danilevsky)、克羅伯(Alfred L. Kroeber)、素羅金(Sorokin)等少數人是例外。我想文化哲學如果真要成立一門踏實的學問則不能不建築在科學研究的基礎之上,而關於文化研究的最大科學成果則當推新興的「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他如社會心理學(Social Psychology)、社會學……等亦占重要的地位。而我個人對於這些學問卻都是門外漢。益以香港書籍之缺乏,更使我有「力不從心」之感,有時雖有一點見地也因為缺乏材料而無法動筆。在這種種困難之下,本書所收的一些論文實在是簡陋得不成樣子。我祇希望將來能有機會看到更多的書籍時再修正與補充已寫的論文,並繼續草成懸而未寫的子目。所以我最後決定將此書定名為《文明論衡》第一集,以示初引端緒之意,而且將來若再有這一類文字,亦可繼續出第二、第三……等集。這是希望讀者們諒解的。
附錄所收的幾篇論文可以說是前幾篇原理的實際運用,而且都是和近代中國文化及其與西方文化如何求配合諸問題有關,雖語多空泛而實經反覆思維所得,讀者閱此數篇將更能瞭解前幾篇的涵義所在。作者近年來思想態度上有所改變,全書力求兼容並包與融會貫通,而無取於「罷黜百家」之狹隘胸襟。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一方面是開創的,一方面又是集大成的,這兩種性質都祇有在一種極其廣闊的精神中才能表現出來—渺小的靈魂是承擔不起偉大的時代責任的。作者於此真是「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因此,縱使本書毫無知識上的價值,這一點繼往開來的心願也還希望能獲得讀者們的同情與支持!
余英時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五日 於香港新亞研究所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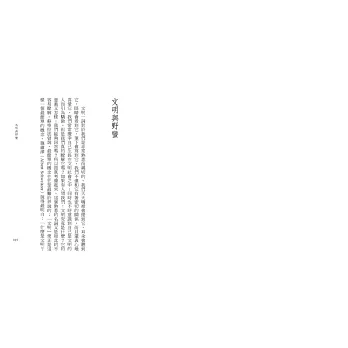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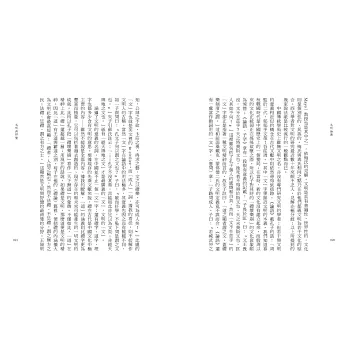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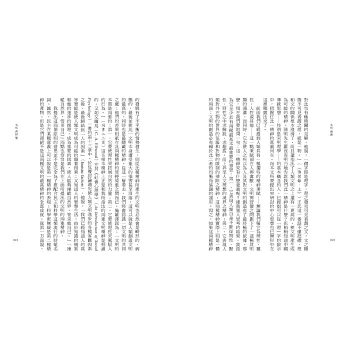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