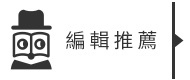序言
當我和穆戈成為密友、見識過她許多作品後,再看到《瘋人說》——一個我完全沒料到的,力發千鈞的敘事系統,我會想:她這就敢處理這麼深刻的命題了嗎?她已經能操作如此複雜的劇情了嗎?
如果你也試圖做講故事的人,就會明白這背後的考量。
人人都有講故事的願望,但大多數人都止於零碎的片段,或模模糊糊地描述出自己腦中的印象。不是因為大家缺乏什麼,恐怕這就是「故事」的原生形態。所謂的天賦之能,不是上天將豐沛曲折的情節化作一張精妙的地圖展開在誰的眼前那樣,沒有那種「老天爺賞飯」,講故事的天賦與才能是傾盡努力積攢、搭建素材,完成持久高效作業的功率和動能。
一個能把故事講得複雜精細的人,是無論如何都能窮思竭慮找到出路,卻並不滿足於此,進而再將路繞成迷宮繼續給自己走的人。一個能把故事講得龐雜宏大的人,是個有起重愛好的人,他操控著的巨型鏟斗就是要一籮筐一籮筐地吃泥沙,挖得深、裝得滿才能讓他產生安全感。在這個意義上,我知曉她的天才,既不玄乎,又不可多得。
我腦中的穆戈只長了張大嘴。我這麼說並不是因為沒見過真人——她雖屬於「蛙系」長相,但嘴並不大。我腦中的她是個無需眼睛鼻子的卡通人,有一張嘴巴用來大笑,再把塵世間的喜怒哀懼吸進去大口咀嚼,足夠了。她是個能量極強的人。初識她時,她早年身處一片混沌中的經歷已讓我足夠吃驚。那種感覺,就好像眼看著一個矮矮的小女孩安靜又狂熱地暴食。我會想:這也是你能吃下的嗎?這也是你能消化的嗎?
因為,就在她書中所寫的這段時期,我眼看著她把自己的生活過得千頭萬緒、一團亂麻。她,每天都像開著破冰船在航行。當時,我是那個在她耳邊吹風,提醒她「你明明知道怎麼更容易」的人。我甚至還煽情地說:我知道你或許習慣了承受重壓、力挽狂瀾,但過去你是不得已的,現在你已經有給自己規劃出更輕鬆生活的選擇權,為什麼要麻木於簡單模式,而去走一條更難的路呢?
這種話一出,我的心頭忽然盈滿了憐愛和感動。但如果讓我再說一遍,我必不會操著同情的口吻。我應當說:她,就是很強。就算讓她平穩地過日子,她也會拿這股跌宕勁兒寫小說。
我在此與大家溝通,是萬萬不想讀者朋友們沉浸在精彩的故事中便忘記寫作者的才能,一方面,本就該重視她個人的技藝:故事好看是因為她寫得好,她還將寫得更好;另一方面,雖然這些故事都有嚴肅的真實背景,但它們並不是照搬生活。描述精神病症的作品會更令人處在焦灼的境地。看到這樣的作品,我們比往常更想知道,這個故事是真的還是假的?有多少是真的,又有多少是假的?如果這個詭異而深刻的故事是真的,那麼,我是不是又往世界的未知黑暗裡前進了一步——我知道前方會發生什麼,下次若是迎面撞上,是不是就不至於那麼慌張?我能不能拿這些故事來衡量身邊的人和我自己?
也許你能在這本書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但值得明確的是,這本書是穆戈以現實案例為基礎,輔以心理學知識和藝術加工的手法寫作而成。她塑造了如男護士小栗子、催眠大師韓依依、心理學大拿齊素這些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大膽觸摸原生家庭、校園暴力等社會問題,重新審視精神疾病和社會的聯繫。我想,這些故事最震撼人心的地方,不是治癒疾病的過程,而是揭露病因。
穆戈是一名心理學碩士,也確實曾是精神衛生中心的從業者,但當得知她的這些故事會被一些讀者賦予心理學科普意義,我最初還有些擔心。但當我仔細看過全文後,我的判斷是,她已盡力負責。書中素材沒有胡編亂造,徵引的學說毫不含糊,每一則故事的心理學脈絡都是真實可信的,為了情節完備而補充的部分也盡力遵照科學。另外還有一些明顯是製造戲劇衝突的手法,我想沒有誰要以此來質疑全書的可信程度。
我們自然不希望書裡的內容被當作學習或私自診斷的材料,儘管所有的科普性表述她都負責任地傳達,為説明理解,還根據故事和病症製作了通俗易懂的病歷,但心理學以及精神病學的研究成果幾乎無一不是片面的、沒有定論的;我們也不希望故事裡的戲劇衝突讓過於在意真實性的您變得不信任這些故事,真的有渴望死在美裡、又擔心自己死狀不美的藝術家;真的有可以為了母親的哀傷而扮演一隻小動物的小女孩;真的有鑽研了一輩子精神病學、卻恨不得取消這個殘酷學科的大教授。援引我親耳聽過的一句話——來自一位鑽研了一輩子精神病學的大教授——「現在,全世界都觸到了精神病學的瓶頸」。
當DSM(《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診斷標準從第一版到第五版納入越來越多疾病,有些疾病之間的區分度越來越低;當諸如抑鬱症的一些常見病症的診斷範圍在默默擴大;當正念療法、積極心理學等佔據了顯要位置,比起傳統的治療來說更能得到大眾信任……凡此種種,都像在對高傲苛刻的精神病學施以反叛和嘲笑:你真的以為自己很懂嗎?你以為我們一定要接受你的挑剔,才能解決自身的問題嗎?
我第一次深刻地認識到,精神病診斷標準只是一定結構內的社會規範,是當我在中產者的世界裡浸淫過一番後再回到農村的家鄉,我發現,那裡的患病率遠遠高於一線城市,而人們不以為奇,甚至不以為病。你可以悲觀地說,這表明精神疾病的本質是貧窮和掙扎。但說實話,那一下子,我感到世界特別開闊,心裡特別輕鬆。
我也曾痛苦於我來自一個異樣的家庭,好像我們「怪物」在正常人中格格不入,可那天我忽然明白了,我們就是我們那個世界的普通人,而另一個世界更為嚴格的標準,是為了將大家整理得都不那麼麻煩,以達到高效生產生活的要求。這種標準雖有它的好處,但畢竟不是自然的公理。
最有趣也最深沉的,即是這最後一點。書中的齊素是穆戈本人某方面觀念的戲劇性外化。而這個觀念,不僅毫不偏頗,甚至可以說十分前沿。要說這是什麼,可以從最底層的認知說起。當你去和一個你以為最缺乏知識結構的人聊起心理學,他可能會不屑一顧,覺得所謂的心理治療根本就是糊弄人的、啥也治不了。說一個人有這病那病也是嚇唬人的,「照你這麼說,誰沒病」。
剛進入這個學科不久的學習者可能不會對此反感,因為他們剛嘗到給「變態心理」分門別類的快樂,他們說得出每一條判斷都是有依據的,令人感到充實的知識都是前人智慧的結晶。但是,只要他們一直往前走,恐怕會驗證到,那些無知者看似粗暴的判斷,幾乎是對的。
這就是我所理解的,齊素說,疾病來自社會與關係。以及謝必的悲劇,表面上看很像現下流行的「輿論暴力」,實質上也是個人與環境的對抗。但是,這個人真的沒什麼問題,無病更無罪。如果可以的話,希望你向上走、向下走、向外走,在你身邊解決不了的問題,可能在別處就會得到解決,甚至變得不再是問題。只有當你留在原有的不適的社會關係中,又感到痛苦,你才需要治療。治療也不是因為你有問題,只是為了幫助你在不那麼痛苦的狀態下,保住你現有的生活和你自己。
穆戈寫這本書,投入了很高濃度的對人類的愛與熱誠,好多次看到書中小實習生莽撞又俐落的質問,我仿佛看到了她本人在我面前眼含熱淚地發出「天問」。從這熱切的初衷裡,我祝願你看完此書,收穫的是自由,因為壓迫本沒有意義。而另一面,從她精心結撰的作品裡,祝願你收穫閱讀的快樂,因為故事本身很精彩。
本文作者為書中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