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孤兒俄羅斯為歐洲人充當人肉盾牌、
卻被歐洲人視為亞洲蠻夷的一部辛酸史?
俄羅斯「壞就壞在地理上」?
地理這個「殘酷無情的後母」,
是拖住俄羅斯邁向歐洲之腿的元兇,
還是促成它成為歐亞帝國的功臣?
一個在後面苦追的次生文明,
想「成為歐洲」而不能,想逃離「亞洲」而不得!
「靈魂分裂」的俄羅斯
在烏克蘭戰爭中再次凸顯出其文明困境!
一個延伸到遠東的綿延不絕的開放邊疆,既是俄羅斯成為歐亞帝國的原因,同時也是它無法融入歐洲的關鍵。巨大的邊疆、蒙古人的征服、來自拜占庭帝國的法統,使羅斯大地這塊「次生文明」,搖擺於歐洲和亞洲之間、掙扎在自由和專制之間、被不斷形成的新的上層結構與下層結構的矛盾和衝突所撕裂。
而二○二二年二月發生、至今仍舊進行中的烏克蘭戰爭,既是專制和自由、正義和邪惡的較量,也是深層和古老的文明史力量的推動。要解釋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這三個羅斯國家的複雜歷史,以及它們和立陶宛、波蘭等波羅的海國家之間的文明分野,就要先回到「羅斯」這個地理概念的形成及其憲制演化的歷史。
■俄羅斯一開始便攜帶歐洲文明的基因!而莫斯科的誕生改寫了一切!
在由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為主構成的「羅斯大地」上,古典羅斯的核心是烏克蘭,即從波羅的海沿著第聶伯河往南抵達黑海這條水上商業路線。今天的烏克蘭首都基輔是最古老的羅斯城邦,它的誕生是瑞典王公保護這條商業路線的結果,可以說烏克蘭自古便攜帶歐洲文明的基因。
然而莫斯科這個邊陲小邦的誕生,打破了基輔羅斯和歐洲的聯繫!在地理上,這歸因於處在東北方向的莫斯科擁有向亞洲開放邊疆拓殖的誘惑。結果,西北方向通往波羅的海的歐洲,東北方向通往亞洲大陸的邊疆,就形成了羅斯世界政治結構中的兩種極端類型:一種是基輔和諾夫哥羅德型,由上層貴族和商人集團控制的市民議會掌握最高權力,一種是莫斯科型,由拓殖草原森林的軍役貴族所依附的大公掌握專制權力。
「諾夫哥羅德人是半個歐洲人,半個德國人,半個立陶宛人,是羅斯世界通向歐洲的紐帶;而莫斯科人是半個韃靼人,半個芬蘭人,半個穆斯林,是羅斯世界通向歐亞大草原和東方各國的紐帶。」這兩種極端類型構成了羅斯世界的永恆母題,使它成為搖擺於歐洲和亞洲之間的靈魂分裂的國家。
■來自蒙古和拜占庭的「亞洲元素」,既是俄羅斯強大的根本,也是它最大的詛咒?
有兩股來自亞洲的勢力深刻影響了羅斯世界之後的演變。一股來自蒙古,一股來自拜占庭帝國(東羅馬)。蒙古的征服瓦解了以基輔為主的舊羅斯世界,而莫斯科以成為蒙古代理人、又背叛蒙古的不光彩形象而崛起,成為羅斯世界的暴發戶。
這也意味著羅斯世界被分成兩半:依附於蒙古的、以莫斯科為核心的亞洲一半,以及依附於立陶宛的、以其他商業城邦自治形式為核心的歐洲一半(相當於今天斯摩棱斯克以西的半個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烏克蘭的絕大部分)。
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迎娶流亡的東羅馬公主,讓莫斯科得以在政治上繼承東羅馬帝國的法統,以所謂的「第三羅馬」自居。如果它沒有繼承東羅馬的法統,那麼莫斯科公國的地位還不如立陶宛大公國,更永遠比不上跟法國和德國,然而新引入的拜占庭上層結構則使得莫斯科更加自外於歐洲。俄羅斯最大的痛苦就是永遠無法成為歐洲!
■上半身是歐洲人,下半身是斯拉夫人?
西歐派(上層)VS 斯拉夫派(下層)的糾葛與對立
作為妥協而誕生的羅曼諾夫王朝,是經過混亂、分裂後的俄羅斯重新出發、全面追求歐洲化的新時代。俄羅斯跳過波蘭,直接從西歐輸入技術和思想。從彼得大帝到凱薩琳大帝,俄羅斯上層貴族和知識分子越來越像歐洲人;拿破崙戰爭以後,俄羅斯的國家威望和利益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峰。
然而西歐化同時強化了沙皇的專制,聖彼得堡的歐化建立在針對俄羅斯廣袤內地的殖民之上。農奴制度的出現,意味著下層的東正教社會與上層的歐化階級再度分裂。
「十九世紀的俄國自由主義者和立憲民主黨人認的祖先是基輔羅斯,他們要把俄羅斯人變成歐洲人。沙皇本人,至少莫斯科的沙皇,認的是拜占庭,他們要做羅馬和君士坦丁堡之後的第三羅馬。而歐亞主義者認的是蒙古帝國。俄羅斯的大一統性並不來自於歐洲,甚至並不來自於拜占庭,而是來自於蒙古帝國。」
這些辯論幽靈般纏住了俄羅斯人的思考。「我到底是俄羅斯人還是歐洲人,還是兩者都是」,「俄羅斯是既非歐洲、又非亞洲的一個單獨的世界」。這些深層疑問,通過托爾斯泰和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寫作,通過自由派和三位一體專制主義者的衝突,通過西歐派和斯拉夫派的衝突,深刻地撕裂了俄羅斯社會。
■烏克蘭的民族發明被蘇聯凍結在一九一八年,戰爭之火能夠解凍嗎?
俄羅斯帝國晚期推行的地方自治實驗和陪審制,在憲制意義上是繼續「成為歐洲」。在為歐洲式的立憲君主制做準備的同時,也必然產生了一系列民族發明: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喬治亞、烏克蘭、白羅斯等。
但是,一戰的出現和布爾什維克的成功逆襲,以及列寧式的極權國家出現,把這些正在展開的歐洲式民族國家發明狀態一刀斬斷。蘇聯像一個巨大的冰箱一樣,把俄羅斯帝國內的各民族凍結在一九一八年。一九九○年代蘇聯解體後,這些被凍結的民族重新回到一九一八年之前,分別產生自己的民族國家,如白俄羅斯、烏克蘭和波羅的海三國等。這是普丁政權不願承認、卻沒有辦法抗拒的歷史。
從這個角度看,烏克蘭戰爭是三十年前蘇聯解體的巨輪、碾過羅斯大地後尚未消失的歷史塵埃。而從整個羅斯世界的文明和憲制演變來看,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再一次證明莫斯科成為歐洲而不能,逃離亞洲而不得的歷史困境。
本書是劉仲敬關於「文明和憲制」的系列講稿之一,作者的切入角度非常獨到,避開了一般常見的傳統政治史的寫法,比如熱衷於描寫王朝的興衰、沙皇等宮廷上層政治人物的故事,而是逆轉讀者對文明的認知,從地理、社會組織結構、憲制演化的角度解讀「羅斯大地」的歷史和政治演變。
從文明和憲制的角度看俄羅斯,它是一種次生文明,其歷史演化無法擺脫被地理牽制的宿命,而不得不變成靈魂分裂的國家。而莫斯科偏好用專制的形式,來解決其上下層階級和東西方文化的結構性矛盾,否則就會造成地理的分裂!這種模式,似乎變成了俄羅斯的宿命,成為歐洲而不能,逃離亞洲而不得,在進退維谷中維持一個橫跨歐亞的專制帝國的運作,這就是俄羅斯帝國在人類文明史中所扮演的獨特角色。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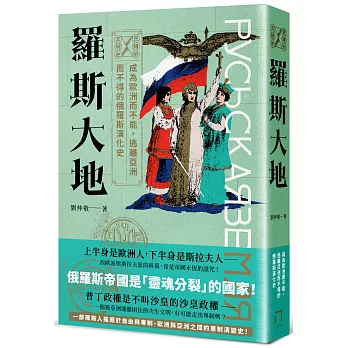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