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你可曾看過一大片雲朵,像粉筆一樣刷白了遠方的地平線?一縷縷的水氣是一條條的直線,朝著地面不斷下降。那一大片半透明的簾幕,是一綹綹懸吊的觸鬚,每一根都還來不及碰觸到堅實的地面,就已從液體蒸發為氣體。
有人說,那是天上的水母。
我說,那是悲傷。
我上一次看見這種氣象異象,是在二〇一九年四月,外子逝世十個月之後。我站在倫敦東南區的屋頂停車場上,眺望著鐵軌,遠方瓷片般的天空那銳利的尖端,出現大理石紋般一條條鴿灰色的線條,吸引了我的目光。我一時沉溺在這些奇詭的彎曲線條,這些逐漸碎裂的指尖,正好呼應我內心那些移動的幻影。一再變形的天際線,一如我的孀居生涯的朦朧輪廓。就像那個週六午後的天空,有水滴,有汙漬,有曲線,有條紋,最後蒸發成氣體。看上去像是消失了,其實完全沒有消失,只是從一種狀態轉化為另一種。
這次在停車場上演的悲傷顯現記,並不是我第一次為了鑽研內心的悲傷,而走入大自然。我的人生在二〇一八年天翻地覆,當時我投向火、水、土、風這些大自然的四大元素,才得以理解內心那些狂亂的感覺。刺痛皮膚的炙熱火焰,還有皮膚之下翻騰不息的海浪。在我肢體四周相互纏繞的樹根,還有拔地而起的強風,刺穿了我,纏亂我的頭髮。
大自然的四大元素有時讓人難以承受。在我剛失去另一半的那段日子,我繞著住家附近的公園行走,四大元素相伴在側,往往是在雨中步行,雨點輕輕打在雨傘上,啪啪作響,有一種安心的感覺。到了夜晚,我在客廳壁爐堆起細細的火柴,看著芥黃色、杏黃色的的搖曳火舌,一路劈啪膨脹成暗紅色的熊熊怒火。
在他離我而去的第一個冬季,凌晨三點的星光之下,我難以成眠,風吹過庭園中銀白色樺樹的樹葉的聲音給了我慰藉。樹根與樹枝。循環與移動。我窗外的世界窸窣作響。我的家變成一個時空膠囊,時時提醒我失去了什麼,於是我常常在清晨時分,在家中四處晃蕩,拿起我先生的毛衣,把臉埋進有小絨球的衣袖,祈求他能跟我說話。
我無論走到哪裡,都看見他的身影。書架上擺得整整齊齊的,那一本本飽經滄桑的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作品。塞在冰箱深處的一罐罐健力士啤酒。隨意扔在水槽邊的牙刷。夾雜在洗淨的我的衣物中,已洗淨的他的衣物:舊襪子、他很喜歡的上衣、褪色的牛仔褲。東一件,西一件不起眼的物品,就像陰森的犯罪現場,見證了過往,陳列著一段共享的人生,一條流失的性命。我的悲傷漂浮著,浮標四散在周圍,就在這間屋子裡流動。這是我們生活的屋子,是我們心愛的屋子,如今卻冷清到讓人無法忍受,一大片陌生的黑暗。
我的故事從這裡開始,在我先生於安寧機構的病床上逝世的幾天之後,我在天崩地裂過後的斷垣殘壁中夢遊,置身在陰影與過往生活佔據的陌生境地。清醒終究不敵半夢半醒的幻覺,以及不請自來的記憶。畢竟要到夜晚,他溫和的身影才會顯露。我在半夢半醒之間,感覺他確實短暫回到我身邊,彷彿天上有一個通道,能讓置身在兩個世界的我倆重聚。也許真是這樣,真能重聚,只是很短暫。但魔法是短暫的幻覺。所有的咒語終究會破滅。幾週累積成幾月,四季不斷更替,地球默默轉動。我感覺內心泛起漣漪,有個聲音一再叫我重新出發,一再對我說,不能因為悲傷而停擺。但這些感覺也流露出過往,時而拉著我往前看,時而帶著我回頭望,我漸漸脫離那個我所認得的三十五歲女人,那個曾經的我。
我好想往前走,卻又害怕放下。就在這矛盾的當下,死亡將我一分為二,製造出兩個我,在白晝與黑夜,舞動著,爭吵著。
我先生死於腦部腫瘤「神經膠質母細胞瘤」(glioblastoma)之後的十二個月,很多人問我那是什麼感覺,愛是什麼感覺、悲傷是什麼感覺、失去又是什麼感覺。這些人就像看見撞成一團廢鐵的汽車,好奇到把頭伸進破碎的擋風玻璃內一探究竟,還要叫車子裡面垂著頭的駕駛,指出身上哪個地方會痛。疼痛是不可或缺的,我們感覺到疼痛,才會知道自己受傷,也才能避免再受傷,但疼痛也很難量化。「失去」沒有所謂的芮氏規模。你從一種極端情緒衝向另一種,也沒有一種測量工具,能告訴你每天走了多遠。與你的心相連的那一顆心不再跳動,你又豈能感受到自己的心跳。
我在二〇一八年冬季開始寫作,直接面對悲傷的醜陋面,但我繼續寫作,是為了吸收這些醜陋面。唯有如此,我才能控制內心經歷的種種。一種強烈的變化在我體內上演,似乎把我從固體變為液體,再變為氣體。在尋常的日子裡,我推著推車走過超市走道,跑下地鐵的電扶梯,趕著上班去,在家附近的餐廳排隊,等著外帶咖啡,這種變化就在一天之內發生。
沒人告訴過我,原來悲傷能掌控你的潛意識,無情侵入你的身體,顛覆你的靈魂。在我先生剛去世的那段日子裡,我在斷垣殘壁中,拚命找尋他的身影。但久而久之,我開始向內追尋,不再尋找身旁少了什麼,而是尋找內心的巨大缺口。也許正因如此,我才會轉而向鰥寡寫作者、科學家,以及學術書籍求助,想平息內心批判的聲音。那聲音對我說,我不該這樣哀痛。當時的我在尋找答案,想驗證從未有人對我說過的道理。
一個下著雨的午後,我在倫敦的衛爾康圖書館(Wellcome Library),身旁全是醫學書籍。我從書上看見美國原住民婦女的故事。美國亞利桑納州西北部的霍皮族(Hopi Tribe)遺孀,喪夫之痛始終難以化解,竟會同時產生幻覺,看見亡夫的身影。我在書上也看到,海豚會伴隨另一半的屍體數日,自己不吃也不睡。大象會一再回到伴侶的遺體旁。我也得知「哀傷的鵝」失去另一半之後,會離開群體獨自生活,體重也會減輕。我讀到這一段,不知怎的竟感到安慰。
我幾乎被法律文書淹沒,全是些例行的政府作業,似乎把他的死亡變成一件很尋常、很正常的事情。我躲進神話故事,逃離現實。遙遠的王國拽著我離開現實。在精靈居住的魔法國度,有會說話的河流,沒有雙手的少女,還有嗥叫的母狼。野獸不能說話,只能嗥叫。一朵染血的嬌弱白玫瑰。哥德式散文編織瘋狂的世界,彷彿蜘蛛的大網環繞著我。我後來才知道,這些故事並未帶我逃離現實。作家安潔拉‧卡特(Angela Carter)曾說,神話故事是「描寫過往的科幻小說」,是「熊與流星的國度」。也許這就是我如此熱中的原因。我步入虛構的世界,幻想將我所失去的送還給我,野獸的象徵讓我回歸那份愛,重返那種震驚。我看過越多神話故事,就越明白這些虛構的奇異故事,全都述說著死亡。我用黑色馬克筆填寫喪葬表格,死亡是我唯一有感的敘事。於是我自己飾演沒有雙手,躺在病床尾端的少女。我也是染血的白玫瑰。我還是母狼,嗥叫著,看著嗎啡將他帶走,離我好遠好遠,前往熊與流星的遙遠國度。
但是,住在倫敦東南區,那位三十五歲遺孀的真實人生故事又是什麼?這可比較難找。我在書架上拚命尋找她的蹤跡,心想這位善良的半人半神,可能躲在字裡行間的空白。但我沒找到。我身心殘缺,難以度日,又找不到可供參考的論述,只能訴諸唯一的辦法:寫作。我無法言語,想說的話在我體內狂跳。我在記事本、日記本上書寫、使用筆記應用程式、在餐巾上隨意寫上幾筆,也在丟棄的信封上塗鴉,述說自己的故事。我在家中到處儲藏片段的記憶,唯恐遺忘。一個版本的我留下神秘的線索,讓另一個版本的我去尋找。接下來的幾個月,我變成一個行走的時代謬誤,在內心與逝去的丈夫交談,模擬日常互動。悲傷可以把一個人分裂成幾個形體,這些形體有時還能隔著時空溝通。從很多方面來看,這本書紀錄了不同型態的我:妻子與遺孀、目擊者與報導者。曾經的我,未來的我。
如果要追求的目標,是徹底脫胎換骨,那我想哀痛已將我變成探索者。我的故事似乎與我小時候愛聽的那些,能讓想像力盡情奔馳的超現實睡前故事有關:穿透鏡子的愛麗絲、桃樂絲與她的便鞋,還有露西走入塵灰滿布的衣櫥,前往納尼亞王國。這些虛構人物千里迢迢前往遙遠的國度,得到珍貴的寶物,才終於踏上回家的路。我的黃磚路帶領著我,從安達盧西亞的崎嶇山峰,到墨西哥太平洋沿岸的惡水。冬去春來,我度過了沒有先生在身邊的第一年,走向戶外的深處,愛上野性原始的森林,千變萬化的天空。我在高聳的榆樹、窸窣作響的樹葉下漫步,感覺到腳下的地面,也找到內心的話語。於是我打開空白筆記本,開始寫作。
我的孀居人生,對我來說是全新的體驗,但放在遙遠的國度來看,我希望能帶給別人一些關於離開與回歸的啟發。一種神秘的迴路,帶領我們找回自己。我們難道不是在人生的某個階段,都曾突然落入某種「森林」?我們累積了那麼些閱歷,還不是想從那些榆樹之下,挖掘出一些無形的東西?想挖掘出逝去的感受、破碎的關係、更年輕的自己?誰都曾經漫無目的晃蕩,沉浸在過往的歲月,想找出熟悉的映象、值得努力的未來,以及契合心境的論述。你還在尋找嗎?我也是,這本書就是明證。把地圖燒掉吧。這是失落,是一種非存在的狀態,由希望推動著向前,是一種即使身陷創傷與絕望的深淵,依然旺盛的強烈感覺。
從這個角度想,也許我的故事也可以是你的故事。如果說哀悼亡夫的第一年,給了我什麼啟示,那就是大自然的四大元素無所不在。只要我們願意接受新的可能性,遲早都會有不願失落的東西。我希望我的故事,能帶給曾經跟我一樣,瘋狂在書架上尋找自己的年輕遺孀一些安慰。但我也有一些話,想跟承受過重大失落的人分享。他們失去的也許是他們所相信的,他們冒險得來的,或是他們所愛的。這種失落讓一切變得好陌生,也讓人聯想到失落的英文字loss起初在日耳曼語的意義:解開、分開、分割。
也許死亡是最大的擾亂,最終極的失落,永遠改變了往後的人生。但這並不代表你不能重新塑造你的人生。在我孀居人生的第一年,我看著我過往的人生溶解、冒泡,從一種狀態變為另一種,有時又回歸原本的狀態。我寫在這本書的文字,並不見得會在你的人生一一上演。我們都是化學反應。四大元素也在我體內發揮作用。就連我寫下這段文字的時候,也不斷在改變。
到底會變成什麼樣子?我到現在還在思考。這種創傷後恢復的實體過程,在科學上叫做「創傷癒合」,但即使奇蹟似地重新生長,也不會是原來的樣子。傷痕永遠留存,忠實呈現受傷的經過。我藉助文字的力量,說出我的故事。文字就像天上一簇簇的燦爛星斗,帶領我走出幽暗的森林。
凌晨三點的星光下,是文字的力量為我續命。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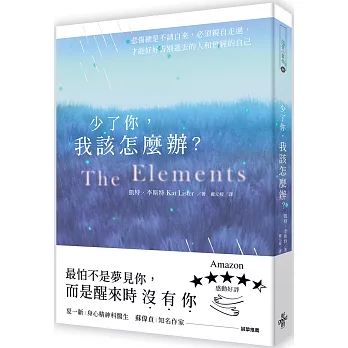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