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為什麼要學習觀看?
汪正翔 攝影創作者
觀看這件事如今成為一種顯學,我們看到許許多多教人觀看的書籍或是課程,然而觀看為什麼如此重要?
「觀看」可以區分為三種層次:第一種是vision,關注視覺在生物機制的層面;第二種是visibility,關注視覺的文化層面,譬如什麼樣的社會風俗之中,讓我們可以看見或不可以看見某些影像;第三種是visuality,這是法國思想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景觀社會》(LaSociété du spectacle)當中提出的概念,它關注景觀背後所潛藏的資本主義與國家權力的邏輯。後面兩者對於我們尤為重要,因為即使我們沒有看過《景觀社會》,我們也能夠理解在一個圖像氾濫的時代,學習觀看有助於我們理解這個社會,這也是為什麼約翰‧伯格(John Berger)的《觀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始終如此暢銷,他其實不是教我們如何看藝術,而是教我們看藝術背後的脈絡,而後者消除了我們對於藝術神祕的恐懼,也增加了我們對於社會、歷史與文化的理解。
反過來說,vision 的討論對於一般大眾相對陌生,即便視覺科學近年來有長足的發展,但是它在視覺藝術的應用仍然有待努力,更不用說成為一般大眾觀看時可以使用的手段。這一方面是因為vision 的領域過於專門,但另一方面潛藏的原因是,關注生物視覺機制被視為帶有一種「純粹視覺」的概念。這個概念從笛卡兒以至於現代主義攝影都可見其蹤跡,它暗示視覺是一種客觀成立的機制,與意識並無直接的關係。當笛卡兒將死人的眼球取出來做成像的實驗,就如同一個現代主義攝影家把創作交給了相機一樣。這樣的想法在1970 年代之後受到了批判,論者批評古典的視覺理論裡面所謂純粹的視覺並不存在,無論是眼睛或是相機都是一樣,於是人們對於視覺的理解從生物的角度轉向文化的角度。
但是視覺並沒有就此被放入文化的脈絡之中,失去了自身的特殊性。譬如我們都聽過一個說法,就是:學習觀看可以讓我們看到更多文字訊息以外的意義,一種意在言外的豐富性,它不一定能夠明確地提供我們「訊息」,但是它讓我們從不一樣的角度看到更多可能性。這裡有幾個關鍵字「可能性」、「豐富性」、「不一樣」,它們依然流行在當代藝術領域,某種程度上延續了視覺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字之外)理解世界的方式這樣的觀點。然而我們還是必須問,這件事如何可能?
此書《大師如何觀看:解構我們感知、創造、學習的方式》為這一個古典的觀點提出一些新的的理由。首先,作者認為從知覺研究的角度,我們本來就用這樣的方式看世界。作者貝蒂‧愛德華從一個我們耳熟能詳的說法出發,那就是人的左右腦功能是不同的,據此作者進一步論述人類的視覺其實也有左右眼的不同—左眼連繫到右腦,著重圖像、辨識事物的整體、空間的關係;後者連繫到左腦,連繫文字、資訊與意義。大多數人通常是使用資訊之眼作為主視眼(主要用來判斷之眼),另一隻眼則作為輔視眼,然而遠古時代的人類會用「視覺」之眼來觀看世界。在這一點上,作者如同許多教授藝術的書籍一樣,鼓勵讀者從圖像之眼及右腦邏輯來思考。只是作者更清楚地提出背後的生物依據。但這裡我們必須要注意,左右腦的區分在腦科學當中仍大有爭議,根據左右腦理論發展的左右眼區別自然也並非定論。所以與其相信腦中有兩個屬性不同的大腦,讓我們以不同的角度來看世界,不如將之理解為,視覺是兩種邏輯(空間與資訊、圖像與邏輯等等)往復協調的結果。
第二個理由是,作者認為在藝術品當中也有左右眼的差別,他舉出了許多經典畫作為例,分析其中人物左眼與右眼的不同。這帶給我們觀看作品更多的樂趣,譬如許多女性的肖像,刻意地著重輔視眼的描繪,呈現一種朦朧、曖昧的狀態。又或者是很多時候,我們觀看一張肖像其實只關注某一隻眼睛所呈現的情緒,即便另外一隻眼睛有截然相反的特質。這一部分是本書當中最引人入勝,但是又最讓人覺得將信將疑的地方,讀者不免會懷疑這些歷史上的藝術家,譬如林布蘭,他們真的意識到了左右眼的差別,因此才刻意地表現在畫作之上嗎?還是說這是作者自己的臆測,如同藝術史家有時會賦予眼睛某種文化象徵的意義?我覺得作者在此所暗示的是,左右眼的不同屬性其實已經內化在藝術家的觀看當中,因此當藝術家呈現作品當中人物的各種目光,自然也帶入了這樣的考慮。唯有我們從意義當中掙脫(資訊之眼),進入這一個視覺的遊戲,我們才能領略藝術品帶來的愉悅。我們這裡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在這整個過程之中,事實上無涉於視覺之外的脈絡(前述visibility 跟visuality 的層次)。
第三個理由是,了解左右眼的不同,能夠幫助我們在創作上做更細緻的實踐。作者提出了許多練習的方式,來幫助我們用不同視覺來觀看對象,譬如如何觀察負空間,或是如何描繪我們自己。就攝影創作的立場,這些練習其實非常地實用,因為創作者總是希望以新的視角來觀看世界,然後這件事究竟要如何實踐?本書其實提出了一些初步的練習方式。但是作為一個只能以一隻眼睛看世界的創作者(我左眼看不見),我對於書中的左眼練習只能敬謝不敏。這件事其實突顯了生理機制其實也是充滿各種差異,創作的類型也是,我們總不能說一個左眼無法觀看世界的人,在右腦上面的創意一定受到侷限。因此這些視覺的練習,與其被想像成一種生理能力的增強(像是訓練身體的某一塊肌肉一樣),不如當成一種意識的開發。
除了上面三點理由之外──人類左右眼本有不同屬性、藝術作品裡面本有左右眼的差異、創作與左右眼差異相關──理解左右眼的差異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能夠幫助我們在日常社交活動之中更順暢地溝通(或是不溝通)。譬如作者說當我們跟一個人講話不合拍之時,我們其實可以盯著他的非慣用眼,這樣他就會覺得不自在,然後快速地結束對話。這一段聽起來雖然有點好笑,但是頗能夠總結作者在本書之中的看法,眼睛既不是如同相機一樣忠實的機器,也不純粹是社會脈絡的產物。眼睛是在我們身上兩個性格迥異的生物,理解它們不同的特性,能夠幫助我們理解它們的主人,也能夠幫助我們理解自己。
引言
他人好奇是強烈的人類特徵。我們想知道:他們究竟是誰?他們在想什麼?他們感覺到什麼?為了一窺我們遇見的人們言行背後的「真人」,我們一直有兩個主要策略。一個是密切注意被說出的話;另一個是用我們的眼睛「看見」反映在對方臉孔和眼睛裡的真實想法。
幾個世紀以來,作家和思想家已經集結出無數關於這種淺意識狀態的諺語和語錄。羅馬政治家馬庫斯・圖留斯・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說:「臉是心智的肖像,眼睛扮演翻譯者。」羅馬天主教神父、神學家和歷史學家聖・杰洛姆(Saint Jerome)說:「臉是心智的鏡子,眼睛不須說話就能透露內心的祕密。」一句起源年月不可考的拉丁諺語說:「臉是心靈的肖像,眼睛吐露祕密。」
就連美國職業棒球捕手尤吉・貝拉(Yogi Berra)都呼應道:「光用眼睛看就可以觀察到很多現象。」
最著名但起源不可考的語錄之一是:「眼睛是靈魂之窗。」告訴我們能藉著深入觀察某人的眼睛,找到隱藏的「真人」。
一個更現代(但不那麼詩意)的版本可能是,「主視眼和輔視眼(dominant eye and subdominant eye)能揭露腦部思想。」問題出現了:我們談論的是哪隻眼睛?左眼或右眼,或兩者?而且是哪個腦?因為我們實際上有兩個「腦部思想」:也就是大腦(cerebrum)的左右半球。而雙眼,在我們大多數人來看基本上是一樣的,為什麼會有「主導」和「輔助」之分?事實上,我們的兩隻眼睛看起來並不相同,反映出我們的兩個腦半球及看待世界的兩種方式。兩隻眼睛之間的區別是可以觀察到的,同時卻又奇怪地無法識別。也許這些差異在我們尋找「真」人的過程中有所幫助?
我們在意識層級上,知道眼睛所見與我們的想法和思考方式有密切關聯,同時,也許與我們的感受有關。說也奇怪,當我們近距離看著鏡中自己的眼睛,或是面對面看別人的眼睛時,卻似乎沒有意識到我們其實可以看見哪隻眼睛對我們正在說或聽到的話做出反應;而哪隻眼睛可能正在感覺,卻不在乎說話的字義。大多數人都沒有意識到這種差異。但是,我們下意識地在日常生活中用這種方法獲取訊息,特別是依循眼睛接收到的訊息,引導我們與他
人互動。
這些相互作用因為所謂的思想/大腦/身體的交叉連接而變得複雜。對於大部分的人來說,我們的左腦半球會「越界」來從頭到腳控制右側身體,包括了主導右眼的功能;同樣地,右腦半球也會「越界」,從頭到腳控制左側身體,包括左輔視眼的功能。
對大多數人來說,右眼與控制語言的左腦半球緊密連結。無論是日常與重要的面對面談話裡,我們每個人都會下意識地試著與對方占主導地位的語言相關右眼連接。我們似乎想用右眼對著右眼說話──也就是主視眼對主視眼。
在面對面的交談中,我們常常會下意識地避開另一隻眼,亦即占從屬地位的左眼。左眼主要由非語言性的右腦半球控制,相較之下對口語明顯無法連結,也沒有反應。儘管如此,它仍然置身於談話當中,看起來有點遙遠,像是在做夢,但實際上是在對語氣、音調、對話中偏視覺和感情等非語言的面向做出反應。
我個人對這種人類眼睛奇怪的視覺差異的認識始於許多年前,是基於《像藝術家一樣思考》研習營裡教學和示範肖像畫累積的心得。我觀察到的越多,它就越引起我的興趣。因此,這本書主要在檢視如何利用我們的主視眼「畫圖」。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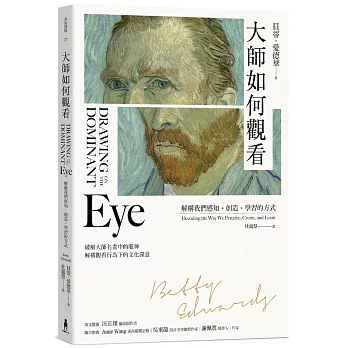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