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若下一個被社會丟棄的是我(或你),我們如何反抗?
人生百味共同創辦人 朱剛勇
今天,這裡也能讓人懷抱夢想嗎?
「人們總認為今天有的,明天也一定會有。照這個道理,昨天有的,今天也非有不可。」──《年輕人們》
小說家福澤徹三曾寫下一本恐怖小說,描述平凡的大學生突然被校方通知學費欠繳而退學,接著才發現父母失聯。男孩想辦法打工自立卻屢遭挫折,最後經歷一連串意外,竟快速跌落底層、變成街友。書出版後引起廣大迴響,甚至快速被翻拍成電影。
這本小說是《東京難民》,台灣出版時改翻成《年輕人們》,許多讀者反應他們更喜歡原名,我當時也是這麼認為,繁榮城市中難民乍現,對當年的島國而言確實更遙遠不思議。然而現在回想,原來是自己沒意識「年輕人們」傳達的驚悚呼告:難民並非來自異地、穿越海洋,而是從平凡生活隨機墜落的人,可能是你,是我,是任何的年輕人們。
前年夏天,當疫情三級警戒逐邁入尾聲,團隊突然接到數通求救電話。來電的人們與我們一直以來的協助對象相當不同──我很少如此形容:但他們很「正常」。求助者大多年輕,年齡落在二十五至三十五歲間,身心狀態與本來從事的工作都相當普通,不少是餐飲服務業。大家共同遇到的困境是遇到疫情影響,被無限期減班、放無薪假;當逐漸無法負擔房租和生活費,才意識到自己可能會流浪街頭。
阿文是其中一位。我們在團隊經營的無家者友善空間認識,他等待使用浴室時和我搭話,發現我們年紀相同後,阿文開始熱絡搜尋更多共通點,他說自已也常協助街友:「我都跟朋友定期集資買便當到車站發送。下禮拜也會到新竹發餐,你想一起來嗎?」
那你是從何時變成街友,變成我們幫助的人?我忍不住問。
阿文的家庭狀態複雜,他十六七歲便開始在外工作,希望能儘早自立。二十多歲時,朋友找他合資開小吃店,阿文說他那時覺得終於熬出頭、能當老闆了,於是卯起來做,常因為顧攤、備料而好幾天沒睡:「後來身體撐不住了,胃破洞吐血,我只好住院休養。小吃店也收了。我出院後身體還很虛弱,投靠朋友一陣子;最後是真的沒辦法,才來到台北流浪、找機會。」
找機會。阿文始終相信自己可以靠自己站起來。只要身體調養好,只要再讓他再次能工作,一切都會變好。那年在旁看著阿文起起伏伏,受疫情影響,他試了幾次卻無法回到餐飲業,去工地打工,卻又擔心高勞力會使舊病復發。最後,阿文離開了據點,決定到其他地方闖闖。
最後一次跟阿文聊天,阿文說:「台北是個充滿希望的地方,只要肯做,都會有機會。」為什麼呢,我無法理解:「現在你還是這麼覺得嗎?」阿文笑著回:對呀。那天之後,我再次翻閱《年輕人們》,發現書封上有這一段文字:「這裡,能讓你懷抱夢想嗎?」
為什麼我們需要認識新下層階級
「假使社會上有我們難以啟齒、無法明確承認或辯論,並缺乏心智工具和詞彙來恰當描述之事,那麼我們都是無聲之人。」──《不平等的樣貌》
與阿文相似的身影並不只存在於小說中。後來在街上、不同社福組織中,我也陸續與這些「年輕人們」相遇:三十歲的雯雯本來是全職母親,遭受家暴後帶著兩個孩子在外租屋,卻因此陷入經濟困境;李哥長年在工地打工,但當身體受傷、收入銳減而負擔不起租金後,只能住在由貨櫃隔成的簡陋小房間。
這些人在墜落前一刻都未發現自己是弱勢者,社會救助制度也是如此認知:他們未達老年身分,有工作能力,也未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社會認為他們可以、應該憑藉已力脫困;然而在我接觸過程,覺得他們從來沒不努力,也沒放棄過努力(如同阿文深信只要努力就有機會),社會卻因此更理所當然將這些人推遠。被推遠的人們載浮載沉,多數要等到「終於」掉落到谷底,符合法定的受助定義後,才終於被體制受理。
如果阿文,以及那些同他一樣的人們,會在這時代裡遭受踉蹌、摔落後難以爬起,當有日浪潮捲向我,或你,我們是否真有如此把握仍能站得住腳?
《底層世代》所期待的,正是帶領讀者直視處在灰色地帶、未被社會福利納入支持範圍的高風險群體。作者梳理「底層階級」一詞的定義,以及其被污名化、進而成為輿論抨擊對象的脈絡,再透過數據及訪談,找出此刻社會已形成、處在危殆狀態卻未被正視的「新下層階級」。
閱讀過程若發現自己也被包含其中,請別害怕,你並不孤單。此刻正是我們相認、結伴,一同補起這面網、停止讓人繼續墜落的時刻,在大浪來臨前。
愈無望,愈有希望:絕望時代的自救守則
相較這些年台灣代理的日本貧困議題出版,《底層世代》並不算好閱讀。若想聆聽生命故事,NHK 採訪小組的《女性貧困》和《無緣社會》會更加豐富、有溫度;想拓展對個別群體的認識,坂爪真吾《裏面日本風俗業界現場》和藤田孝典《貧困世代》則分別對性產業與貧困青年有更深入的描繪。
《底層世代》著重於數據分析,從就業結構中討論非典型勞動導致貧窮的風險極高,再對照家戶收入與個人所得,層層抽絲剝繭找出最容易墜落底層的類型。令人驚訝(或不驚訝)的結果是,所謂的類型竟然廣泛分布,包含男性、女性,青年與高齡者,甚至有部分也無關是否出生在貧窮家庭。
聽起來是讓人感到絕望的結果,然而作者在分析過後,竟提供了積極正向的見解。他認為每個人都是有希望的,多數經濟不穩定的青年男性因為感知得到自己的困境是由社會結構造成,因而更有機會被組織動員,改變社會;而許多女性則因積極維繫社會關係,即便在貧困生活中也有培養興趣的意願,反而不容易陷入絕望。甚至在最後章節也提供了政治改革的積極建議,這些都是過往相關議題討論中所難以出現的樂觀。
艱困咀嚼書中的圖表、數字,我盯著小數點,心想阿文終於不再被排除了,他遭遇的困境痛苦終於被正視與定義。而我與阿文的距離,確實沒有想像中遙遠,就如同他當年所說。
我們真的有機會在時代的浪打上時仍安好存在嗎?前年收到阿文的信,他說:「世界上有更多熱情的人,那會更美好。」似乎在提醒我們別放棄希望。無論如何,祝福即將閱讀這本書的你找到自己的答案,願機會永遠對我們有利。
從日本的他山之石反思台灣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危殆生活》作者 黃克先
歐美國家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貧富不均的現象日益惡化,更少數的富人以更驚人的速度積聚更高比例的財富,這使得許多學者投入社會不平等的研究,憂心忡忡地提出各種改革呼籲。從各種社會不平等指標來比較世界先進國家的表現,日本都是非常突出的。儘管相對平等,但我們會發現日本人卻非常關注社會上新興經濟弱勢的處境。不僅嚴肅的社會評論節目會邀請學者做系統性的討論,製播的戲劇與電影中也常以繭居族、飛特族、尼特族為題,例如著名演員阿部寛與佐藤健主演的《那些得不到保護的人》、二宮和也主演的《飛特族、買個家。》、吉岡里帆的《健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深田恭子的《Silent Poor》。NHK更經常製播討論社會新興邊緣群體的節目,多方訪談了貧窮者與服務者,內容不但紮實且有深度,其成果常出版成冊供更多日本民眾認識各類貧窮現象,例如台灣已翻譯過來的《無緣社會》、《女性貧困》。另外如藤田孝典所著談青年貧窮的《貧困世代》及老年貧窮的《下流老人》,及家庭社會學者山田昌弘的《社會為何對年輕人冷酷無情》都引發不少台灣在地的討論。
書同樣關注新興貧窮現象,而因作者是長期關注日本的社會階層化與階級問題的社會學者橋本健二,因此書中摻雜更多的數據、類型區分、術語、學院詞彙。他延續以往認為「一億總中流」的平等社會走向階級差距拉大的格差社會的論點,本文主體以此為開端,在第三章討論目前日本新的階級結構,包含了四大階級:資產階級、新中產階級、勞工階級、底層階級,而本書即聚焦在底層階級上,其主要特點是從事非典型工作。橋本再以六十歲及性別為分界將其區分為四種類型,在四、五、六章中分別討論其不同處境。第七章則談到底層階級由於從事危殆的(precarious)工作型態而常面臨失業的風險。第八章則別出心裁地討論底層階級與日本政黨政治之間弔詭的關係,提醒左派政黨要找回初衷與理念。最終在結尾處,橋本一如本書開頭,以日本人熟知的連續殺人犯為例,認為這種社會不平等的困境很可能導致各種災難性的後果,呼籲大家要正視。
相對於前述由NHK編採或長期任職非營利組織的作者撰寫的相關著作,本書因為較缺乏底層人士的現身及人敘事,讀來較為艱澀,但讀者也能透過更多客觀數據捕捉貧窮者樣貌。事實上,當代社會中的貧窮現象日益複雜且容易被表象掩蓋,當中也涉及許多文化因素及幽微的情緒感受,本就應藉由多重管道方能掌握全貌並有更深刻的理解,除了藉由統計數據分析以外,我們也應搭配實地參與貧窮者生活,或傾聽有貧窮經驗者講述的研究成果,加上第一線工作者及從事社運者的觀察,方能窺其全貌,並擬定更有效且減少副作用之應對貧窮政策或介入方式。
二〇〇〇年以後的台灣社會進入社會不平等加劇的時期,儘管從各種衡量指標及統計數據來看,台灣與其他國家相比,人民之間仍是相對經濟平等的,但相較於以往確實貧富差距明顯擴大,社會學者林宗弘等人的研究更明確指出,階級流動變得困難重重,過去引以自豪的要拼才會贏的生活哲學成為往事,黑手變頭家的故事常只停留在追憶中,無法上漲的薪資及驚人的住房成本讓青年生活壓力沉重,要繳納各種社會保險卻眼見早在他們能領取之前就可能破產。許多忽略更廣泛經濟結構因素及社會脈絡的觀察家或主流媒體,更屢屢為這些「崩世代」年輕人貼上各種如草莓族、小確幸世代的負面標籤,更讓他們覺得無力且無言而傾向躺平或厭世。面對這樣的處境,我們需要更多橋本健二撰寫的《底層世代》的著作,助我們省思在高速成長過後陷入停滯的當代社會經濟不平等的樣貌為何,而身處貧困的人們具體處境又如何。
前言(節錄)
一九六五年,永山則夫國中畢業後隨即透過集體就業機制來到東京,輾轉換了許多工作,最後在一九六八年秋天連續犯下了多起槍擊殺人事件,其死刑在一九九七年被執行。永山則夫在獄中大量閱讀了文學作品和思想典籍,繼而寫下多部作品問世。其中一篇名為〈驚產黨宣言〉的文章,是他在一九七一年所寫下的。
在這篇文章裡,他主張社會由三個階級組成:「大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與貴族無產階級」及「流氓無產階級」。所謂流氓無產階級指的是沒有固定職業的勞工與居無定所的流浪漢。卡爾.馬克思曾經主張這個階級是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敵對的潛在犯罪者,並留下諸多侮蔑性言論。然而根據永山的論點,被馬克思視為革命性下層階級穩定受僱的無產階級,將和大資產階級勾結而導致自身的貴族無產階級化,終與流氓無產階級產生對立,犧牲後者並使自己免於從事高危險性的勞動,過上豐衣足食的生活。於是永山便主張,如今只有流氓無產階級稱得上是革命階級,他們從事個體式的恐怖攻擊,與資產階級抗衡,或將集結為恐怖分子組織。(本文收錄於《遺忘人民的金絲雀》一書)
把自己化約為革命的流氓無產階級,由此正當化自己的所作所為,這般荒唐論調倒也並非無法理解。不過若再更深入地去思考,會發現他所陳述的是相當精確的現況分析,或者說讓人有點毛骨悚然的預言,因為現今的日本社會,正逐步朝他所描述的景象靠近。在階級落差逐漸擴大的趨勢中,「大資產階級」確實積累了愈來愈多的財富。而受雇者階級之內也出現了巨大的落差,其中位居頂點的是任職於跨國企業的高所得菁英,成群結隊散落底層的則是領著低廉工資的非典型勞工,其所占全體比例正持續增加。這樣的結構,正是造成社會不安定的根源。
在這些非典型勞工中,筆者先將為貼補家用而打工的主婦、非正職的員工及管理職、擁有專業證照或技能的專業工作者排除,將其餘的人稱為「底層階級」(underclass)。這個階級的人口數量約為九百三十萬人,占總就業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並正迅速增加。
這個階級多為以下這一類人(此處的九百三十萬人雖包含高齡人口,但以下統計數字不計入有資格領取年金的六十歲以上人士)。
以平均年所得僅一百八十六萬圓為界線,貧窮率是相當高的百分之三十八.七,其中女性的貧窮率更是接近五成。這個階級的人所從事的工作,許多是體力勞動、銷售職與服務業;具體來說包括了商店店員、廚師、服務員、清潔工、收銀員、出納員、倉管與裝卸工、護工、居家看護以及派遣事務員等。平均工時只比全職勞工少一至兩成,許多人工時甚至不比全職勞工短。
正因深陷貧困,結婚成家也非易事。此階級男性高達百分之六十六.四為未婚,有配偶者僅占百分之二十五.七。單身女性也超過半數,其中高達百分之四十三.九的人曾經歷離異或喪偶,成為陷入貧窮的主因。對生活感到滿意者僅占百分之十八.六,不到其他階級的一半。
許多人度過灰暗的童年。超過三成的人曾遭霸凌,一成的人曾拒絕上學。也有很多人中途輟學,大約三分之一的人從畢業到找到工作之間有一段空窗期。
他們的健康也多半出了問題。有四分之一的人自覺健康狀態不佳。曾患上心理疾病的人占兩成,是其他階級的三倍。其中不少人如此自述:「時常感到絕望」、「意志消沉,做什麼都提不起勁」、「覺得自己沒半點價值」。
能從旁給予支持的親友也很少。跟其他階級的人相比,底層階級的人身邊親近的人很少,他們很少參加社區活動和基於興趣而成立的集會以及同學會。過半數的人對於未來感到不安。
過去提到資本主義社會的下層階級,指的都是無產階級,亦即勞動階級。自營業者之類的舊中產階級姑且不論,構成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階級,是包括經營者在內的資產階級、專業工作者與管理階層所構成的新中產階級,以及理所當然位於最下層的勞動階級。
然而雖說經濟不景氣導致整體所得水準有所下滑,勞動階級中從事典型勞動的人卻提高了所得,這使他們看起來更像是新中產階級。勞動階級內部出現巨大的裂縫,非典型勞工被排除在外,跌落至最底層。於此,新的下層階級,也就是底層階級便誕生了。
「底層階級」這個詞彙並非筆者自創。對此筆者會在第二章詳細論述,不過這個詞很早以前便已用於階級研究與貧窮研究的領域中。其用法依時代與論述者詮釋角度而有所不同,但所指對象皆是那些永久陷入難以掙脫貧困狀態的群體。
美國與英國的大都會中聚集著大量的失業者、就業不穩定的人以及少數族裔的貧困階層。與其不同的是,日本直到最近都未出現這種現象。不過,在階級落差逐漸擴大的趨勢中,日本也出現了與典型勞工有顯著差異的底層階級,他們占了整體就業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已足以成為階級結構中重要的一環了。正因為如此,筆者才會主張「新階級社會」已經出現。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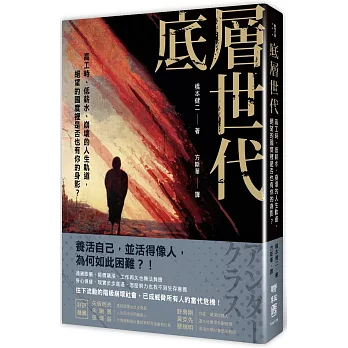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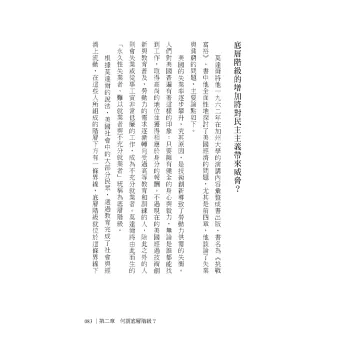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