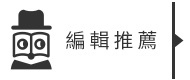前言
羅伯特.奧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的人生——他的事業、聲譽,甚至他的自我價值感——在一九五三年的耶誕節前四天,突然打滑失控了。「我無法相信發生在我身上的事。」他大聲感嘆,眼睛凝視車窗外,開得飛快的車正載著他奔向他的律師位於美國華盛頓特區喬治城的家。在那裡,幾小時內,他必須面對命運攸關的抉擇。他該辭去政府顧問的職位嗎?或者他該反擊美國原子能委員會(Atomic Energy Commission,簡稱AEC)主席路易.史卓斯(Lewis Strauss)那天下午突如其來遞送給他的指控信件?這封信通知他,一份新的背景調查和政策建議宣布他是對國家安全有所威脅的危險人物,接著描述了三十四項指控,涵蓋了荒謬的——「根據報告,你在一九四〇年列名為『中國之友』的贊助人」——到政治性的理由——「一九四九年秋天,以及在那之後,你強烈反對發展氫彈」。
古怪的是,自從原子彈轟炸日本廣島和長崎之後,奧本海默一直懷有模糊的預感,前方有什麼黑暗和不祥的事等著他。早幾年,在一九四〇年代晚期,他已在美國社會取得無庸置疑的標誌性偶像地位,成為他那一代最受尊敬和仰慕的科學家與公共政策顧問,甚至登上《時代》和《生活》雜誌的封面——那時他就已經讀過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短篇小說《林中野獸》(The Beast in the Jungle)。這篇關於執念以及因為自我中心飽受折磨的故事,讓奧本海默看得完全呆掉了。故事裡的主角被自己的預感所糾纏,他在「等待某件稀罕而奇特,很可能異常驚人和可怕的事,且遲早會發生」。無論是什麼事,他都知道那會「吞噬」他。
隨著戰後美國興起反對共產主義的潮流,奧本海默愈來愈明白,「林中野獸」在跟蹤他。「獵紅」的美國國會調查委員會要求他出庭、聯邦調查局(FBI)監聽他住家和辦公室的電話、關於他過往的政治活動和政策建議新聞媒體刊載惡意中傷的故事,在在使他覺得自己是被狩獵的人。一九三〇年代他在柏克萊時期的左翼活動,加上戰後他反對空軍以核子武器進行大規模戰略轟炸(他稱之為種族滅絕的計畫),激怒了許多華府圈內的有力人士,包括聯邦調查局局長艾德格.胡佛(J. Edgar Hoover)和路易.史卓斯。
那天晚上,在赫伯和安.馬克斯(Herbert and Anne Marks)夫婦喬治城的家中,奧本海默苦苦思索他面前的選項。赫伯不只是他的律師,也是他最親密的友人之一。而赫伯的太太,安.威爾森.馬克斯(Anne Wilson Marks)曾經是他在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祕書。那個夜晚,安觀察到奧本海默似乎處於「幾近絕望的心情」。不過,在連番討論之後,奧本海默有了結論,或許辭職就形同定罪,無論對方設的是什麼局,他不能讓指控橫行無阻。因此,在赫伯的指導下,他草擬了一封信給「親愛的路易」。奧本海默在信中指出,史卓斯慫恿他辭職:「你給我一個狀似可取的替代方案,由我自行請求終止合約,不再擔任(原子能)委員會的顧問,那麼就得以避免公開回應這些指控……」奧本海默表示他認真思考了這個選項。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他接著說:「這種做法將意味著我接受並且同意這種看法,即我不適合為這個至今我已服務了將近十二年的政府效力。我不能這麼做。如果我是這麼不足取,我就不可能如我所努力過地,為我們的國家效勞,或者擔任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院長,或者不只一次發覺自己代表美國的科學界和國家發言。」
那天長夜將盡時,羅伯特.奧本海默疲憊不堪又意志消沉。喝了幾杯酒之後,他到樓上的客房休息。幾分鐘後,安、赫伯,以及陪伴奧本海默到華盛頓的妻子吉蒂(Kitty),聽到「可怕的撞擊聲」。火速奔上樓,他們發現臥室空無一人,而浴室門緊閉。「我打不開門,」安說:「我也無法讓羅伯特回應我。」
奧本海默癱倒在浴室的地板上,而他失去意識的身體擋住了門。他們用力一點一點將門推開,把羅伯特癱軟的身體推向一邊。當他甦醒過來時,「他當然是話說得含含糊糊。」安回憶道。奧本海默說他吃了一顆吉蒂的處方安眠藥。「不要讓他睡著。」醫生在電話裡警告。因此直到醫生抵達之前,他們帶著奧本海默走來走去將近一小時,哄他吞下一小口一小口的咖啡。
奧本海默的「野獸」撲過來了;這場將結束他公職生涯的試煉開始了,然而相當諷刺的是,這既提升了他的名望,又鞏固了他的歷史地位。
羅伯特.奧本海默從紐約市前往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這一段路引領他參與了二十世紀科學、社會正義、戰爭和冷戰歷史上的偉大鬥爭與勝利,也讓他從籍籍無名走向聲名顯赫。他的非凡智力、他的父母、他在「倫理文化學校」(Ethical Culture School)的老師們,以及他年少的經歷,指引他走向這趟旅程。專業上,他的發展始於一九二〇年代在德國學習量子物理學,他熱愛而且熱心宣揚這門新科學。一九三〇年代,他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建立美國這方面最頂尖的研究中心的同時,經濟大蕭條在美國國內造成的後果及國際上法西斯主義興起的影響,推動奧本海默與朋友(其中許多位是同路人或共產黨員)活躍於追求經濟與種族正義的鬥爭之中。那些年是他生命裡一些最美好的時光。十年之後,人們如此輕易地拿那些年的活動來箝制他的聲音,這提醒了世人,我們宣稱的民主原則是多麼脆弱地維持著平衡,以及必須多麼小心翼翼來護衛。
奧本海默在一九五四年忍受的痛苦和羞辱在麥卡錫時代並非特例。然而他是地位無人能比的被告。他是美國的普羅米修斯,「原子彈之父」,戰爭期間為他的國家帶頭努力從大自然攫取令人敬畏的太陽之火。之後,他明智道出其中的危險,也對潛在的助益懷抱希望。接著,軍方接受了核子戰爭的提議,學院的戰略家也跟著推波助瀾,使他近乎絕望地嚴詞批判:「我們要如何理解,一個總是把倫理道德視為人類生活不可或缺一部分的文明,除了使用慎重其事的字眼和賽局理論的術語,就沒法子談論幾乎會殺死每一個人的前景?」
一九四〇年代晚期,隨著美蘇關係惡化,奧本海默咬住核子武器議題不放,持續提出這類尖銳的質疑,嚴重困擾了華府的國家安全機構。一九五三年共和黨重返白宮,提拔了主張大規模核武報復的倡議者,例如路易.史卓斯,擔任華府有權勢的職位。史卓斯和他的盟友決心讓能夠贏得信賴並挑戰他們政策的那個人發不出聲音來。
一九五四年,批判奧本海默的人藉由攻擊其政治觀點和專業判斷(事實上就是他的人生和價值),曝光了他性格中的許多面向:他的雄心和不安全感、他的聰慧和天真、他的堅定和畏縮、他的隱忍克制和徬徨困惑。美國原子能委員會(AEC)的「人事安全聽證委員會」公布將近一千頁印得密密麻麻的逐字稿——《關於奧本海默案》(In the Matter of J. Robert Oppenheimer),揭露了大量訊息,然而聽證會紀錄也透露出奧本海默的對手對於穿透這位複雜男人自幼建構的情感盔甲是多麽無能。《奧本海默》探究盔甲下的謎樣人格,追溯羅伯特.奧本海默的一生,從二十世紀之交於紐約上西區的童年,到一九六七年去世。這是一本極為個人的傳記,因為作者相信一個人公開的行為和他的政策決斷(在奧本海默的例子裡或許甚至包括他的科學)皆受其一生私密經驗的引導,我們在此信念下進行研究和寫作。
完成此書花了四分之一個世紀,《奧本海默》奠基於成千上萬份紀錄,從國內外的檔案和私人收藏蒐集而來。這本書取材自奧本海默個人收藏於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大量文件,以及美國聯邦調查局(FBI)超過四分之一世紀所累積的數千頁監控紀錄。很少有公眾人物承受過這樣的審查。讀者會「聽到」他的話語,由FBI的錄音設備捕捉下來轉成文字稿。不過,即使是書面紀錄也只能說明一個人一生的部分真相,因此我們也訪問了將近一百位奧本海默的密友、親戚和同事。許多在一九七〇和八〇年代受訪的人都已經過世了,然而他們述說的故事留下了一幅細緻入微的肖像,這名卓越不凡的肖像主人帶領我們進入核子時代,而且奮力想要找出方法排除核子戰爭的危險。他沒有成功,我們繼續努力。
奧本海默的故事也提醒我們,我們的身分依舊是與核子文化密切相連的民族。「自從一九四五年之後,我們的心頭上都有那顆炸彈。」小說家達克托羅(E. L. Doctorow)評述。「核子首先是我們的武器,然後是我們的外交,現在是我們的經濟。我們怎麼能認為威力如此可怕的東西,不會在四十年後,構建了我們的身分?我們塑造出來對抗敵人的最巨大魔偶(golem)就是我們的文化,我們的炸彈文化——它的邏輯、它的信仰和它的視野。」奧本海默的奮戰是英勇的,他試圖藉由遏阻他曾協助釋放的核子威脅將我們帶離那個炸彈文化。他最讓人動容的努力是提出一份「國際原子能管制」計畫,後來成為世人所知的「艾奇遜-利連塔爾」報告(Acheson- Lilienthal Report,它實際上是奧本海默的構想,大部分內容由他執筆)。這項計畫仍是核子時代中獨一無二的理性典範。
不過,國境內外的冷戰政治使得計畫註定失敗,美國以及名單愈來愈長的其他國家,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選擇擁抱炸彈。隨著冷戰結束,核子大滅絕的危險似乎過去了,然而卻迎來另一個反諷的轉折,核子戰爭和核子恐怖主義在二十一世紀或許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在眉睫。
在後九一一的年代裡,讓我們回想一下核子時代的開端,原子彈之父警告我們,這種武器帶來的是無差別的恐怖,即刻使得美國愈發容易遭受恣意攻擊的傷害。在一九四六年不公開的參議院聽證會中,他被問到「三、四個人是否無法走私(原子)炸彈組件到紐約,然後把整個城市炸掉」,他尖銳地回應:「當然做得到,而且人是有可能摧毀紐約的。」一名受到驚嚇的參議員接著提出問題:「你要用什麼工具來偵測隱藏在城市某處的原子彈?」奧本海默嘲諷:「一把螺絲起子(用來打開每一個木箱或手提箱)。」唯一可以抵禦核子恐怖主義的方法是:銷毀核子武器。
奧本海默的警告無人理會,最後,他被消音了。如同反叛的希臘神祇普羅米修斯——他從宙斯那裡盜來火贈與人類,奧本海默給了我們原子之火。不過之後,當他試圖控制它,當他設法讓我們明白其中可怕的危險時,當權者如同宙斯,憤怒出手懲罰他。如美國原子能委員會轄下聽證委員會中的異議分子沃德.艾文斯(Ward Evans)所寫,撤銷奧本海默的安全許可是「我們國家盾章上的汙點」。
序曲
該死的,我恰好熱愛這個國家。
——羅伯特.奧本海默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美國紐澤西州的普林斯頓。儘管惡劣的天氣和嚴寒冷凍了美國東北部,六百位朋友和同事(諾貝爾獎得主、政治人物、將軍、科學家、詩人、小說家、作曲家和來自各行各業的熟人)聚集起來,哀悼羅伯特.奧本海默的去世,追思他的一生。有些人認識的他是和藹可親的老師,深情稱呼他「奧比」(Oppie)。其他人認識的他是偉大的物理學家、在一九四五年成為「原子彈之父」的男人、國家英雄,以及科學家成為公僕的象徵。每個人皆帶著深沉的苦澀回憶,只因僅僅九年之後,當時甫上任的艾森豪總統所領導的共和黨政府宣布羅伯特.奧本海默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使他成為美國反共聖戰中最著名的受害者。他們心情沉重地來到這裡,緬懷一位傑出人士,他不凡的一生點綴著勝利,也籠罩著悲劇。
出席的諾貝爾獎得主包括了世界知名的物理學家:伊西多.拉比(Isidor I. Rabi)、尤金.維格納(Eugene Wigner)、朱利安.施溫格(Julian Schwinger)、李政道和艾德溫.麥克米蘭(Edwin McMillan)。愛因斯坦的女兒瑪格(Margot Einstein)也在場,致敬這位她父親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上司。奧本海默一九三〇年代在柏克萊的學生、也是密友和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元老的羅伯特.瑟柏(Robert Serber)也在場,還有偉大的康乃爾大學物理學家漢斯.貝特(Hans Bethe),這位諾貝爾獎得主揭露了太陽的內部運作。來自加勒比海寧靜的聖約翰島上的鄰居伊娃.德納姆.葛林(Irva Denham Green)——經歷一九五四年的公開羞辱之後,奧本海默夫婦在島上建造了一棟海濱小屋避居。緊挨著伊娃而坐的是掌握美國外交政策的袞袞諸公:律師暨長年的總統顧問約翰.麥克羅伊(John J. McCloy)、「曼哈頓計畫」的軍方首領萊斯里.葛羅夫斯(Leslie R. Groves)將軍、海軍部長保羅.尼茲(Paul Nitze)、曾獲普立茲獎的歷史學家小亞瑟.史勒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以及紐澤西參議員克里福德.凱斯(Clifford Case)。詹森總統派了他的科學顧問唐納.霍尼格(Donald F. Hornig)代表白宮出席,他也是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的元老,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進行「三位一體」測試引爆第一顆原子彈時,他就在奧本海默身邊。點綴在科學家和華府權力菁英之中的是文學和文化界人士:詩人史蒂芬.史班德(Stephen Spender)、小說家約翰.奧哈拉(John O’Hara),作曲家尼古拉斯.納布可夫(Nicholas Nabokov),以及紐約市芭蕾舞團的總監喬治.巴蘭欽(George Balanchine)。
奧本海默的遺孀,凱瑟琳(暱稱「吉蒂」).普寧.奧本海默(Katherine “Kitty” Puening Oppenheimer),坐在普林斯頓大學亞歷山大廳的前排,參與這場將被許多人記憶為壓抑、溫馨與苦澀交織的追悼會。跟她坐在一起的是,他們二十二歲的女兒東妮(Toni)和二十五歲的兒子彼得(Peter)。坐在彼得旁邊的是羅伯特的弟弟法蘭克.奧本海默(Frank Oppenheimer),在麥卡錫主義橫流期間,他本人的物理學家生涯也遭到摧毀。
伊果.史特拉汶斯基(Igor Stravinsky)的《安魂頌歌》(Requiem Canticles)在禮堂響起,前一年秋天就在這個大廳,奧本海默第一次聽到這首樂曲,而且讚賞不已。接著,認識奧本海默長達三十年的漢斯.貝特,講述了三篇悼詞中的第一篇。「他比任何人做得更多,」貝特說:「讓美國的理論物理變得卓越……他是領導者……不過他不會作威作福,也從來不會下令應該做什麼。他讓我們發揮出最好的一面,就像一位好主人對待他的賓客……」在洛斯阿拉莫斯,奧本海默督導數千人,在一場設定的競賽中搶先德國人造出原子彈。奧本海默把一片原始台地改造成實驗室,同時把一群背景迥異的科學家打造成一支有效率的團隊。貝特和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的其他元老相當清楚,如果沒有奧本海默,他們在新墨西哥州最初建造出來的「小器械」絕對無法及時完成於戰爭中使用。
奧本海默在普林斯頓的鄰居、物理學家亨利.德沃夫.史邁司(Henry DeWolf Smyth)致第二篇悼詞。一九五四年,原子能委員會(AEC)的五位委員中,史邁司是唯一一位投票贊成恢復奧本海默的安全許可。見證了奧本海默忍受「安全聽證會」形同動用私刑的專制法庭,史邁司完全理解這是一齣扭曲事實的滑稽戲碼:「這樣的不公不義永遠不可能矯正;這樣的汙點永遠不可能從我們的歷史中抹除……我們深感遺憾,他為國家完成了偉業,回報卻是如此不堪……」
最後,輪到資深外交家暨大使喬治.肯楠(George Kennan),戰後美國遏制蘇聯擴張實施的圍堵政策,就是他孕育出來的主張。肯楠是奧本海默的老友,也是他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同事。沒有人比奧本海默更能刺激肯楠去思考核子時代的重重危險。也沒有人比奧本海默是更好的朋友,當肯楠不同意美國冷戰政策軍事化的觀點而落難成為華府「賤民」時,奧本海默捍衛肯楠的著作,庇護他在研究院安身。
「沒有人,」肯楠說:「承受過更大的殘酷。人類最近征服了一種凌駕自然的力量,卻跟他們的道德力量完全不成比例,由此引發兩難的困境。沒有人看得更清楚,這種不斷加大的差距對於人性會帶來什麼樣的危險。這種焦慮從來沒有動搖他的信念,他始終堅持追求所有形式的真理,科學和人道的。也沒有人比他更熱切地想要派上用場,防止發展大規模毀滅武器可能導致的大災難。他念茲在茲的是人類的利益,然而身為美國人,透過他所屬的這個國家共同體的媒介,他同時看到自己在追求這些抱負時擁有的最大可能性。
「在五〇年代初期的黑暗日子裡,當麻煩從四面八方向他蜂擁而來,當他察覺自己位於爭議的中心而焦頭爛額時,我提醒他注意一項事實:他會受到國外一百個學術中心的歡迎,並且詢問他『難道沒有考慮過定居國外嗎』。他眼睛含著淚水給了我答案:『該死的,我恰好熱愛這個國家。』」
羅伯特.奧本海默是一道謎,他是一名展現偉大領袖超凡魅力的理論物理學家,也是一名培育曖昧歧義的美學家。在他離世的幾十年後,他的一生在人們口中卻愈漸包裹在爭議、神話和謎團裡。對於科學家來說,例如日本第一位諾貝爾獎得主湯川秀樹認為,奧本海默是「現代核子科學家的悲劇象徵」。對於自由主義者來說,他成為麥卡錫主義獵巫風潮下,最著名的殉道者,象徵了右翼不講基本原則的惡意。對於政治上的敵人來說,他是地下共產黨員,也是證據確鑿的騙子。
事實上,他是充滿人性的大人物,既有才華又複雜,集聰慧與天真於一身,熱情倡導著社會正義,同時是不知疲倦的政府顧問。他致力於控制失序的核武競賽,這為他招來有權有勢、官腔官調的敵人。如他的朋友拉比所說,「他非常有智慧,也非常愚蠢」。
物理學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在羅伯特.奧本海默身上看見深沉和尖銳的矛盾。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科學和理性思考。然而,如同戴森的評述,奧本海默決定參與製造大屠殺性質的武器,「無疑是一樁浮士德與魔鬼的交易……當然我們依舊承受著後果……」如同浮士德,羅伯特.奧本海默試圖重新協商這樁交易——因此受到打壓。他帶頭研究釋放出原子力量的方法,然而當他尋求途徑只為警告同胞這其中的危險,想要約束美國對核子武器的依賴時,政府質疑他的忠誠,並且要他接受審判。他的友人將這種公開的羞辱,比擬為一六三三年另一位科學家伽利略接受中世紀時期的教會審判。有些人在此事件中看見醜陋的反猶太主義幽靈,並且回想起一八九〇年代,艾佛列德.德雷福斯上尉(Captain Alfred Dreyfus)在法國經歷的試煉。
不過,任何比擬皆無助於我們了解羅伯特.奧本海默這個人,了解他身為科學家的非凡成就,以及身為核子時代締造者他所扮演的獨特角色。這本書就是他一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