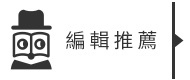中文版序
去年我的書問世之後,短短一年裡,香港已經面目全非,而且變化速度快得驚人,我無法想像這一年裡香港多少事物被破壞,多少異議被噤聲,多少歷史被改寫。香港如今被籠罩在沉默的陰霾之中,而當愈少人出來批評,中共就愈能肆無忌憚地改造香港。香港正在被瓦解,而且腳步不斷加快。
我在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關心的其實不是現在,而是過去。我想要重塑香港的歷史,讓香港人自己講述他們自己的故事,而不是繼續由殖民統治者代替他們敘述。當時我並沒有料到,中國共產黨會如此迅速地試圖改寫現在,它不僅強行改變視角,甚至還扭曲焦點。中共這些作為讓人迷失方向,我在這本書記錄下來的每一個當下時刻,反客為主成了重中之重。
自二○一九年的抗議運動以來,許多東西都一一消失了:政黨、工會、報紙、書籍、藝術品、各種口號和抗議的歌曲。時間過得愈久,消失的東西只會愈多。不久之前寫下的書頁,如今讀來恍如隔世,只覺滄海桑田。我感覺自己生活在一個被毀滅又被重建的世界,這座城市像被撕開了一道裂縫,露出潛伏在底層的暗影社會。
在所有消失的事物之中,最令人痛心的是香港的人。比如被關押牢中的四十七名泛民主派人士,因為他們二○二○年曾參與初選而遭控「顛覆國家政權罪」,現在還在遙遙無期的審訊階段。同樣消失的還有《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先生,他面臨一連串的指控,目前正被單獨拘禁。除了他們,還有數不清的民眾在參與了抗議活動之後下落不明,以及數以千計的香港人自願放逐自己,流亡海外。這些都讓香港變得日益貧瘠。
這本書出版之後的一年以來,北京方面加強了對香港人的壓制力道,甚至針對八名海外運動人士發出了價值百萬美元的懸賞。我在墨爾本見到了他們其中一人,他的名字叫劉祖廸。他臉上靠近眼睛的地方有一道疤痕,是他在英國被不明人士攻擊所留下的,那次的攻擊嚴重到差點讓他失明。他說,這道疤是某種榮譽的象徵,他每次照鏡子都能看到。
這些公然的恐嚇行為,其實也顯示了中國有多麼恐懼。中國共產黨最害怕自己所統治的人民,害怕他們在團結中找到力量。這就是為什麼它試圖消除香港獨特的歷史、身分認同、文化和語言。它想要粉碎香港人,擊破人們在抗議運動之中與彼此建立起來的緊密連結。在香港發生的一切,對台灣和全世界來說是鐵錚錚的警示寓言。
今年初,我的中文譯本出版社總編富察延賀在訪問中國期間被拘留了。這毋寧又是一記警告。富察引進了許多西方著作譯本,包含許多近代歷史著作,讓華語世界讀者接觸到新的思想和觀點,為台灣人架起了瞭解中國和其他世界的知識橋梁。我很榮幸成為他的作者之一,並且希望讀者記得,富察為了捍衛出版自由正付出巨大的代價。他目前被關押隔離在中國,他的困境充分顯示,中國共產黨是多麼恐懼思想的力量。
讓中國懼怕的事物,還包括記憶的力量,但是香港人最擅長的就是記憶。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門運動的血腥鎮壓。在中國,人們被禁止公開紀念;但在香港,人們每年自發地舉行悼念守夜,為當年在中國境內被殺害和監禁的人點亮燭光。如今,這份記憶的責任落到了新的香港僑民及海外支持者的肩上,我們必須想辦法不斷記得此時此刻在我們的城市所發生的一切。
在過去的一年裡,我曾到文學季、圖書館、大學和中學校園分享香港的議題。我上過廣播,也到課堂、社區中心去演講,甚至有一次分享會的地點是在一家中餐廳。我意識到,這座城市正在我們眼前不斷變化,而且變得愈來愈陌生。我離開香港愈久,就愈發認不得這座城市。但我也很清楚,這完全是北京擅長的手法;那些仍留在香港的人無法再公開發言,而其他生活在海外的人則被邊緣化,變得無足輕重。
各形各色的人來聽我演講,也有人在閱讀我的書之後寫信給我,我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他們之中有些是香港人,原先覺得自己相當了解香港的歷史,結果出乎意料地發現他們還漏掉了更多新的細節。當然還有許多是跟我處境很類似的人,他們有的是混血兒,有的在香港長大,或在香港住過數十年,或是有家人住在這座城市,如今我們都因為失去了一個「家」而感到失落。
然而,無論我們身在何處,為自己發聲依然深具力量。某一次我到紐西蘭參加活動,地點位在奧克蘭市中心一個著名的劇院,這個空間宏大無比,我光想到自己要站上那個舞台就超級緊張。當我從舞台上向觀眾席望去,我看見席間坐滿了紐西蘭民眾,其中大多是中產階級的中年白人。但是在演講後的問答時間中,有四位彼此不認識的香港人站起來分享了他們自己的經歷。他們都在討論他們失去的東西,他們的每一字一句都是在挑戰中共強加的敘事控制。我聽著他們的分享,感受到這個空間的情緒愈來愈滿。就在座談結束之際,突然一句呼聲從大廳的後方響起,迴盪在整個空間:「香港人加油!」
這句話其實被我原封不動地印在書封上。這本來是一句在歡呼的時候喊的加油口號,後來變成了抗議的口號,如今,這句話被貼上了煽動的標籤,面臨香港政府的審查。幸而隨著每一本售出的書,每一本流通在圖書館的分身,我們心中那微小但重要的反抗意志、彼此相繫相持的希望和心願,將繼續傳達到世界的每個角落。香港人加油! ( 林慕蓮,中文版序 )
前言
我蹲在香港一座摩天大樓的屋頂上,陽光火辣辣地烤著我的頭,汗水滴進我的眼睛。我正在描畫一幅大概有八層樓高的抗議布條,而且寫的詞彙還全都是粗話,不禁讓我以為自己是否已經決定轉行不當記者了。熱浪在空氣中翻騰,眼前密密麻麻的屋頂緊密相依,像極了俄羅斯方塊。我上來樓頂是為了採訪一個祕密的藝術合作組織,他們專門繪製支持民主的巨大直幅標語(香港稱為「直幡」),並且以打游擊的方式掛到香港的山峰上。我在旁邊看著看著也忍不住手癢起來,跟著拿起畫筆加入他們。
這是二○一九年的秋天,中國國慶日前一天。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明天它將慶祝七十週年紀念。好幾個月來,數以萬計的人走上街頭示威,這是香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反政府抗議運動。在歷經一百五十五年的英國殖民之後,香港於一九九七年回歸中國,實現了史無前例的主權移交。雖然當時北京承諾,在二○四七年之前,香港可以繼續原來的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但是現在中國正威脅通過立法,背棄當初的承諾。
這群祕密書法家一直忙著部署他們的攀岩隊伍。他們都是選在深夜的時候攀上香港的懸崖峭壁,因為這樣等人們早上醒來,就能看到巨大的標語,敦促他們「上街反惡法」或「保衛香港」。在局勢低迷的時候,這些巨大布條幫忙重振抗議運動的士氣。我打從心底佩服這些標語製作者的大膽和勇氣,可惜我一直不知道他們是誰,也不知道如何聯繫他們。有人知道我對他們相當著迷,那天早上突然通知我,邀我到現場看他們怎麼組織行動。這麼千載難逢的機會,我當然一口答應。
我們所在的頂樓超級曬,但是位置夠隱密,空間也相當寬敞,足夠讓巨大的布條整個攤開來乾燥。現場聚集了七位標語畫家,我答應不透露任何可能暴露他們身分的細節。不過最讓我驚訝的是,我原以為這些人會是一些年輕的運動者,結果沒想到是一群有點年紀的男女,而且他們工作期間幾乎不發一語,默契十足,顯然對彼此相當熟悉。他們迅速地攤開一片厚厚的黑色棉布,然後輕踏著腳步將布整平,看起來像在屋頂上跳一首輕快的集體舞蹈。接著,他們沿著邊緣放上石頭固定布料。然後,一位年長的書法家拿著白色粉筆,開始在布料上勾勒四個巨大的漢字輪廓。他的動作流暢而優美,像極了舞動的毛筆,在布料上輕盈地移動。
最後一個漢字現形時,我忍不住噗哧笑了出來。書法家在這幅布條精心繪製的四個字是:「賀佢老母」,乍看之下字面上是在說「恭賀他的母親!」但實際上是借用了廣東話常講的髒話「屌你老母」,非常粗俗難聽,差不多等同於「幹恁娘」的意思。布條的標語其實是在罵「賀你媽的國慶活動啦!」這不僅是挖苦北京即將舉行的大型軍事閱兵,也是在強調香港人不認為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這句口號像一記大不敬的耳光,雖然聽起來像半開玩笑,但極有可能惹上大麻煩,繪製標語的人如果被抓,是很有可能坐牢的。
看著他們拿起油漆罐,靜靜地蹲在布條旁邊塗顏色,我在心裡與自己天人交戰。幾個月以來,我的兩種身分不斷地在拉扯著我,我不僅是香港人,也是一名記者,努力地想遵守報導的中立原則。但是,隨著我所熟悉的世界逐漸崩解,一切都變得不再確定,要繼續保持中立變得愈來愈困難。從表面上來看,這座城市仍然活力充沛,熙來攘往的人群在摩天大樓林立的街道上湧動,過斑馬線的時候提示音會嗶嗶作響,頭頂上的LED招牌爭奇鬥豔搶奪目光,空氣中的氣味融合了中藥店刺鼻的魚乾腥味與攤販濃郁茶葉蛋的桂皮香氣。但是,在這些紛沓嘈雜的感官感受底下,這個社會的運作機制正在改變。我無法再撇開眼。
警察不再是保衛人民安全的人,而更像施展暴力的暴徒,隨意毆打或逮捕在街上的孩子,那些孩子可能只是剛好穿了特定顏色的衣服,或者在特定的時間出現在特定的地點,有時甚至無緣無故。法院不是中立的法律仲裁者,而是有自己的政治判斷和行動,它們會取消民選議員的資格,監禁和平的抗議者。政府官員不再是制定和執行政策者,不再直接與人民互動,而是躲到幕後去不讓人看見,僅由警察代表它們對人民施加暴力。一夜之間,世界整個天翻地覆。
各種已知的交戰規則似乎不再適用,連新聞工作也是如此。警察非但沒有把記者當作平民一樣保護,還特意專門攻擊記者。他們朝我們噴胡椒噴霧,丟催淚彈,對著我們使用高壓水槍,洗不去的藍色化學藥劑灼痛了我們的身子,他們還將槍口對著我們,毆打我們,逮捕我們。我們原本都穿著標有「記者」中英文字樣的螢光背心和頭盔,但我們很快就注意到,這反而讓我們的頭部和身體成了最顯著的攻擊目標。
香港地狹人稠,到處是迷宮般的公寓大樓、密集的巷弄和市場,幾乎很少人不被政府針對抗議動用的強力鎮壓手段波及。近九成的民眾曾被催淚瓦斯熏過,比如只是夜半出門買魚蛋粉當宵夜,或是週日下午沿著海濱散步,甚至只是坐在家裡頭,街上刺鼻的煙霧就飄了過來,從窗戶的縫隙或是空調的通風口滲進屋子。香港有三分之一的居民出現創傷壓力症候群。有時候感覺就像這個政府正在對著人民發動戰爭。
這段時間也深深影響了我個人的層面。我是哪裡人的這個問題,對我來說一直很複雜,因為我是個中英混血,雖然出生在英國,但在香港長大。我五歲的時候,因為我新加坡的父親要擔任公務員,舉家搬到了香港。自我有記憶以來,香港一直是我的家。雖然我並不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但我是香港製造的。香港人擁抱的那份刻苦耐勞的精神和頑強的毅力,也在我的血液裡流淌。香港人將其稱為「獅子山精神」,這個名字取自香港電台製作的一系列電視劇,故事真實反映了獅子山山腳下,香港基層市民的生活境況。由於這個小山頂的岩塊像極了一頭蹲踞的獅子,因此被人稱為獅子山。對我來說,所謂獅子山精神,就是無懼對手有多強大,我都願意為了保護自己在乎的價值而戰鬥。
我曾經在中國生活並從事記者工作十年。我內心的某種愧疚感驅使著我,去寫下我認為需要公開講述出來的故事,無論那些故事在政治上有多麼敏感。我離開北京時開始寫一本書,一本關於中共如何在一九八九年血腥鎮壓抗議運動,以及它如何成功地將這些殺戮從集體記憶中刪除的書。我很清楚,這本書會讓我很多年都不能再回中國,但是我也同樣清楚,這是一個必須講述出來的故事。在新聞報導方面,我很常碰觸也很擅長報導抗議運動,但我從未想過,有一天會有一場運動如此全面地影響了我所鍾愛的家鄉。當這件事開始發生,我毫不猶豫地決定要報導它。我在墨爾本新聞系教課,有一段時間我請了研究休假回到香港。抗議活動爆發時,我就住在香港。休假結束我又回澳洲教書,但我定期飛到香港進行短期報導,直到新冠疫情封鎖了我們的邊界。
在這種種情況之下,要如何做出合乎道德的新聞報導呢?到目前為止,我一直無條件地遵循公認的新聞報導做法,盡可能地將自己從故事中抽離。但是,如果我已經是那個故事的一部分了,我還有辦法做到這點嗎?我為此苦苦思索了好幾個月,沒有得出明確的答案。
那天在屋頂上做採訪,這個問題其實迎刃而解。我知道所有該繼續當旁觀者的理由,但我也知道我不會這麼做。我的內心驅使我站起來,走過去為自己拿起一個油漆罐。我知道我正在越線,從恪守中立原則的記者,變成一個自願參與其中的抗議者,這麼做違反了二十五年來我所遵從的新聞專業倫理。但那一刻我也意識到,我其實並不在乎。我並不同意抗議運動所做的每一件事。我本能地反對任何使用暴力的行為,無論警察使用了什麼手段,我只要看見抗議者朝警察扔磚塊或投擲汽油彈,內心依然會感到驚駭。但是隨著抗議活動展開,繼續當個順民安守本分的想法每一天都在瓦解。我們永遠只能活在當下,未來充滿了各種不確定性,無法事先預知,而過去也已經變得無關緊要。因此,我為自己拿了一罐油漆,將刷子蘸入黏稠的白色油漆中,成為了團隊的一員。
我從「賀」這個字開始幫忙,一開始並不是相當有趣,因為這基本上像在玩放大版的著色本,你必須照著限定的範圍內塗滿顏色,只不過範圍大上好幾倍。這工作並不難,但我的手有點抖,我必須非常專心才不會超出線條。太陽熱辣辣地烤著我的脖子後面,額頭上的汗珠時不時滴落到布料上。但是漸漸地,著色讓我整個人像進入了冥想狀態,我的所有心思都專注在手上這份小任務上,完全忘記了應該採訪其他人。「文字的力量」深深地攫獲了我。
與此同時,還有另一件事情默默牽引著我。多年來,我一直對某位身世成謎的人物深感著迷。沒有人料到他後來會成為本土的偶像。他曾在垃圾站工作,有著一口殘缺不齊的爛牙,經常打赤膊,精神健康也有問題。但是他在公共場所留下了寫得歪歪扭扭、像小孩子學寫字的書法之後,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起初人們會謾罵他,到後來開始追捧他。他的本名是曾灶財,但是每個人都稱他為「九龍皇帝」。多年來,曾灶財深信九龍半島凸出的那塊土地是屬於他家族的財產,但是在十九世紀被英國人給偷走了。他想像自己是大片土地的統治者,統領範圍甚至擴展到香港島和新界。沒有人知道為什麼他會這麼相信,但是他的信念變成了一種狂熱。
一九五○年中期,九龍皇帝瘋狂地到處留下他的書法字跡,指責英國偷走了他的土地。除了控訴的內容,他還費盡心思寫下他家族總共二十一代人的族譜,有時不僅寫下名字,還寫下失去的地名,偶爾出現大罵英國女王的粗話。九七年以前,他抨擊的對象是殖民的英國政府,九七年英國將香港歸還給中國之後,他改為針對中國。
九龍皇帝書寫的地方不是紙張,而是揮著狼毫筆在他失土的牆壁和斜坡上,像皇帝一樣留下墨寶,主張自己才是這塊土地的主人。他精心挑選自己落筆的地點,他只在皇室的土地,或是主權移轉後為政府所有的土地寫字。他特別鍾愛電箱、柱子、牆壁和高架橋的橋墩。在那些舟車勞頓的通勤者和疲乏倦怠的退休人士眼中,他的文字像在變魔術,本來前一天還在,隔一天便消失了,原來是被一群穿著橡膠靴,帽子上披著薄毛巾遮陽的政府清潔人員洗掉或用油漆覆蓋掉了。但是,一夜之後,他的文字又回來了,好似從未消失過,宛如在玩一場打地鼠遊戲。而且這個打地鼠遊戲持續了半個世紀,遍及香港各地。
明明九龍皇帝的書法寫得極糟,但是卻帶來了相當大的迴響。他只接受過兩年的正式教育,他寫下的每個字都讓人看出他幾乎是個文盲。他歪扭蹩腳的字體暴露了所有缺點,真正的書法家會試圖遮掩,但是讓人印象深刻的也是這些缺陷。他的字跡展現出某種原創性,大方承認了人類的不完美,像是在鼓舞人們勇敢說出「我他媽的不在乎」。他打破所有的規則,拒絕傳統中國文化的約束。這部分其實也是很香港。香港就是一個過渡的中間地帶,一個充滿各種越界的地方,同時也是一個避難所,接納甚至頌揚那些在中國大陸不被接受的異議分子。
二○○七年,九龍皇帝因心臟病駕崩了,他生前在公共場所總共創作了大約五萬五千八百四十五件的作品。多年以來,他的字跡慢慢寫進了我們的腦海中,連同日常生活中軍綠色的天星渡輪和摩天大樓天際線,一起成了香港身分認同的一部分。對許多人來說,他們無法為自己發聲,而且會本能地感到不適,九龍皇帝的作品第一次表達出他們的處境。「這有點像我們的政治現況,」一位評論家這樣告訴我,「土地曾經屬於英國,現在屬於中國。它應該屬於中國,但大多數香港人不認同中國政府。某種程度上,他們仍然認為香港是一個殖民地,是中國的殖民地。所以曾灶財做的事情,其實就是他們想做的事。」九龍皇帝說出了他子民的心聲。
二○○七年他過世了,報章媒體同聲地哀悼。九龍皇帝駕崩,每個人都懷念他。……九龍皇帝駕崩,他的人民在哭泣和哀號。……九龍皇帝駕崩,他的墨寶是充滿詩意的傑作。……九龍皇帝駕崩,筆者感到難過,香港失去了一位傳奇人物。……九龍皇帝「駕崩」後由誰承繼呢?他的作品從街頭消失,但也開始出現在蘇富比的拍賣場,而且價格一路飆升,成為了香港最有價值的藝術家。
幾年前,我腦中閃過一個念頭,我想要寫一本關於九龍皇帝的書。雖然這顯然吃力不討好,但我卻始終放不下這個念頭。他的家人一直拒絕接受記者採訪,關於他的具體事蹟少之又少。但我依然固執地展開我的探尋之旅。我跑遍建築工地、公共房屋,也去了新界的村莊,試圖找尋任何曾經認識九龍皇帝的人。我在香港生活了四十年,這些地方卻是我第一次拜訪。在這個過程,我看見了許多不一樣的香港。我成長的香港是一個在泡泡中的泡泡,我這趟追尋九龍皇帝的旅程打破了那個泡泡。
我費盡心思找到了一群古怪的人,有人曾跟著九龍皇帝一起塗鴉、有人唱過關於九龍皇帝的歌、有人寫過九龍皇帝、或甚至只是知道他。我開始注意到,這個故事愈來愈背離了我原先的想像。一開始我的目的只是想確認,他主張自己擁有土地所有權的這件事是否為真。我原本認為只要做夠多的採訪,就能還原出具體的細節。但是所有的受訪者幾乎在所有事情上都有各自不同的詮釋跟理解,就連對於目前現有、少量的傳記資料,或是他是否患有精神病,大家的想法都有很大的差異。更糟糕的是,他們在採訪中花了很長的時間在相互攻擊。我平時使用的新聞採訪技巧,全都派不上用場。
與此同時,隨著我深入挖掘九龍皇帝的故事,我也更加了解香港的故事。為了確認他的土地所有權主張,我開始研究英國殖民者如何占有和徵用土地。我很快意識到,為了理解這些事情,我還必須理解香港是如何變成英國殖民地,這段歷史非常的錯綜複雜。我原本沒有打算爬梳更古早的歷史,但所有對九龍皇帝感興趣的人都不斷談到宋朝的男孩皇帝,他們在十二世紀的時候逃到了香港。最後我也開始對香港殖民時期之前的歷史產生興趣,這段歷史可以追溯到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中期。不知不覺中,九龍皇帝帶領我回到了歷史最初的地方。
在這段追尋之旅中,我認識了許多香港不為人知的故事,包括創世神話和傳說、真實和虛構的歷史、從紀錄中被抹去的反抗故事,以及未曾有人講述的勇氣故事。這些故事改變了我對香港歷史的看法,因為我之前一直認為,香港歷史非常簡單易懂,只不過是一連串板上釘釘的事實所拼成的敘事。但真實的歷史並非如此,那些被隱藏起來的歷史,挑戰了過去那套國家強加的單一敘事,乘載著不同的觀點與色彩。它們將香港人放在故事的核心,甚至將香港人重新納入有關主權移轉的關鍵談判之中,重新挖出過去這些香港最重要的聲音。這些隱藏的歷史讓我了解,近年來的各種起義行動並非孤例,而是延續長久以來強占與反抗的故事。這也是我最終寫下的故事。
不過,儘管我的書寫焦點轉向了,但我也發現九龍皇帝已經深深影響了我,他成了我觀看香港故事的稜鏡。就像稜鏡將白光折射出彩虹一樣,在二○一九年大規模街頭抗議運動展開之後,九龍皇帝的故事也折射出各種各樣的敘事,以我未曾預料的方式照亮了香港。無論是九龍皇帝的故事,還是抗議運動的發展,都是小小的大衛對抗鋪天蓋地的歌利亞,都是用渺小的生命對抗無理的強權。無論是抗議運動的發展,還是九龍皇帝的故事,都變成了誰有權力抹除香港,誰有權力講述香港的故事。綜觀整個歷史,香港人在官方的歷史紀錄中不是被邊緣化,就是被整個抹除。香港人從未能夠自己講述自己的故事。唯獨這位可憐又悲傷的老皇帝是例外,作家馮敏兒曾說,他是「香港最後一位自由人」。
對我而言,九龍皇帝意料之外地從我原本要寫的主題,變成了寫作的指路明燈。香港政治的陀螺不斷地旋轉滾動,我注意到這之間有個規律。每次有重大事件發生,我往往已經認識其中的關鍵人物,而且都是在我追尋九龍皇帝的途中認識的。二○一六年,一位名叫陳雲的大學教授,因為直言不諱地發表政治觀點而被大學解雇,我記得他是一本關於九龍皇帝的書中第一篇文章的作者。二○一四年,雨傘運動持續占領街頭十一個星期,訴求更全面的民主。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因為參與雨傘運動而受到審判,在那之前我已經認識她了。因為我們都同樣對九龍皇帝感興趣。二○二○年,香港最受歡迎、專門諷刺時事的電視節目《頭條新聞》,因為涉及政治內容而被喊停,我寫信慰問節目主持人曾志豪。他曾寫過一篇關於九龍皇帝的報紙專欄,我去採訪他之後跟他成為了朋友。有時候冥冥之中,九龍皇帝引領著我走出荒漠之地,帶領我去認識了香港最有趣的思想家。
這些事情都並非巧合。那些思考過或書寫過九龍皇帝故事的人,都必須面對九龍皇帝最在意的議題:領土、主權和失去。在其他人連想都不敢想的時候,九龍皇帝就公開提起了這些問題。他為自己取名叫九龍皇帝,這個名字本身就是對香港殖民者的當頭訓斥。他才是最初的主權者,九龍是他的土地;他是乩身,是說真話的人,是神聖的苦行僧。
隨著年月過去,這本書愈來愈難寫。二○二○年六月,北京試圖訂立香港的國家安全法,這本書中寫的主權和身分認同,在政治上突然變得非常敏感。任何關於主權或自治的討論,對法律來說就是意圖在搞分裂。倘若九龍皇帝活到現在,大概會被視為國家安全的威脅。香港人持續不斷的反抗,無論這個反抗有多麼微小,都是在追隨著已故的九龍皇帝的腳步。
今日的九龍皇帝是誰呢?是昔日那些住在圍村裡,擁有這片土地的古老氏族嗎?是那些改變了城市面貌的摩天大樓裡的跨國公司嗎?還是那些遠在北京,試圖透過立法和武力,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香港人的共產黨領導人呢?或者,是那些用自己的肉身占領九龍半島街頭,試圖奪回屬於自己的歷史和空間的平民百姓?如果故事是一枚稜鏡,那麼我們選擇從哪個角度切入,就會決定我們看到什麼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