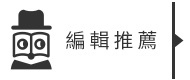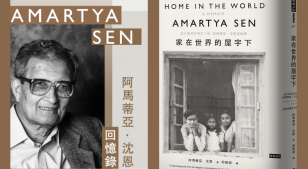序
我最早的兒時記憶之一,就是被船隻的汽笛聲吵醒。我那時候才快三歲。那汽笛聲嚇得我馬上坐了起來,我爸媽一直安慰我沒事,我們只是從加爾各答沿著孟加拉灣要航向仰光而已。我父親原本在現今劃屬孟加拉的達卡大學(Dhaka University)教化學,這趟旅程是應邀到緬甸的曼德勒(Mandalay)擔任三年的客座教授。我被汽笛聲吵醒的時候,船已經順著恆河從加爾各答往海上航行了一百哩遠(當年加爾各答還是個大船可以停泊的港口)。父親告訴我,接下來我們要出海航行好幾天,才能抵達仰光。想當然,我當時根本就不懂什麼叫做出海,更不知道人們有那麼多種方式到各地旅行。但是我那時確實有一股展開冒險的感覺,對於我前所未見的大場面感到無比興奮。孟加拉灣的海水是那樣的湛藍,就好像是從阿拉丁神燈裡倒出來的一樣令我目眩神迷。
我記得最早的事幾乎都發生在緬甸。我們家在那邊住了三年多。有些事物對我仍是歷歷在目,像是曼德勒的美麗宮殿、宮殿外頭那條迷人的護城河、伊洛瓦底江兩岸的風光景致,還有我們處處可見的寺廟塔樓。曼德勒留給我的印象是那麼優雅美麗,但在別人口中卻是骯髒汙穢的模樣,我想,就連我們當時住的那間傳統緬甸房屋也同樣在我的愛意渲染下格外漂亮了吧。但說真的,我當時確實是快樂無比。
我從小就開始四處旅行。在緬甸度過了童年時期後,我回到了達卡,但接著很快又搬到了桑蒂尼蓋登(Santiniketan)去就學,著名的大詩人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在那裡創辦了一所實驗學校。包含我在內,我們一家子都深受泰戈爾的影響。我這本回憶錄的書名就是借用了他的《家園與世界》(The Home and the World),可見他對我的影響有多大。
在桑蒂尼蓋登的泰戈爾學校認認真真地讀了十年後,我又搬到了加爾各答去上大學。我在加爾各答認識了不少好老師和好同學,課餘之暇,我們還經常到大學隔壁的一家咖啡廳裡討論爭辯。之後我就到了英國劍橋,這一趟走的同樣是迷人的海路,只不過改從孟買出發到倫敦下船。劍橋這地方以及我就讀的三一學院所傳承的輝煌歷史,深深叫我心蕩神馳。
接著我又到了美國,先在麻薩諸塞州的劍橋麻省理工學院教了一年,然後又到了加州的史丹佛大學。我在輾轉四處的期間也曾好幾次想落地生根,最後又回到了印度(途經巴基斯坦的拉合爾與喀拉蚩),在德里大學教授經濟學、哲學、賽局理論、數理邏輯,以及——相對嶄新的——社會選擇理論。歷經這三十年的前半生,我成為了一個兢兢業業的年輕教師,期盼著人生接下來更新、更成熟的另一個階段。
在德里落腳後,我開始有時間可以省思這豐富多采的早年經歷。我認為要思考世上不同文明,共有兩條截然不同的進路。其中一條是採取「碎片式」觀點,把紛呈萬象都當作是不同文明的具體展現。這條路子認為不同碎片之間彼此敵對,近來可說蔚為風潮,恐將延續「文明衝突」的看法。
另一條進路則是採「包容式」,專注在從各種不同展現裡找出最終那個文明——也許可以稱之為「世界文明」——開枝散葉的證據。這本書當然不是要研究文明的本質,但是各位讀者可以看得出來,我對世事還是比較傾向於包容式的理解。
從中世紀十字軍東征到納粹在上個世紀的侵略,從鄰里衝突到政教戰爭,各種不同信念之間總是爭鬥不斷,但是也總有一股包容求同的力量來抵抗衝突。只要睜眼看看,就能發現族群與族群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總能彼此體會諒解。行遍天下,更會處處發現指向追求寬大包容的各種蛛絲馬跡。千萬別低估了我們彼此切磋學習的能耐。
人生大樂之一,就是能有人彼此切磋相伴。西元十世紀末、十一世紀初,曾於印度居住多年的伊朗數學家阿爾-畢魯尼(Al-Biruni)在他的《印度史》(Tarikh al-Hind)中曾說,彼此學習,不僅共享知識,更能共存共榮。他介紹了印度在一千年前就發展出來的數學、天文學、社會學、哲學與醫學,更證明了人類確實可以透過友誼而擴增知識。阿爾-畢魯尼對印度人的那份親暱讓他對印度數學與科學產生了興趣,成為了數學與科學專家。不過儘管親暱,他還是不免要對印度人打趣一番。他說,印度人的數學非常好,但是印度學者最了不起的才能卻是另一點:他們總是能夠把自己一無所知的東西說得天花亂墜。
如果我也是這樣,那我會對自己這種才能感到自豪嗎?我不知道,但是說不定我應該從只說自己確實知道的事情開始。這本回憶錄就是這份努力的小小嘗試,無論我談的這些事我自己是不是真的知道,但至少總是我的親身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