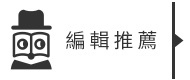前言
移動的指標
有時候我在想,人生的上一個階段與下一個階段,是否都會有隱微的關聯。這裡想說的是居住地。老家在桃園龍潭,儘管不是在那裡出生,但人生至此前半段幾乎在那兒度過。龍潭是台灣十大名茶產地之一,茶園是我很熟悉的地景,家附近也有不少製茶廠,雖不致於過分浪漫地說我在茶樹間長大,但是看到一畦一畦的茶作還是感覺像家。
大學到木柵讀書,又是另一個茶產地,文山包種、木柵鐵觀音,名氣更響亮,上貓空泡茶聊天是當年大學生偶有的休閒,學校每年舉辦包種茶節雖然與農產無關,但到底是想牽扯一點在地特色。我在木柵住十多年,出門在附近活動,來來去去經過許多老茶行也是很慣習的事。
我是一個對住所相當固著的人,若非搬來香港,彷彿就會一直在木柵住下去。人生前三十年都在茶鄉的意義是,我很適應安靜邊緣的位置,就像血型A的人一進到空間裡,要找靠牆的座位才感到安心。我不介意每次進入市區、前往核心地帶都必須移動,反而有點需要那段轉換的過程。後來我跟一個遠方的人戀愛,每次見他,得花上半天的時間,搭車、搭飛機,移動得更長、更遠,也不覺厭煩。我把自己固定在一個偏僻的地方,可能潛意識就是喜歡在移動這樣看似無意義的事情上浪擲時光。
搬來香港前,在木柵的一間公寓住了六年,巷口斜對面是一座加油站,一旁不遠處的公車站則有一間葬儀社,每天出門上班,都在那間葬儀社前等公車。有時我覺得無所謂,有時又莫名感到介意,特別是當它偶爾有生意上門的時候,大門敞開,靈堂直對著你,死者的照片盯著等公車的人背脊發涼。我常常想不透那間葬儀社為什麼會開在這裡,以它生意清涼的狀態看來,大約是自宅家族事業,但附近完全不見相關產業,離殯儀館也有段距離,根本沒有聚集經濟的效益,真是這個社區很特殊的存在。
結果,抵港後的第一間住所,加油站就在公寓樓下的大馬路上,附近全是殯葬業,棺材、骨灰罈、花圈、紙紮人一應俱全,每天遠遠地還看得到殯儀館裊裊的白煙。事至此,已經沒什麼好介懷的了,甚至有點明白為什麼我在木柵的家附近,會有一間突兀的葬儀社。它彷彿一直是下一個居住地的指標。
我與觀世音菩薩向來有緣,紅磡正有一間歷史一百五十年的觀音廟,那裡幾乎成為我頭幾年在香港的心靈支柱。
紅磡觀音廟建於同治十二年(西元一八七三年),信眾以街坊鄰里居多。這一百五十年來,雖曾重修,但也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至今仍屹立不搖。二戰時,有一則軼聞,據傳當時盟軍瞄準紅磡黃埔船廠,果有一日轟炸紅磡區,街道民宅面目全非,唯有觀音廟全身而退,外頭死傷慘重,而躲藏於廟內的百姓安然無事,眾人皆言觀音顯靈護祐。
我總是對這種帶有神祕色彩的小故事著迷,更重要的,初來乍到異鄉,不遠處就有一位熟悉的長輩照看著你,安心不少。後來,每有身心動盪,或遠行前求平安,甚至是尋覓新屋這類雞毛蒜皮的小心願,總會厚顏無恥地去叨擾香火鼎盛的觀音娘娘,祂老人家雖不至於把我寵壞地有求必應──像是我許願找到一間鋪有木地板的房子,便嘗試兩回才成──但實在是把我和另一半這個小家庭照料得穩妥,我倆在紅磡住得安逸,賴著不肯遷去別區,祂便一次又一次為我們在最佳時機覓得安身處所,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好。
落定紅磡的前半年,由於人生地不熟,社交量極少,幾乎不太離開居住的區域。但心思卻常常移動回台灣,看著朋友們在台灣各地工作生活、旅行走動,看著他們去了什麼有意思的地方,就記錄在我的地圖上,想著有一天自己可能也會去。雖然搬至亞洲的心臟地帶,卻彷彿來到距離過往核心更遙遠的座標。那段日子每晚都做夢,白天的日常刺激太少,夜晚的潛意識便高速運轉,家人、朋友、甚至是久沒聯絡的故人,輪番出現在睡夢中。我很喜歡香港的生活,但原來脫離母體的那種不適,難免久久不散。
也是因為這樣回溯過往居住地之間的關聯,忍不住想著下一個地方會是哪裡,紅磡這個老老的街區會給我線索嗎?神遊回台灣會更費力嗎?移動,或許會是一輩子的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