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黑色玻璃
前陣子日環食在美國西部出現,我的社群上到處是人們轉發的奇形怪狀的樹影——原本飽滿的光線遭陰影遮蓋,於是落在地上的影子就像新月一樣又尖又細,好像誰勾勒出來的素描畫。在這事件當中,人們著迷地看著原先日常裡固有的事物,它們變形了,混入了異樣與陌生,恍若有人趁他們不注意時對現實施展了幻術。人們集體上街,帶著一塊塊黑色玻璃、黑色壓克力等工具出門,興奮地期待著。不過撇除掉日食本身與其所被遮擋的光線外,光是有一小段時間聚集大量人潮、透過一片片黑色去觀看就已足夠不可思議。在等待的期間,人們拿著那黑色玻璃到處張望,於是戀人的臉變成了黑灰色的、嬰兒的微笑變成了黑灰色的、老人家坐在陽臺悠閒曬太陽的身影變成了黑灰色的。就這麼一次,人們對於這遮擋世界的顏色有了容忍與覺察。
擁有重新注視的目光其實相當珍貴,正是因為這種注視,我們才能從無數習以為常的生活裡找到驚奇之處、擁有感悟與反思。這種再注視也是在這本詩集裡所追求的。不過日食能夠被預告、經由科學家計算,還能得知會出沒在哪個特定的位置,在其他沒有日食的日子裡,我們要如何擁有這樣的目光?我想詩是那一塊塊的黑色玻璃,在平常日子裡,人們拿著這樣的東西不知所措,但總會有藉此將什麼看得更清楚的時刻。
《醒來,奶油般地》這本詩集中,我以三輯各自寫了不同的主題,「骷髏狀的人馬」寫我在都市裡的生活感受與打工時期的所思,「身體群像」則關於我的身體經驗,而「無法複製的局部」寫那些與我共生的自然,也就是只有能親眼見證的一切。
我告訴我的母親第二本詩集即將出版了,她則問這個書名是什麼意思?我說生活就像煎鍋上的奶油一樣,很快就會燒焦,是一邊醒來一邊感到痛苦的意思。她似乎對於我有這樣的感受感到詫異。在母親眼中,生活或許是相對單純的吧,上班之餘排休,去探訪家人或出門走走。到頭來,我才是那個想得太多而到哪裡都格格不入的人。我的幸福注定與我的痛苦相互滋長,因著我以梳理苦厄為生,言說才讓我有了一絲絲存在的位置。
從工作回學校念書的第一年,我到飲料店打工,展開了為期一年半工半讀的日子。這並不是我第一次打工,卻是在餐飲業做得最久的一次。我的母親在我約莫高中時重返就業職場,就此開始了在餐廳工作的日子。餐飲業的共通特性是,你需要在一般人用餐之前吃飯,為此午餐和晚餐的時間被打亂了,你尚未感覺到飢餓,卻總是必須先胡亂往胃裡塞點什麼,因為待會可沒有時間吃飯。是以,在打工的日子裡,我不禁感覺到我與她是共享著同一副勞動的身體。
我們都是動作很快的人,我以我的敏捷與能幹為傲,不過長時間的磨耗或許跟人的意志無關。當然我的母親辛苦多了,且我與那些在勞動現場擔任正職工作的人經驗仍差遠了,然而儘管於此,我仍感受到一種矛盾是,當我的雇主讚頌著這些大量重複性的勞動時,我感受不到具體的意義。
如何在看似被動的狀態中持續維持著自己的主動性?我想這是作為受雇者的普遍難題。然而這也很難說單單是雇主的責任,社會結構所建構的價值觀與之環環相扣。我遇到的雇主的確都是不錯的雇主,才能還算是維持了一年之久的打工生活。但這些受雇者值得擁有一個更好的環境條件嗎?一定是的。
在輯一「骷髏狀的人馬」裡,我還延伸談及了諸多不同都市裡的角色,例如必須常常趕路的送貨員、從辦公大樓走出來偷閒的上班族、從市中心移動到郊外的捕狗者,等等。我希望這些聲音能呈現出更多的非我感受,但也深知其中帶有偏好與揀選,是不足的部分。另外一些則是以寓言方式書寫,寫這些急速流動的時間所招致的:焦慮、恐慌、壓抑,與無時無刻磨耗著我們的城市價值。我自己至今仍未有解方,卻透過捕捉隱蔽於日常的這些存在,我知道我是待在了什麼樣的位置。
輯二「身體群像」一開始是想寫女性經驗,然而越是朝這方面發想,越有種自我刻板化的束縛。我自己作為一個女性,還要在乎什麼樣寫出來的東西才可以被歸類為女性書寫嗎?這種反思在二〇二三年六月的#MeToo事件中變得迫切與強烈。七月,我在《自由副刊》發表了一篇散文,〈應在場的不在場〉,處理自己在這場運動中的觀看與困惑。而回到詩集中,我希望藉由我書寫自己的身體經驗去擴展女性書寫這樣的標籤,我在曬衣場進行勞動的身體、和朋友們溯溪變得冰涼的身體、在圖書館進行漫長閱讀的身體……這些都是我經驗的一部分。於是,除了那些只有在女性身上會發生的事,我也寫了同時是會在所有人身上會發生的事。
本輯中的〈讓藍色樹蔭吃了悲傷〉、〈白色閃光,一瓣瓣〉、〈站立紅泥之中〉這三首詩,其實是奇士勞斯基的電影「藍白紅三部曲」所啟發,但寫著的過程中已與電影無關,與「自由、平等、博愛」三個原先電影的主軸更沒有連結。除〈讓藍色樹蔭吃了悲傷〉這一首算得上是與《藍色情挑》相符,寫一個從逃離悲傷到坦然面對的過程,後兩首詩基本已脫離原有電影情節,是我自己另外發想出來的故事,為的是想呈現女人主動訴說、行動、改變的一面。思及至此,能不能與電影完全扣連就變得不那麼重要了。
在花蓮唸了四年書,真實地感受到什麼是會黏人的土地,也如當初學校的老師們所說,從這裡帶走的絕非只有美好的記憶,還有一種面對土地的態度。如今在大臺北也居住了四年了,已經從無法適應的動盪,轉化成了觀察城鄉之間的變化與差異。二〇一九年結束從波蘭的交換回臺後,我發現對於自己所居住的島嶼十分無知,又因為一些契機接觸到了公視《我們的島》這個節目,進而開始關注環境議題。二〇二二年春天,我曾加入荒野保護協會的解說員訓練,為的是想對環境有進一步認識。後來雖未持續參與,卻有幸認識一群熱愛環境的民眾,藉由他們所帶領的走讀,理解到了臺北也並不只是個都會區,其中的濕地、郊山,甚至公園,這些假日散心之處所擁有的生態,是平時沿捷運線、大馬路的我們所未可見,卻真實存在於這片都會區中的。
作為環境議題的初學者,我想,去顧及所有面向是困難的,卻仍想書寫那些所從中領略到的、觀察到的事物。我常告訴朋友傍晚天未暗的空中有蝙蝠,而他們會說:「真的嗎?」我則繼續說道那些蝙蝠可能住在停車場、地下室、水管,牠們飛行的路徑跟燕子不一樣,光看飛行軌跡就可以看出。我也曾在父親開車行經北海岸的路上指認出一隻老鷹(我沒有厲害到認出確切的種類),而父親一樣是驚訝且懷疑地看著我說:「真的嗎?」我如何能告訴這些人,我們以為的自然,其實就在身邊不遠處,而非以為的遠方呢?
「無法複製的局部」,那其中意思是,我認為自然的體驗是無法輕易藉由文字、攝影、繪畫等方式所重現的。當我試圖描繪一朵花在路邊所帶給我的感動,無論當下的感受有多麼具體,訴說之很容易只是自顧自地耽溺。是以我想,書寫這些也成為了最困難的地方。其中的得獎作〈廢田,冷海,曠野中的白矢〉,有賴於《上下游新聞》的〈【重磅調查】大風吹,吹什麼?風電重擊的海口人生〉這篇深度報導。這些記者費時一年,訪問了當地居民、漁民等,並同時借鏡英國經驗,試圖提供其解決的辦法。我希望他們所宣揚的價值被看見,於是寫了這首詩。我無疑是相信綠電的必要性,然而我們在興建相關措施,或者任何「有益於公眾」的建設時,是否能更加細緻地執行呢?臺東紅葉村就曾花了半年時間與地方居民溝通,重新將溫泉與地熱產業結合,我想成功的例子還是有的。
創作這本詩集的時間較為集中,絕大多數都是這兩年間所創作。輯一的半數寫自於臺灣文學基地駐村時,輯三先於輯二,是在二〇二三年春天完成,輯二則是多半於當年七月在臺東短居時所作。其中混入了少許前一年的作品,我將之打散於各處。
這本詩集的完成,首先要感謝顧玉玲老師,是她讓我在北藝大這一年多以來的時間有了相當大的啟發。從我們如何思考記憶到面對社會議題該秉持著什麼樣的態度,回到研究所在課堂間的對答每每使我回味許久。謝謝俞萱在二〇二二上半年開始舉辦線上沙龍,包括了讀詩課與電影課,我亦也從中學習到許多,尤其是這一年間我們給彼此的通信與對話。我從過去就想上俞萱的課,但礙於地緣關係總是無法參加到。這次的讀詩課讓我認識到許多當代世界詩人的作品,我深知其翻譯的費時與困難,很感謝這樣的心力,不過最重要的還是,每每在參與俞萱的課時,我感受到的對於彼此的敞開與真誠。同時也謝謝木馬繼續出版我的詩集,謝謝本書的編輯瀅如。謝謝支持我寫作的家人,以及隨時在我身邊、不吝於提出批判的易澄。
藉由這本書,在我寄望它成為黑玻璃的瞬間,觀察日食的行動會開始的,不管是日偏食、日環食、日全食,重新感受日常的驚愕,存在於世界各個角落上。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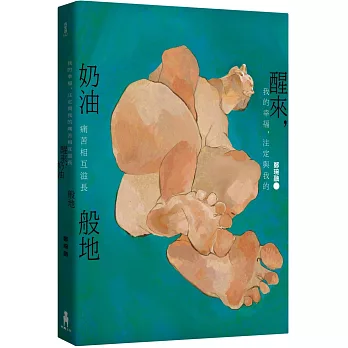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