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你所不知道的諾貝爾獎作家
張文薰(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日本文學在臺灣,是個人人都可以說上一兩句意見的領域——「作家很愛自殺」、「內容很變態」、「太多色情畫面」——奇怪的是,臺灣人不見得會對海明威、馬奎斯這樣說三道四。讀者談論夏目漱石、村上春樹的樣子彷彿他們就住在隔壁,或許因為漢字的親近性,以及風土環境的背景相似、都在十九世紀船堅砲利的威脅下開國西化,中文讀者感覺日本不是戴十字架白膚高鼻的「別人」——尷尬的是,日本卻又跑得那麼快,戰敗後甚至出了兩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談到這樣的鄰居,人都不免因為豔羨而帶幾分酸意。
尤其是川端康成與三島由紀夫。溫泉旅館的妓女、與沉睡少女共枕的老人、火燒金閣寺的和尚、夫妻歡愛後切腹的軍官,關於性與死,聳動獵奇的題材甚至蓋過了作家營造意象、醞釀情感、建構思想的苦心,讀者的心思往往停駐在對作家的直截疑問上:「他為什麼寫這個?」「他最後為什麼要自殺?」
關於文學與死亡,一般看到的其實都是已完成品,自殺在日本傳統中甚至接近一種完成。但本書《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往復書簡》讓讀者有機會接觸「過程」,一部作品從靈感啟發到完成出版的過程,一個初出茅廬的文藝青年邁向偉大作家的過程,還有那終究最讓人好奇的,在自衛隊基地公開自殺的精神變化過程。
「過程」所提供的是解開疑問的線索,卻非答案本身。例如關於三島由紀夫對軍國主義的傾倒與自殺,從昭和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給川端康成信件中「近日有機會搭乘F104超音速戰鬥機,著實痛快」的內容,可發現此前多在分享文藝活動觀賞經驗的三島變化之徵兆。兩年後的昭和四十四年八月四日,三島透露自己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自衛隊活動,並強調「如這般投入腦力、體力與財力參與某項運動,實為頭一遭」。而這項社會運動「就算只是無聊的虛妄幻想,就算僅有百萬分之一的可能」,自己也將放手一搏。三島由紀夫對於投身於集體性社會運動已有死亡的覺悟,放不下的只有「死後家族的名譽」。而唯一能託付「守護家人」任務者,唯有川端康成而已。
足以讓三島由紀夫在死前托孤與守護名譽的川端康成,必定對於其人格與成就、評價方式都極為了解,並能分享相同價值觀。這兩位諾貝爾獎等級的作家之間的情誼,破除凡人臆測的「文人相輕」迷障,早在三島正式成為文人作家前就已經開始。
本書的第一封信是川端康成給「平岡公威」贈書的致意,三島這時還是東大法學部的學生,雖寫出《繁花盛開的森林》而嶄露頭角,但仍是被動員到軍用工廠中服役的二十歲少年。而四十六歲的川端康成已是寫出〈伊豆的舞孃〉、《雪國》的成名作家,與幾位遷居到鎌倉的文學家結盟,試圖在戰火中維繫日本文化的餘脈。在軍事管理與滅絕危機的生活中,三島由紀夫對著尚未謀面的川端康成叨叨絮說,自己如何發現了藝術與創作的珍貴,而且冀望有朝一日能寫出「任誰都會讚嘆的短篇」,並提出「唯美古典短篇」的構思。生存危機催發了創作欲望,文明崩壞之前的古典馨香,三島由紀夫在懷抱同樣美學信仰的大作家之前毫無懼色、侃侃而談,與其說是亟欲獲得權威的肯認,更是在戰爭文化廢墟中尋找知音的孤寂與焦慮,這是一位青年作家的誕生。
於是,川端康成不只刊登三島由紀夫的作品,更為他匍伏不前的《盜賊》提供修改意見。而即使三島自承原稿「粗糙、冗長與幼稚」令人難耐,重寫過後甚至「無論怎麼讀都毫無價值」,應該「收進怎麼也不願再次開啟的書櫥深處,永藏不出」,反覆再三之後,仍勉力將其完成出版。昭和二十三年的《盜賊》成為三島由紀夫第一部長篇小說里程碑。如果不是川端康成的提點與鼓勵,這如「不斷崩塌又堆起、堆起又崩塌、永不得成就」的石塔般折磨三島由紀夫的創作歷程,恐怕將重挫這位後來多以長篇聞名的作家,而緊接之後問世的,恐怕也不會是其代表作《假面的告白》。川端康成給《盜賊》的序文說到:「三島君那早熟的才華,絢爛奪目卻也令人不安惆悵。(中略)那是以真花精萃編織而成的纖弱人造花。」是我僅見最為精妙動人的評論。
日本近代作家之間多有直接或間接的師承關係,如夏目漱石、谷崎潤一郎都在現實生活與創作手法上,關照影響著許多後來者;但川端康成對三島由紀夫那不吝讚賞卻暗自擔憂的態度,以及從「真花精萃編織而成的纖弱人造花」這句評語所顯現出的風度與眼光,舉世難得。更難得的是,即使擁有炫目才華,三島由紀夫的成就更來自不斷的自我否定與超越,從昭和二十一年春到二十三年底的三年間,往復書簡中呈現了他在《盜賊》中頓挫又執筆的自我鞭策,以及在父親任官的期待與自我文學夢想之間的拉扯徬徨。偉大作家絕非天縱英才可及,三島由紀夫與川端康成一同穿越戰爭的破壞、美軍的言論統制、為官任事的誘惑,才從戰後的廢墟中起身,走向世界舞臺。
在接觸介紹作品外譯機會的過程中,三島由紀夫從單方面冀求前輩指點的新人,成長為能提供川端康成參選諾貝爾奬引介文的世界級作家,他甚至建議癯弱的川端康成運動健身。而川端康成也愈發看重三島,甚至發現《雪國》英譯本的作家履歷以「發掘與支持出色的年輕作家如三島由紀夫」記錄自己的貢獻時自嘲。昭和三十三年十月三十一日的三島信件是寄給川端康成夫人的,內容分類列出住院所需用品,這是因為川端夫妻因病先後住院,三島由紀夫與其父母、新婚妻子都表達了關懷與協助。從文壇前後輩到通家之好,這張鉅細靡遺到令人咋舌的清單,最是明確呈現出作家的凡人面貌,偉大藝術家更無法逃過肉體衰敗、歲月流逝的命運。此時的三島由紀夫事業正在起飛,但川端康成已是能用「腹中的小石群讓我遲疑」海外參訪來自我解嘲的老翁之齡,相對於三島對健康與體態的熱中,川端康成的態度顯得淡然無所謂。面對著親密師友的得獎與老朽,逐步走向那個目前尚無法、應該也不想追隨而至的「美麗的日本與我」的枯寂境界,三島由紀夫彷彿是邁開腳步似的奔往世界的另一端——以紀律與行動力展現個人意志與決心的地方,追尋另一群伙伴。
三島由紀夫最後與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正是他寫信給川端康成的年紀啊)結盟,傾全力想喚醒自衛隊員發動政變的行為,可以視為一種自我武裝嗎?武裝脆弱易老的肉身,搬動巨大的傳統來抵抗時間,凝凍青春的剎那光華為永恆。這是我在本書中尋得的線索,卻因為證物被銷毀而死無對證——原來三島由紀夫還有最後一封信,從自衛隊駐紮的富士演習場寄給川端康成家,卻因為「文章太無章法,擔心保留下來會損害到三島的名譽」,而被燒毀。那封以潦草鉛筆字跡寫成的信,是否指出了最後三島精神狀態的瘋魔?把信燒掉的是川端康成本人嗎?畢竟一開始,三島由紀夫的遺孀是連本書內的信件都不願公開的。會在乎文章不合句法、有損名譽的是誰呢?是身為作家的名譽、還是身為平岡公威的名譽?或甚至可能是收信人的名譽呢?在通信兩造都已消亡的現在,看著本書附錄,三島由紀夫友人佐伯彰一與川端康成家屬的對談紀錄,白紙黑字,揭露了一封可能是謎底、卻已然灰飛煙滅的信件之存在,我彷彿追捕兇手卻來到空無一人的懸崖邊,聽聞不知何方傳來的歷史回聲:文學問題的解謎過程,文學而已。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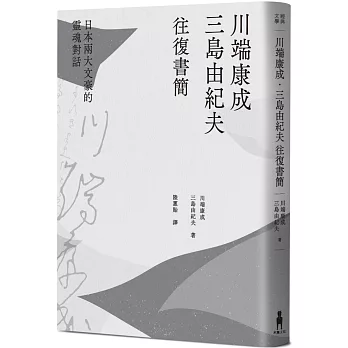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