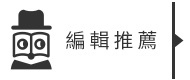前言
再次穿越黑暗
當光州市裡塵埃終於落定,一九八○年五月光州抗爭的倖存者們內心懷抱著一種負債感,認為他們必須在國家歷史與民族面前,把這段抗爭的真相忠實地記錄下來。
一九七○年代的韓國處於第四共和的維新獨裁時代,身為一位作家,我為了寫作與參與民主化運動,當時選擇住在全羅南道。我在全羅南道的海南與光州生活了十多年,結下許多不解之緣。光州的悲劇發生後,這些緣分成為我無法擺脫的命運。企圖記錄這場抗爭的人,大多是體制外的青年知識分子,他們受到嚴密監控和關押迫害,或淪為通緝犯,就算在逃亡途中也堅持要完成這份工作。在嚴酷的時期進行非公開採訪和蒐集資料,訪談曾經目睹過光州慘劇的市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到了一九八五年,光州抗爭五周年將屆,我們面臨著不能再推遲記錄工作的時代要求。誠如李在儀所說,儘管參與資料整編的人或許不多,但有許多願意接受我們訪問,為我們口述自身經歷的市民,正因為有了他們,《穿越死亡,穿越時代的黑暗》才能真正稱為是人民的見證。
應光州友人之邀,我欣然擔負起出版抗爭記錄的責任。有鑒於當時的政治氣氛,這樣的角色可能會為我召來牢獄之災,不過身為作家,理所當然要有這種心理準備。本書的書名──「穿越死亡,穿越時代的黑暗」,引自詩人文炳蘭從靈魂吶喊的詩作《重生之歌》(부활의 노래)。此書名也體現了從殖民地時代以來在民主化與統一的道路上,韓國人民克服無數危機與障礙的近現代史。在光州民主化運動中作為抗爭最後據點的全羅南道廳,經過最後一天凌晨開始的鎮壓,生存下來的意志與死亡的英靈慘烈地化為精神象徵,寄託在一九八○年代民主化運動與「六月民主抗爭」高舉的旗幟之上。
雖然歷史與人類的軌跡如何變化是一個古老的命題,但最終能驅動歷史的還是人類的力量。人類壽命的生理極限意味著,不論何時,每個時代新舊總是同時並存,世界不會在一夕之間變得更好。六月民主抗爭之後,韓國歷史走入具有局限性的妥協民主化時代,不僅沒能徹底清算權威主義體制留下的政治與文化遺產,連面對舊秩序的既得勢力,也不得不保障其活動空間。再者,儘管我們已經披上了成熟的民主主義外衣,國體仍是一個已分裂的「安保國家」,無法擺脫本質上的缺陷。
二○○八與二○一三年韓國連續選出兩位保守派總統,過去搭乘獨裁體制便車的守舊勢力立即重施既得利益者進行理念鬥爭時慣用的老套伎倆──以「北韓」為藉口,試圖破壞與剷除五一八光州抗爭帶來的民主價值。他們靠著重新復活的舊體制公安部隊撐腰,主張五一八民主化運動不過是一場暴動,是一群暴徒對軍隊這一國家公權力的叛亂,且無止盡地歪曲、捏造整起運動是北韓的特種部隊所挑起,或是收到北韓指令的不法分子所為。
當然國軍也是由國民的子弟組成,首要任務就是保護國民的生命與財產。但當全斗煥與「新軍部」於一九八○年派遣空降特戰部隊進駐光州時,目的卻是保護他們黨羽的政權;正如後來一九九○年代的法庭判決所指出的,特種部隊進駐光州是篡奪國民主權的政變和軍事叛亂行為。因此,他們是一支沒有正統性的私人武力,不是國民的軍隊。無差別地屠殺主張恢復民主主義的國民,使光州市民為了守護自身的生存權而發生防禦行為,這是憲法明示的國民抵抗權的體現。
無論是光州市民還是人在現場的國內外記者,都親身體驗到所謂北韓向南韓派遣軍隊的說法純屬無稽之談。即便美方新近公開的情報報告書中沒有證實,新軍部自己也完全了解北韓介入之說並非事實。最重要的是,全斗煥自己調遣了本應致力於防衛國土的正規部隊進入光州進行鎮壓,證明了事發當時,完全沒有必要在意北韓威脅的事實,而美國政府默許了全斗煥的行動,也引起了之後長久以來韓國人的反美情緒。自南北韓分裂以來,「北韓干預和指使」一直是韓國獨裁體制慣用的招數,在光州抗爭期間試圖「抹紅」市民軍的「毒針事件」也不例外。相反的,真正有事先計畫好的反而是以全斗煥為首的新軍部,還為作戰行動取名為「忠貞作戰」;光州市民們不僅沒有收到任何指示,反而根據自身在事件當下所處的位置,彼此從陌生人的關係開始互相協助、保護身邊的人、一起戰鬥,成為同志,進而形成市民共同體。
在《穿越死亡,穿越時代的黑暗》出版後,我經歷了波瀾起伏的人生,不得不獻身於傳遞光州真相的工作。當本書於一九八五年出版後,全斗煥的國家安全企劃部為了羞辱發行人羅炳植與我,將我們以「散布謠言」的輕罪拘留;之後,羅炳植因出版《韓國民眾史》再次被捕並遭到起訴,至於我,則被建議接受剛好收到的一項邀約,前往柏林出席文化活動,並交給我一份短期護照。很明顯全斗煥政府此舉是因為忌諱光州抗爭的輿論蔓延開來,成為眾所周知的歷史事件。
對我來說,這是我第一次離開彷彿孤島般位於半島南部的韓國,這次機會讓我能客觀地觀察「自我與他者」。我輾轉於歐洲、美國、日本等地,與海外文學團體、市民團體、以及僑胞社會一起舉辦宣揚光州抗爭的活動。政治流亡人士尹漢琫創辦的「在美韓國青年聯合會」(Young Koreans United of USA),在美國發行了本書的複印版。梁官洙與住在大阪的青年同胞則將本書翻譯成日文,由「日本天主教正義與和平協會」(Japan Catholic Council for Justice and Peace)出版。直到出國以後,我才意識到,韓國的民主主義發展之所以受限,原因即在於身為「安保國家」的制約。
一九八九年,韓國的開發獨裁時代進入尾聲,為了抵抗政府以「北韓」為理由,一再企圖製造公安事件鎮壓我們的民主化活動,我與牧師文益煥一起訪問北韓。我們此行的另一用意,也是想將兩韓統一的議題納入韓國民眾的日常論述中。北韓之行結束後,我無法歸國,在海外流亡了四年,接著返國後旋即被捕,在牢裡待了五年,這段期間我持續與韓國社會隔絕。從一九八五年之後的十三年間,無法執筆的我不像作家,而更像是活動家。不過我總是試著安慰自己,我在這段時期用全身的行動活出了文學。
自兩韓分裂後七十多年來的體制競爭中可以看出,通過各種經濟社會指標已證明了南韓比北韓取得了壓倒性的發展。在所有二次世界大戰後從殖民統治解放的國家中,韓國可能是唯一同時實現工業化與民主化,朝向近代體制變革的國家。因此,北韓的安全威脅如今已無法當作迴避民主改革的藉口。二○○八與二○一三年兩次的保守派政府公開與北韓敵對,兩韓關係重返冷戰時代,政府拱手將朝鮮半島危機管理的主導權讓給外部勢力,導致韓國長期以來將停戰狀態轉變為和平體制的努力化為泡影,我們的國家反而陷入一觸即發的戰爭危機。歸根究柢,這種作法牴觸了光州抗爭的精神──實現民主主義,讓兩韓能在朝鮮半島和平共存。
二○一三年上台的朴槿惠政府,走在回歸第四共和維新獨裁的回頭路上,比她的保守派前任李明博更赤裸裸地侮辱光州這段歷史。最明顯的例子之一就是,試圖詆毀《獻給你的進行曲》(임을 위한 행진곡)這首歌。這首歌為紀念光州事件死難者而作,是反抗政府壓迫的象徵。他們利用我在一九八九年訪問北韓的事實大做文章,除了荒謬至極地說《穿越死亡,穿越時代的黑暗》是抄襲自北韓的書之外,還指控這首歌是奉金日成之命而作。當然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這首歌寫於一九八二年,而我的北韓之行還在七年之後。另外,抗爭一結束,光州在地的宗教組織已經開始將事件記錄潮湧般送往海外。大約在同一時間,來自海外媒體的照片與影像記錄也開始反過來輸入國內。無論持有偏見的人指控《穿越死亡,穿越時代的黑暗》抄襲的北韓「原著」是什麼書,這本「原著」都只能是一種抄襲自原資料來源的實證之作。令人感到可恥的是,回顧當時扭曲的政府體制,由於全斗煥政權嚴酷的新聞審查,韓國新聞界連一個字也不能報導光州事件的真相。
我們早在二○一○年光州抗爭三十周年之前,已開始討論要出版《穿越死亡,穿越時代的黑暗》的修訂版,但由於各自的生活無法配合一直推遲,直到二○一四年鄭祥容、鄭龍和、李在儀與田龍浩再次找上羅炳植與我,表明了出版的決心,我們才妥為展開工作。這次會商過後沒多久,羅炳植因痼疾去世,我們忍痛繼續工作。同時,針對光州事件的歪曲與攻擊仍持續不斷,我們也咬緊牙關繼續準備。就在這段期間,將朴槿惠逐出總統府的「燭光革命」運動展開了。
韓國前所未有地充滿希望。導致眾多青年死難的五一八光州民主化運動與「世越號」沉船事故(譯按:二○一四年四月十六日發生的船難,造成四百餘名韓人死傷,韓國社會的各種問題,尤其是腐敗問題,也因此在事故調查過程中一一暴露),喚醒了韓國人民,在同樣閃耀的季節裡,偉大的市民們改變了世界。由於他們的努力,時至今日本書不再只是一本血與淚的記錄,而是集體走向正義與和平社會的里程碑。
黃晳暎
二○一七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