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九八六年夏天,我在帕薩迪納加州理工學院的實驗室擔任博士後研究員,在不見陽光的實驗室內長時間埋頭工作。我不喜歡這種作息,開始夢想探險。我草擬了一個計畫,打算去遙遠的中國最後的原始森林裡尋找猿猴。我把計畫告訴了李中清教授,他當時也在加州理工,叫我一定要跟他的朋友連繫,那位朋友當時在國家地理學會擔任攝影記者。不久,我就在黃效文為了籌組CERS而在各地進行演講的一個場合上找到了他。他講完之後,我向他介紹了自己,還有我的計畫。
一九八七年夏天,我們一起上路,到了雲南最偏遠的幾個地區。那是我第一次去中國,儘管那趟遠行只有一個月的時間,卻改變了我一生的方向。那時,效文以探險生涯的無限可能,激發了我,至今他也一直在激發很多其他人。
在這兩本新書─圖文並茂的系列叢書第十五、十六冊─效文再次以探險者、攝影家、一流敘事者的本領,帶我們遠征很少有人會去的地方。隨著他興趣不斷拓展,探險的幅員也不斷擴張,如今他的腳步遍及全球,涉及的題目之廣,從伊洛瓦底江打擊犯罪、加德滿都地震歷險、魁北克比手劃腳交涉午餐,直到在杜拜尋找啤酒,無所不包。
雖然其中不少行旅新鮮而具異國風味,但是效文不忘留出時間重訪他很久以前第一次拜訪的地方,尋思時間與發展引致的變化。他今天對於內在的探索,並不下於外在,因此往往探入更具深度的話題,諸如聖地引發的靈性探觸、石油為基礎的經濟前途、看待老化與生死的角度等等。然而,永遠不變的老式探險依然多得很,不管是以船上溯欽敦江,或是垂降菲律賓無人去過的洞穴,還是悄悄溜進西藏深處嚴禁外人的佛寺。
他的探險精神永遠不滅!
科學主任
畢蔚林博士
序
一九九一年初的一天,黃效文來到我供職的雲南省地理研究所演講,演講的內容是關於長江和長江源頭探尋。坐在聽眾席中的我一開始就感到很驚奇:那英文“How Man Wong”,是這次演講的主題?是將字寫錯、應寫為“How Man Wong”─人類如何做錯事?或是這位演講人的英文名字?他的身體看上去是那麼瘦削,還帶著副眼鏡,怎麼可能會是一位探險家呢?!一個自然地理學概念上的江河與源頭問題,怎麼包含了那麼多精采的人文與歷史內容?!
演講完了以後,這位讓我佩服得五體投地的演講者,向我們的老所長郭來喜教授提出了一個建議,說他夏天要去青藏高原探險,他原來的生物學助手有事不能參與,地理所可否借他一位有野外經驗的年輕生物學者做助手隨行。就這樣,老所長把有著七年野外生物學考察和洞穴探險經驗的我借給了黃效文。那年,我才二十八歲,他嘛,四十二歲。
那次的青藏高原探險,我做的助手工作似乎還讓黃效文滿意,於是接下來就不停地讓我做助手,合作做黑頸鶴保護項目、懸棺保護專案,等等;後來一起隨他去了長江當曲源頭、去黃河源頭後再去找瀾滄江源頭……;再後來……哦,那些轟轟烈烈的探險故事大多都寫在他的二十來本書裡了。
在一九九一年的青藏高原探險之前,我的工作和生活都在海拔三千公尺以下;從那以後,黃效文把我的足跡和整個人生都帶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而就在兩天前、二○一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於老撾湄公河探險的船上,當黃效文說讓我給他的新書寫個序言時,驚寵之餘,我忽然發覺,自己現在人生的一半歷程,是他帶著我走過來的。在這歷程中,除了指引出他創辦的學會的前進方向之外,一路上更多的是教會我怎麼走的老師,以及看到你在路上需要幫助時扶你一把的兄長(嗯,他的那些書中沒有寫這些故事)。
如果說一次人生路途上的相遇是緣分的話,可以在探險路上的一路風雨相隨、生死與共二十五年,這完全只能用「命中注定」來解釋了。感謝上帝將我的興趣與職業配備得如此完美的同時,還給我安排了這麼一位亦師亦友的帶路人!
中國主任
張帆
序
這段時間,昆明的天氣已經很熱,情不自禁想回到在香格里拉浪都村的項目點犛牛乳酪廠避暑。有天晚上,我忽然接到我的老朋友─黃效文打來電話,說要我寫一篇稿子。那天晚上我很難入睡了,半睡半醒度過一晚。起床時,太陽照出這仙境般的中國探險學會試辦的「社會企業」美香奶酪廠,帶起我很多回憶。
一九八一年的夏天六月初,我在昆明的幾個同學和同事,給我帶來了一個來自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的新朋友─黃效文先生,我感到非常高興,有機會能夠認識這位來自美國的朋友。既然是來自遠方的朋友,那當然得用藏家風俗─酥油茶來招待了。
聽說他離開我家後就被公安局審問,而後我也被審問,問我「怎麼認識這位從美國來的人,他跟你是什麼關係?」我說:「我也剛知道他是美國來的美籍華人,其他的我不知道。」
一九八五年我們家去參加「五月賽馬節」時,在賽馬場旁邊的坡上看見兩頂奇特的小帳篷,一輛豐田越野車、一輛摩托車和自行車,我感到很新鮮,走過去一看,是幾年前到我家的那位來自美國的黃效文先生。
之後好幾年沒再見到這位先生。一九九九年某一天,我接到一封邀請函,書松尼姑寺僧尼宿舍專案竣工儀式請州文化局的領導出席,這時身在文化局分管文物工作的我應邀而去。來到尼姑寺一看,又見到了這位多年不見的黃效文先生,一見如故,我們彼此都很高興。特別是見到黃效文先生在尼姑寺所做的援建專案,我作為當地分管文物工作的局領導,向他表示了謝意。竣工儀式結束後,黃先生說,我是他認識的第一個藏族,他前幾年都在藏區跑,很想在藏區多做一些文化和自然保護項目,希望我給他一些幫助,特別是雲南迪慶藏區,我一口答應了他的請求。
第二年冬天,黃先生說要到四川稻城的貢嘎山朝聖和探險,特別邀請我一路同行,於是我也在單位請休假,陪他去貢嘎山探險,想體驗一下探險是什麼樣一個事,這樣就去了。路上所遇到的故事黃先生的書已經描寫過,我也不囉嗦了。之後黃先生又邀請我在他中甸的辦公室工作,我沒有拒絕,也沒有答應,一年之後,我痛下決心,辭了文化局副局長的職位,提前辦理退休手續,決定加入黃效文先生的文化和自然保護隊伍中。二○○一年之後到現在,一直如此,做了很多文化和自然保護項目。
自退休之後跟著老朋友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欣慰的是所做事似乎比在政府工作其間更有意義,更有開創性。時間過得很快,我已經是踏入六十五歲的人了。認識黃效文先生已經三十四年,但我們的友誼之果,都結在我們所開展的文化和自然保護項目之中。
中甸中心主任
七珠七林
自序
今天我在桂林為一年一度的整合永續研討會做了場主題演講。昨晚大衛.洛克斐勒二世及其夫人蘇珊聯合為研討會揭幕。他們向在場的中外聽眾分享了兩人在自然和文化保育上、親身參與的多方經驗─在他們的家族中,這類保育工作已有久遠的傳統。
就我而言,從我們參與的自然、文化保育工作看來,桂林似乎是我這場演講的最佳地點。畢竟,自孩童時期我就知道此地的秀麗,常聽父親說起二次大戰期間,在桂林求學的故事。由於日本占領香港,他的醫學教育驟然中止,我父親和幾個同伴從廣東來到桂林,全程大部分仰賴徒步!
我自己造訪桂林也相當早,幾乎是四十年前了。一九七七年,我是個年輕的記者,經常旅行進入中國。演講中我敘述了自己的故事,佐以當年拍攝的懷舊圖片,彼時文化大革命才剛結束,中國尚未對世界開放。今天看來,那些影像彷彿已是遙遠的記憶,因為桂林跟中國其他地方一致,早就向前大步邁進。
過去的許多世紀中,人傑地靈的桂林不但以自然景觀聞名,也出了象徵中國傳統文化巔峰的不少學者。我在這裡為自己的兩本新書寫序,本來是再理想也不過了。然而桂林這方面已有很多變化。是好是壞,則見仁見智。
過去四十年來,我探索了中國與世界各地很多偏遠、「原始」的地區。也許,一千兩百年前生活於五代時期的布袋和尚,有首詩偈可給今天的我們一些啟示和靈感。
「手執青秧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 六根清凈方為道, 退步原來是向前。」
CERS創辦人兼會長
黃效文
二○一五年十一月五日寫於桂林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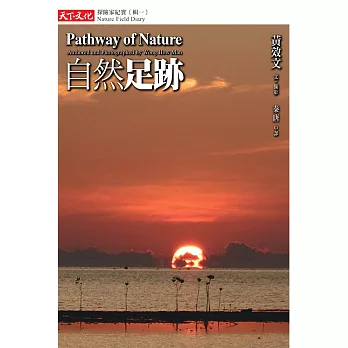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