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四月初春,梅雨方歇,在上海往北京的高鐵上,遇到剛從臺北到中國打拼的年輕人。聊了幾句就發現曾經同為紅樓過客,不覺談了一路。他的眼神裡有對遠方的期待,更多的是對未知的茫然與焦灼。
四百年前,美麗之島的祖先們為了活得更好,吃得更飽,悲情的橫渡黑水溝,四百年後我們以一樣的勇氣,離鄉背井,回到這葉地理課本上的秋海棠,行囊裡有些什麼呢?需要些什麼?車窗外一輪明月跟高鐵保持著同樣的速度,月娘啊,是否可以為我們指點迷津?
走出北京南站,迎向人海,我們交換了微信,互道珍重,其實彼此都明白相逢無期,一種難以言喻的悲涼掩殺而來。
臺北這兩天下雨,撐不撐傘都很尷尬。然而我最喜歡這種雨天,跟自己的心境很合拍。大部分的時候,我就是這麼不上不下的活著。理想早已逐漸遺忘,像無緣卻依然戀想的青梅竹馬,偶爾在路上遇見,互道珍重其實是有點矯情,別過頭去,彼此都有一點悵然。
人到了某個階段,經過了些風風雨雨,明白了一些人、一些事,會期待一種屬於自我的理解。年輕時就發現自己的軟肋,是怕失去一種自我標籤。曾經大言不慚的說:「我能接受你不喜歡我的設計,但是不能說我的設計沒有風格。」然而什麼是風格呢?我以為的風格需要孤獨為基調,思考作為主旋律,偶爾的挫折為裝飾音。感動一方面來自共鳴,一方面也來自一種對風格不同的讚嘆。從不依附品牌,生命依舊必須精彩。
逃離攀附不僅僅是勇氣,還是初老男子一種必須的品味。下了通勤的巴士,轉文湖線之前,一杯特調咖啡,一個花生貝果,開始我的一天。通常這是天氣不好的時候,也是我開始嘗試跟自己對話的時候。
這些年如麻瓜般在職場的浪間穿梭,偶爾也有浪端馳騁的快意,但大多數時候卻是必須盯住眼前的浪,在市場與技術的快速變化中保持平衡。眼睛的餘光,還必須關注即將湧上來的新浪,在失去平衡之前及時躍上。
上班前也要像一般上班女郎一樣塗脂抹粉,努力做一個專業的演員。朝九晚五,劇本類似,對白雷同,雖說為五斗米不得不折腰,對自己的一肚子雪月風花,有時不免略感歉意。
我們喜歡學習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常常問自己為什麼要活著,似乎人生下來就是要達成某種神聖的使命。初中時看到國文老師在黑板上寫下宋儒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內心激動不已。似乎已經有偉大的先聖先賢,替自己立下了人生努力的方向與目標。
從一個手無縛雞之力,言不及義的文青,到天天打拼,爆肝邊緣的工程師,再蛻化成一個戴著面具,裝模作樣的專業經理人,這條路我走得跌跌撞撞。日漸蒼老的軀殼下,剩下微微跳動的心。還有一點點自以為是,就跟青苔一樣,憑藉的只是一點頑強。
青苔是一種非常非常古老的生物,它需要的水及陽光極少,可以生活在極為惡劣的環境中。地球上這麼多物種滅絕了,青苔會不會問自己,它生存的目的是什麼呢?晚近接觸到佛學,看到「堪忍」二字。以佛的角度而言,人生最多也就是「堪忍」而已。青苔應該是堪忍中之堪忍吧。青苔般的攀附在濁世的我,細數過往,支撐我走過來的其實是一種「天奈我何」的白目吧!
每個人都有一個隱藏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語言文字都不是溝通的必要條件,中文裡有「心有靈犀」四字在描述這種狀態。人類創造了很多字彙來形容人生的行為和狀態,有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等等。為了讓你瞭解,也只好用這些字彙來說說我的故事,當真是一種無可奈何的事。
也許有一天有一種儀器,像X光一樣,掃描一次就可以把一生的悲歡離合轉換成文字,人與人依然各有背景,各自以自己的方式理解朋友和敵人。上世紀七○年代有一首歌〈Sound of Silence〉,如果你聽過,也許可以更瞭解我要說的故事。
我們習於用一個大家理解的方式展示自己,但是卻也習於用隱晦的方式理解別人。藉有敘無真是一種莫可奈何。當有人可以把內心的世界赤裸裸的揭露時,我們給予掌聲或噓聲。這些掌聲或噓聲只是在生命河流之前,訴說一種難渡彼岸的局限而已。
你我有緣,這些於我已是煙塵舊事,書中人物似假還真,自非純屬虛構。對於你也許就是現在進行式或者是未來式,只是換了個不同的名字而已,同樣日日夜夜與你血肉之軀短兵相接的周旋。
穿越劇裡的「信號」—心意如果真誠,自然能找到方法傳遞。假使你看過這部韓劇,相信你會懂的。僥倖或者還能還自己一點清白。
夏研
二○一九年五月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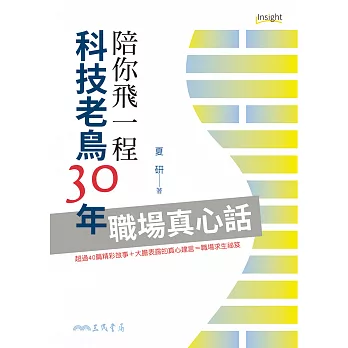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