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究竟之旅
河口慧海的《西藏旅行記》
.西藏神秘國邊境不安
在藏史學者賀文宣所編的《清朝駐藏大臣大事記》(1993, 北京)裡,光緒三十年條下正月二十日乙亥(1904年3月6日)有分條記載:「裕綱奏陳藏人以英人欺淩無禮,力阻藏臣赴邊與印督會議,難于起程。旨著暫允藏人之請,檄馳委員等力阻入亞東關前進之英兵再進,俟有泰到任徐籌善策。」
這個條目內容展示的是歷史上某一刻一個緊迫危急卻又複雜微妙的處境,當中,心焦如焚向北京中央朝廷急報情勢危殆的是清廷駐藏大臣裕綱,而提兵已侵入錫金、西藏的邊關亞東,並躍躍欲試亟欲東進的是英國印督特使榮赫鵬(Francis Younghusband, 1863-1937),清政府不想與英國發生戰端,要求裕綱親赴邊境與英人談判,西藏十三世達賴喇嘛卻意有未平(他有俄國人在背後搧風壯膽),藏人執意要自行抗英衛土,而大清政府派來即將接替裕綱的新任駐藏大臣有泰已經在路上…。
如果把故事景觀再放大一百倍,這是更大的歷史矛盾的一個小片段。英國設東印度公司始於1600年,也就是遠在鴉片戰爭之前,堅船利砲的大英帝國早已在中國一旁(印度)虎視眈眈了兩百多年,期間它逐步吞併了尼泊爾、布丹、和哲孟雄(今稱錫金),清廷雖然在1890年簽訂中英藏印條約,保住了西藏主權,但西藏南方屏藩盡去,邊陲門戶洞開,鎖國自守的香格里拉神秘國其實已經是岌岌可危,再也保不住了。
同樣的故事,我在<旅行與探險經典文庫>收入的另一本書:法國女旅行家亞歷山卓.大衛尼爾(Alexandra David-Neel, 1868-1969)所著<拉薩之旅>(My Journey to Lhasa, 1927)的導讀中就曾經描述:「在地理上印度緊貼著西藏,英國人想對西藏有更大影響力的念頭從未間斷;尤其到了十九世紀末,英國人擔心俄國人的影響力自新疆南下,恐將危及印度,更覺得需要控制西藏做為緩衝;兩個強權在中亞地區爾虞我詐地暗自角力,被英國作家吉卜齡(Rudyard Kipling, 1866-1936)稱之為『大競局』(The Great Game),更在小說<阿金>(Kim, 1901)中把它不朽地形象化…。」
除了吉卜齡目中無人卻又生動難忘的「大競局」一詞,也許近人英國史家彼得.霍浦寇克(Peter Hopkirk)筆下的通俗史書<世界屋脊的私闖者>(Trespassers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1982)是另一個對當時歷史氛圍最佳的全景式描繪。總之,上面所說的孤獨無援的邊臣急報,背後有一個雄大奇詭的場景;西藏長年的閉關自守(只對中國、布丹、尼泊爾、哲孟雄等地開放),既不准外人入藏,亦不許藏人與外人往來(違者的處罰極其殘酷嚴峻),西藏內部佐國的政教合一高僧們不一定能夠了解十九世紀末世界帝國主義的複雜競爭情勢,對日益衰頹的大清帝國也有不服之心,而俄國人和英國人內心都有不可告人的算計,而其間更穿插了一群立意要探索西藏奧秘的旅行者與傳教士…。
熟悉近代西藏歷史的朋友可能已經知道上面那場「英軍進逼,邊臣告急」故事的下一回合,英人進軍當然不聽清政府的勸阻(他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藉口,不是嗎?),而揮舞著中古世紀武器的西藏僧兵肉身當然也擋不住新式洋槍洋炮,1904年4月9日,英軍在骨魯地方大敗藏軍,4月11日就攻抵江孜,並繼續往拉薩推進,儘管中間清廷與駐藏大臣都做了各種外交上的努力,也攔不住探險家軍人榮赫鵬的部隊和意志,8月3日英軍入拉薩,達賴倉皇逃離布達拉宮,有泰不得不率官員迎英軍,西方人眼中第一位抵達拉薩的探險家榮銜終於落到榮赫鵬頭上(那是他多年的夢想)…。
.日本學問僧識見不凡
包括彼得.霍浦寇克在內的西方旅行史家,都傾向於認定榮赫鵬是第一位進入拉薩的「外國人」,而前仆後繼競相入藏的旅行家也至此終於有了結論,用霍浦寇克的話來說,榮赫鵬是「這場無與倫比大競賽的真正贏家」(really the winner of this extraordinary race)。
但,且慢!如果榮赫鵬是第一位進入拉薩的外國人,他們要如何面對另有一位異人在1901年3月21日喬裝僧人漢醫率先來到了拉薩,整整比榮赫鵬早了三年有半?事實上,如果把印度人算進來,這位異人的藏文老師孟加拉人達思(Sarat Chandra Das)則早在1879年和1881年就曾經兩度成功抵達拉薩。
這裡說的異人指的是日本僧人旅行家河口慧海(1866-1945),俗名河口定次郎,他是出身黃檗宗五百羅漢寺哲學館(今日東洋大學的前身)的學問僧。他在讀破一切藏經之後,為了追求比漢譯大藏經更古老的梵文經文(日本語佛經都由漢文轉譯而來),發願入藏求經,三十二歲(1897年)自神戶出航,先至印度大吉嶺追隨達思習藏文,三年後決意假扮中國僧人潛行入藏。他從尼泊爾加德滿都出發,順利經日喀則進入拉薩。河口慧海在拉薩遍訪聖地、求法問道將近兩年,並以漢醫身份濟世治人。他的醫術高明,又對窮人不取分文,聲名乃逐漸遠播,遍交藏人權貴,甚至連達賴喇嘛十三世都聽聞有此一「中土高僧」,還多次接見了他(漢文流利的達賴十三世喇嘛並未識破這位冒牌貨)。
但薄紙終究包不住火,他的行醫善舉得罪了若干原本地位崇高的藏醫,拉薩又至少有兩位藏人曾經在大吉嶺見過他(他在大吉嶺是個名人,而且並未偽裝中國人的身份),他的秘密就逐漸有隨時走漏的風險。1902年5月,他的真實身份傳到達賴喇嘛耳中,河口慧海立即面臨急切如風的追捕;他連夜動身,以十八天的時間迅速逃到錫金邊界,不久後,他就安抵大吉嶺他的師傅達思的住所。一場長達兩年不可思議的旅行就此落幕,只是可憐了在拉薩與他交往的藏人朋友,以及在逃亡路上幫助過他的藏人,後來都受到了嚴刑酷罰。
河口慧海在1903年返回日本,隨即在報上連載他的旅行所見所聞,1904年更以《西藏旅行記》之名由博文館出版;1909年,他又將全書親自英譯為《西藏三年記》 (Three Years In Tibet),風行一時,他的冒險行蹤乃為世人所周知,如今此書已經是了解西藏民族風俗與昔日旅行歷史的經典了。
回到旅行史上入藏競賽一事,西方史家主張不該把河口慧海計算在內;他們的理由,河口慧海是亞洲人,身份偽裝有了太大的優勢,而歐洲人不管藏文多麼流利,微服入藏的難度高太多了。譬如正當慧海居停拉薩之際,另一位歐洲大探險家斯文赫定試著假扮蒙古朝聖者自北方入藏,在距拉薩五天的行程之外被識破,功虧一簣,可見競爭不公平。話雖如此,但我們別忘了稍晚抵達拉薩的女探險家大衛尼爾,不也是假扮藏人成功混進入了拉薩?
也許我們不要太計較西方史家的小家子氣,河口慧海畢竟是識見、氣度都極不凡的東方旅行家,他的旅行條件也絕不是寬裕容易的,他自稱他的旅行方法是「頭陀乞食」(也就是沿途托缽)的,不是西方探險家那種駱駝成隊、挑伕成群的富人之旅。河口慧海又是一位敏銳的觀察者與忠誠的記錄者,他在西藏所見並不是一個和睦的理想國,而是一個神人合一的恐怖統治;而藏人特有的艱苦生活條件、以及從而衍生的獨特風俗,他也不畏可怖,一一據實以錄,部分內容恐怕不是腸胃不健康的讀者所能吞嚥。但也正是如此,他留下的記錄的深度、準確和全面性都不是浮光掠影的西方探險者所能比擬。
東方僧侶旅行自有傳統,他們不是垂涎他人國土的侵略者,而是求法問道的自我追尋者;榮赫鵬進出西藏,在他國文獻裡充滿了倉皇恐懼的兵災急報,而慧海入藏取經,完全是孤獨來去的鬼影,他國文獻根本不曾彰顯。從今日生態的觀點來看,那高下是分明的。我必須說,這是法顯、玄奘以降的東方旅行傳統,我們在河口慧海身上,再度看見久逝的古風。
詹宏志
編輯前言
.探險家的事業
探險家的事業並不是從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才開始的,至少,早在哥倫布向西航行一千多年前,中國的大探險家法顯(319-414)就已經完成了一項轟轟烈烈的壯舉,書上記載說:「法顯發長安,六年到中國(編按:指今日的中印度),停六年,還三年,達青州,凡所遊歷,減三十國。」法顯旅行中所克服的困難並不比後代探險家稍有遜色,我們看他留下的「度沙河」(穿越戈壁沙漠)記錄說:「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耳。」這個記載,又與一千五百年後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穿越戈壁的記錄何其相似?從法顯,到玄奘,再到鄭和,探險旅行的大行動,本來中國人是不遑多讓的。
有意思的是,中國歷史上的探險旅行,多半是帶回知識與文化,改變了「自己」;但近代西方探險旅行卻是輸出了殖民和帝國,改變了「別人」。(中國歷史不能說沒有這樣的例子,也許班超的「武裝使節團」就是一路結盟一路打,霸權行徑近乎近代的帝國主義。)何以中西探險文化態度有此根本差異,應該是旅行史上一個有趣的題目。
哥倫布以降的近代探險旅行(所謂的「大發現」),是「強國」的事業,華人不與焉。使得一個對世界知識高速進步的時代,我們瞠乎其後;過去幾百年間,西方探險英雄行走八方,留下的「探險文獻」波瀾壯闊,我們徒然在這個「大行動」裡,成了靜態的「被觀看者」,無力起而觀看別人。又因為這「被觀看」的地位,讓我們在閱讀那些「發現者」的描述文章時,並不完全感到舒適(他們所說的蠻荒,有時就是我們的家鄉);現在,通過知識家的解構努力,我們終於知道使我們不舒適的其中一個解釋,就是薩依德(Edward W. Said)所說的「東方幻想」(Orientalism)。這可能是過去百年來,中文世界對「西方探險經典」譯介工作並不熱衷的原因吧?或者是因為透過異文化的眼睛,我們也看到頹唐的自己,情何以堪吧?
.編輯人的志業
這當然是一個巨大的損失,探險文化是西方文化的重大內容;不了解近兩百年的探險經典,就不容易體會西方文化中闖入、突破、征服的內在特質。而近兩百年的探險行動,也的確是人類活動中最精彩、最富戲劇性的一幕;當旅行被逼到極限時,許多人的能力、品性,都將以另種方式呈現,那個時候,我們也才知道,人的鄙下和高貴可以伸展到什麼地步。
西方的旅行文學也不只是穿破、征服這一條路線,另一個在異文化觀照下逐步認識自己的「旅行文學」傳統,也是使我們值得重新認識西方旅行文學的理由。也許可以從金雷克(Alexander W. Kinglake, 1809-1891)的<日昇之處>(Eothen, 1844)開始起算,標示著一種謙卑觀看別人,悄悄了解自己的旅行文學的進展。這個傳統,一直也藏在某些品質獨特的旅行家身上,譬如流浪於阿拉伯沙漠,寫下不朽的<古沙國游記>(Arabia Deserta, 1888)的旅行家查爾士.道諦(Charles Doughty, 1843-1926),就是一位向沙漠民族學習的人。而當代的旅行探險家,更是深受這個傳統影響,「新的旅行家像是一個來去孤單的影子,對旅行地沒有重量,也不留下影響。大部分的旅行內容發生在內在,不發生在外部。現代旅行文學比起歷史上任何時刻都深刻而豐富,因為積累已厚,了解遂深,載諸文字也就漸漸脫離了獵奇采風,進入意蘊無窮之境。」這些話,我已經說過了。
現在,被觀看者的苦楚情勢已變,輪到我們要去觀看別人了。且慢,在我們出發之前,我們知道過去那些鑿空探險的人曾經想過什麼嗎?我們知道那些善於行走、善於反省的旅行家們說過什麼嗎?現在,是輪到我們閱讀、我們思考、我們書寫的時候。
在這樣的時候,是不是<旅行與探險經典>的工作已經成熟?是不是該有人把他讀了二十年的書整理出一條線索,就像前面的探險者為後來者畫地圖一樣?通過這個工作,一方面是知識,一方面是樂趣,讓我們都得以按圖索驥,安然穿越大漠?
這當然是填補過去中文出版空白的工作,它的前驅性格也勢必帶來爭議。好在前行的編輯者已為我做好心理建設,旅行家艾瑞克.紐比(Eric Newby, 1919- )在編<旅行家故事集>(A Book of Traveller’s Tales, 1985)時,就轉引別人的話說:「別退卻,別解釋,把事做成,笑吠由他。」(Never retreat. Never explain. Get it done and let them howl.)
這千萬字的編輯工作又何其漫長,我們必須擁有在大海上漂流的決心、堅信和堅忍,才能有一天重見陸地。讓我們每天都持續工作,一如哥倫布的航海日記所記:「今天我們繼續航行,方向西南西。」
詹宏志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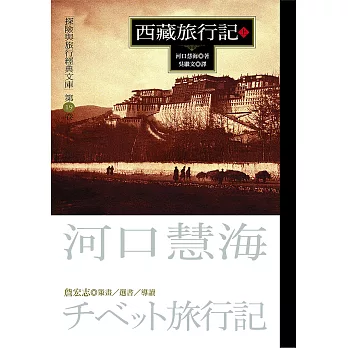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