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臺灣人在亞細安
二○一七年十月五日,臺灣的立法院發生了一件非常小的小事。
當時,剛從總統府調任國家發展委員會還不滿一個月的新主委,在第一次前往立法院接受質詢時,遇上在野黨立委提問,政府如何評估臺灣需不需要爭取參與慣稱 RCEP 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一項以東南亞十國為核心往外擴大的區域自由貿易協定。
立委順口一問:「ASEAN 是什麼?」沒想到,主委頓時語塞,猶豫之間脫口而出:「北美的自由……」雖然馬上就被身旁的幕僚打斷,但已來不及,除了當場被糾正,也隨即被好事的媒體寫成了挖苦的花絮新聞。
ASEAN 是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也就是東南亞國家協會(東協),而既然你已經翻開了這本書,我們相信你肯定知道:「亞細安」就是 ASEAN 的音譯中文名稱。
既親近又陌生的鄰居
行政官員有沒有答對近乎快問快答的冷知識小問題,當然不是什麼值得放大檢視的嚴重缺失。何況,就算真的要考驗臺灣人對東南亞有多不熟悉,肯定也不是官員的專利,以下就是一個簡單的小測試:
你知道二○一八年一整年臺灣人前往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歐洲和紐澳的出國人次有多少嗎?答案分別是美洲七十一萬人次、歐洲五十三萬人次、紐澳二十一萬人次。你知道二○一八年一整年臺灣人前往東南亞的出國人次有多少嗎?不包括寮國和東帝汶,答案是兩百四十五萬人次。
換句話說,臺灣人每一年前往東南亞的人次,差不多比前往歐美紐澳的人次全部加起來還多出了快一倍。
從交通部觀光局每年公布的這一組數字來看,「地緣關係」肯定是決定出國目的地人次多寡的關鍵。距離臺灣比較近的地區,一來可能有比較多產業投資,在地工作、生活的臺灣人理論上會比較多;二來基於旅行費用相對便宜,前往觀光旅遊的臺灣人也應該會比較多。別說東南亞,即使是臺灣人最常前往的中國、日本和韓國,根本原因也大致都是如此。然而,這二百四十五萬人次的意義,還是值得我們再多想一想。
行政院主計處近年來針對「國人赴海外工作」都會進行例行性的統計分析。根據入出國時間、勞健保投保等官方紀錄,主計處推估出二○一八年在海外工作的臺灣人應該在七十四萬人左右,其中以地區來看,中國港澳就佔了五十五%,東南亞則以十五%居次,遠高於日本、韓國。
這一年,在東南亞工作的臺灣人大約有十一萬多人。讓我們假設,因為距離比較近的緣故,他們每一季都會往返臺灣和東南亞一趟。也就是說,二百四十五萬人次之中,可能有四十五萬人次是因為出國工作才去到東南亞;但剩下來的,仍然有兩百萬人次之多,這個數字至少是美洲的三倍、歐洲的四倍、紐澳的十倍。
從出國人次的逐年變化趨勢就能很明顯地看出來,早在政府拋出新南向的口號之前,臺灣跟東南亞的往來關係,就已經有一定程度的密切了。但大家都去東南亞做什麼呢?除了工作和觀光旅遊,我們還能想到哪些臺灣人前往東南亞的原因嗎?直覺會浮現的答案,或者能試著猜測的線索,似乎不多。
難以想像其他去東南亞的目的,跟我們能利用於認識東南亞的大眾渠道長期以來一直相對匱乏有關。攤開臺灣主流媒體的內容,在已經相對有限的國際消息篇幅之中,能找到的東南亞時事訊息幾乎在任何時候都不成比例地稀疏且破碎。即使難得關注了,很多時候也是透過遠處西方國家的眼光,來打量這些自己的近鄰。
亞細安的動盪 DNA
《走入亞細安》這本書最主要想呈現的,並不是「臺灣人怎麼看待亞細安」。我們認為臺灣社會已經很習慣以自我為中心來衡量「東南亞跟臺灣有什麼關係」、「臺灣需要知道東南亞哪些事情」乃至於「什麼是觀看東南亞的臺灣視角」,彷彿我們很清楚知道自己是誰、眼中的對方又是什麼樣子,但多數時候情況並非如此。
從近代史來看,亞細安跟臺灣有許多相似的命運。我們幾乎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才浮現出今日國家的輪廓;在國家成形的過程中,我們幾乎都經歷過內部族群關係的矛盾與衝突,也都深刻地被「冷戰」意識形態的對立框架影響了很長一段時間。比起我們傾向抬頭仰望的日本、總是競爭比較的韓國,亞細安的十個國家,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差異非常大的政治與經濟發展經驗,某種程度更像是臺灣處在平行時空裡可能產生的各種不同鏡相。
這本書的第一部分,就先以簡明的圖文故事,帶大家扼要地認識亞細安如何誕生,並逐步演變成今日的格局。
大部分臺灣人可能會直覺認為,相較於聯合國、歐盟,亞細安應該是一個比較晚近才出現的政府型國際組織。其實一點也不。二○一七年八月,亞細安剛剛慶祝了它的五十歲生日,若以人生來描述,這已經是一個中年正盛、一步步要邁向熟齡的知天命之人了。
一九六○年代,亞細安誕生於新興國家彼此對抗、衝突的亂局中。殖民者不願完全放手離去的獨立佈局,不同政權對於民族、疆域的不同見解,乃至於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互相滲透的圍堵角力,不同因素交叉影響,最後催生出一個起初國際戰略意義遠大於區域合作關係的區域國家組織。初創的五個成員國之中,馬來西亞當時成立不過四年、新加坡獨立僅僅兩年、菲律賓和印尼各自脫離殖民統治二十年左右,只有泰國在二戰前已形成如今的君主立憲體制,但當時因為中南半島的戰爭動盪,內政其實也被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左右甚深。從一九六七年至今,前二十多年整個東南亞地區或多或少都還受到戰爭衝突與軍事佈局影響,要直到一九九○年代以後才稱得上各國政局都逐漸穩定,亞細安也才逐漸增加到今日十國的規模。
和平到來的早與遲,也造成國家發展的起跑點落差非常大。一九六七年時,亞細安不論政治或經濟都處在高度不穩定的狀態,十個國家的實質 GDP 總額還不到兩千億,僅佔全球的一·○三%,相較於人口比例明顯偏低。接下來五十年之間,成長趨勢逐步拉高,尤其在一九八○年代末期以後,亞細安的成長速度就已明顯超過世界整體的腳步。二○一六年,亞細安十國的實質 GDP 總額已達到全球的三·四%。整體來說,五十年內實質 GDP 成長了十五·九倍,遠高於全球的四·七九倍。儘管份額仍很小,但可以說這個地區的經濟活動活絡度是以高於世界平均的三至四倍速在發展。
從人均 GDP 的變化則可以看出,東協新舊成員之間有一個明顯的落差。一九九○年代以後才加入的新成員四國(Cambodia, Laos, Myanmar, Vietnam,CLMV),數據上都是典型的中低發展國家(事實上,柬埔寨甚至一直到近幾年才正式脫離聯合國定義的「最低度發展國家」行列)。然而,如果換個角度看逐年的 GDP 成長率,卻又是不同的光景。東協十國從一九九○年代起的 GDP 成長率普遍都高於全球平均。而新成員國比起老成員國(ASEAN 6)又普遍還更高一些,即使碰上區域性甚至全球性的經濟波動,新成員國受影響的程度,也往往比老成員國來得輕許多。
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風暴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亞細安國家的經濟成長,長期都非常仰賴國際資本從外部挹注,因此泡沫化的潛在危機一直存在。當一九九七年下半年從泰國開始因為國際熱錢流出引發一連串嚴重的貨幣波動,以東南亞為首當其衝,亞洲各國就紛紛都面臨了一波國際金融炒家禿鷹式的掠奪。
結果,一九九八年東協十國的實質 GDP 成長率呈現明顯兩極。老成員六國全部負成長,其中當時最依賴國際借款與外國投資的泰國、印尼和馬來西亞受到的衝擊最為嚴重。誠然,亞洲金融風暴帶來的衝擊並沒有持續太久,一九九九年以後各國就逐漸回復到原本的發展腳步。但在受創最深的三國,這波衝擊卻對後來的國家發展都產生了長期的影響。
印尼當時選擇了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金融援助與配套經濟改革計畫,但初期效果並不明顯,國內動盪最終造成執政三十餘年的強人蘇哈托(Suharto)政府倒台。接下來的十多年,先天條件格外良好的印尼,其經濟發展並沒有因為向國際結構性接軌而一飛沖天,反而維持起起伏伏,直至近年才逐漸發揮了優勢。
馬來西亞選擇不理西方國家反對進行外匯管制,短期經濟恢復得最快,但也助長了該國政商裙帶壟斷的結構性問題,後來成長腳步也逐漸放緩。此外,強勢的總理馬哈迪(Mahathir bin Mohamad)對時任財政部長、主張配合國際進行更大規模經濟結構改革的副手安華(Anwar Ibrahim)進行的殘酷政治鬥爭,也埋下了後來馬來西亞反對陣營整合的種子,深刻影響了馬來西亞晚近的政治格局。
泰國在金融風暴後也經歷政府倒台的不穩定局勢。商界出身、在內閣任職的塔克辛(Thaksin Chinnawat)建立了泰愛泰黨(Phak Thai Rak Thai)並且勢力迅速壯大,在二○○一年成為泰國首相。塔克辛上任後宣稱要記取金融風暴的教訓,嘗試推動一系列有別於以往的實業發展計畫,帶動經濟轉型,但政治上與傳統勢力無法共容的矛盾,卻也造成後來他遭到政變鬥垮之後,泰國就進入了紅黃衫軍長期對立的政治僵局。
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東協十國的政治與經濟發展呈現互為因果的高度交纏。人們不太可能單純以與世界經濟的接軌程度,或者政治民主化的程度,來論斷這些國家發展的表現好壞;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特殊的議題框架,「進步」與「開放」在特定的社會、特定的時間點上常常是互相矛盾的一組形容詞。更重要的是,一切的一切,其實幾乎都在二戰結束到東協元年的二十年之間已經埋下了種子。
從關鍵字看亞細安
這本書的第二部分,則收錄了五篇風格各自不同的報導性作品。每一篇都設定有一個我們認為與臺灣有對照價值的關鍵字主題。
賴奕諭在菲律賓的偏鄉反思「原住民族」的概念。擁有上千種方言的群島國家菲律賓,對「原住民族」的認定方式因循著殖民者古老的分而治之手法,以一個族群有否接受天主教信仰(做為是否「順服政權」的指標)為主要判定標準,族群的區別是在歷史過程中逐漸生成,跟臺灣以「血緣」和「文化」認定的習慣不同。但即便如此,菲律賓的原住民族也並非與世隔絕,全然只因為抵禦殖民者的統治而保留並堅持自身的傳統文化。賴奕諭以呂宋島半部山區的薩加達(Sagada)人為例,精采地分析了他們對儀式細節的傳承與實踐,其實是不斷在與外界(包括國家、現代文明和其他少數民族或團體)互動的過程中形塑出來的需求;他們對外來影響的拒斥也無法單純以「對抗」的浪漫想像化約地理解,跟現實生活中的對外關係與利益盤算都有關係。
郭育安在馬來西亞的檳城探討「文化遺產」的涵意。保存歷史建築物,使一個建築空間變成一件文化遺產,必然有某些價值會被突出強調,進而決定了人們想像空間的方式。郭育安在入選聯合國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的老市區喬治市(George Town)裡追蹤被立法禁止的養燕活動。喬治市保有大量舊式街屋與長期的市區凋零有關;為供應燕窩產業而生的養燕活動,也因此才出現在閒置的老房子裡。從爭取到維護世界遺產的過程中,古蹟團體和地方政府不斷放大經聯合國認可的普世價值,並透過振興傳統技藝,強化居民對世遺的光榮感與對地方的認同感,但自成一套技術的養燕卻因衛生安全、環境噪音和破壞建築的考量,不被認為活化了古蹟,無法融入世遺論述,終致全面被禁。什麼是有價值的特色或傳統?這個問題並沒有先驗的一致標準,而是在爭論中逐漸劃出了界線,最終才形成人們所接受的模樣。
在這兩篇作品之中,我們嘗試拋出的問題是對何謂「地方傳統」的詰問。從薩加達和喬治市的經驗,我們都看到傳統並非靜止不變,只是在生活中隨時等待被發現、取用甚至刻意展演的固定東西。傳統的內涵,以及它之於一個群體或地方的意義,在不同情境下可能會產生變化,什麼部分應該要被保留?什麼部分可以權變?甚至捨棄?怎麼詮釋一項文化活動、一種文化概念維持或中斷的意義?往往都是在社會互動之中才能決定。
萬宗綸在新加坡觀察到「填海發展」背後的思維與對鄰邦造成的衝擊。新加坡雖然是一個繁榮的城邦國家,但自獨立以來政府一直視「國土狹小」為競爭與發展的極大劣勢,因此通過有計畫地填海造陸已經讓國家擴張了超過二十%的土地。不斷填海與其出色的經濟發展一樣,成為國家必須汲汲經營維持的「成功」神話。然而,新加坡追求這個另類的「大國夢」無法自力完成,反而需要不斷攫取其他國家的資源。它憑藉著經濟上的優勢,吸引周邊國家前仆後繼地成為其砂土和勞動力的輸出國,卻對這些國家因此產生的環境生態爭議或社會經濟問題無所聞問。
林佳禾和游婉琪在馬來西亞的關丹則發現「中國因素」有多種不同的作用力。身為一個經濟發展遲滯的地方,關丹十多年來先後因為稀土提煉、鋁土礦開採到外國直接投資,而連環引爆環境公害與地方發展的爭議,往源頭一追溯,每件事都跟中國有關係。然而,關丹真正身處的浪潮其實是馬來西亞政治民主化運動波濤洶湧一段劇烈的變動期,它在不斷高低擺盪的狀態下,真正不斷角力的課題是地方人士對落後發展的糾結心理,以及地方政治難以動搖的僵化格局。中國在每件事裡的角色都不太相同;投身在爭議之中的關丹人,也並不單純地只把中國當成威脅或盟友,而是隨著不同的情境調整看待中國的態度。
最後,胡慕情和林佳禾在越南的北中部則見證了全球化時代的「邊陲發展」有素樸的正義感恐怕難以拆解的複雜利害關係。二○一六年,臺灣的台塑集團在河靜(Hà Tĩnh)省投資的大煉鋼廠,疑似因排放廢水造成鄰近省份超過兩百公里沿岸水域污染,導致大量魚群暴斃的意外,成為越南史上抗議規模最大、賠償金額最高的環保公害事件,至今責任釐清和損害賠償的爭議仍未完全消散。然而,本地的漁業究竟受到什麼樣的衝擊?工廠周邊的聚落正在經歷什麼樣的轉變?直接走進現場了解,卻發現問題恐怕另有隱情。無法在越南的政治環境下推展的維權運動,必須看得見越南本地漁業資源管理和偏鄉發展的困境,找出在跨國司法訴訟之外介入在地的方法,才有機會從根源改變地方社會的問題。
透過這三篇作品,我們則對「跨國治理」提出了多重視角的反省。世界的政治經濟有其體系,隨著跨境的人流、金流與物流都愈來愈繁複,資本尋租的穿透力已經使得乍看起來再如何邊陲的地方,都難以讓人想像遺世獨立。然而,儘管不同資本的力量大小可以極度懸殊,但一旦在地理空間中延展開來,在另一地的主權面前仍必然有其脆弱,這使得每一個地方的治理機制,仍有充份的力量可以發揮有效的槓桿與制衡作用。倡議和行動的人不難找到介入的縫隙,但無論哪一種尺度的治理,最終仍然得要追求每一個地方都能找到協調的發展之道。於是乎,在愈是全球化的年代,愈能貼近在地的角度去發現問題,反而變得益發重要了。
寥寥的五篇作品,當然無法窮盡亞細安的複雜度與多元性。奕諭是人類學家、宗綸和育安是地理學家,三人都曾以研究者的身份在東南亞蹲點生活,選題和寫作中不時透露著學科的關懷,以及源自於在地經驗累積出來的飽滿感。佳禾、婉琪和慕情則是媒體工作者,完成報導的方式是透過多次短期採訪行程的堆疊,處於語言不完全暢通的異文化環境中如何深度挖掘議題、架構觀點和舖陳敘事,其實是專業經歷中極特別的考驗。正因為這樣的差異,這五篇作品的規格稱不上對稱,但話說回來,這也正是製作《走入亞細安》這本書想要達到的效果之一。
臺灣的網路與媒體傳播環境正在改變,而新南向政策對於從關於東南亞的學術知識到普及寫作之間的橋接,也的確起到了紮實的作用。近幾年來,有志對各種知識性、議題性東南亞內容長期進行寫作耕耘的個人,持續勤於討論、製作內容的團隊,乃至於可以容納這些內容的優質公共書寫平台,都比過去增加了許多。《走入亞細安》所呈現的只不過是臺灣一年造訪東南亞那「目的不明」的兩百萬人次裡,極微小的一只切片而已。臺灣人在亞細安,肯定還有更豐富深入的互動經驗正等待被發掘。
策畫主編 林佳禾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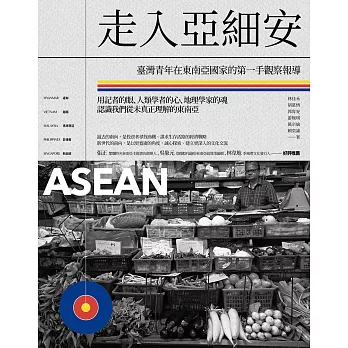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