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就像一頓簡易家常飯的心理治療──適用心理學
有時,某個詞彙如獵鷹般盤旋在心中,又如夕陽下的河水流淌進心裡。「適用技術」正是這樣的詞彙。這個能拯救人們的概念,如此簡單又美好,無法不被它吸引。
在非洲的某座村莊裡,因為缺乏飲用水,孩子們一早就背起水桶外出汲水。他們往往需要步行數小時汲水後再返回,由於孩子們步伐蹣跚,加上水桶破舊,回程幾乎流失了半桶水。獲悉這件事的設計師,與其他人合力製作了圓筒狀的水桶。
之後孩子們的生活出現了轉變。他們像是玩遊戲般將裝滿水的水桶滾回家。如此一來,不僅可以用更短的時間搬運更多的水,也得以更有效的儲存水資源。村民的生活也變得不同了。孩子們原本為了汲水無法去學校,現在也可以上學了。一個如此簡單的水桶設計為日常生活帶來了奇蹟。這是一般常見的成功適用技術案例。
在這個人類夢想遷居火星、航太科技大行其道的時代,仍有一群人因為缺乏簡單且實用的技術而無法過上正常的生活。適用技術的概念,正是源自於對他們的關懷與關注。適用技術同時也試圖找出全球糧食供應充足,卻有許多人因飢餓死亡的原因。
在以人類生活富饒為目標的科學時代,甚至是科學萬能時代,卻只有少部分人過著富足幸福的生活,這是相當奇怪的現象。有些人認為其原因並不在於我們缺乏最先進的科學技術,而是我們日常需要的適用技術不足、資源分配不均所致。這是細膩而偉大的洞察,所以在我初次接觸到適用技術的概念和相關案例時,內心非常激動。
簡單的科學原理和平凡的技術帶來的結果並不平凡,甚至創造出傑出驚人的成果,將原本生活在痛苦之中的灰調人生轉為彩色,就像看著口袋中原本皺巴巴的紙片,經過魔術師大氣一吐變成鴿子、往天空飛去的神奇表演。
只不過這裡還需要加上一點,那就是「洞察他人痛苦的細膩心思與熱忱」。這是將非現實化為現實的奇妙力量,猶如魔術師口中吐出的氣。「適用技術」的概念如宣紙上的墨水滲透進我的內心時,正好與我當時的想法一拍即合。這不僅是我在治療現場(主要是創傷現場)聽著淚流滿面的人吐露心聲時,心中出現的疑問,也是我長久以來身為心理治療方面專家的想法:我們真正需要的不是專家的心理學,而是適用心理學!
證照派不上用場的創傷現場
近十五年來,我與遭受各種國家暴力的受害者並肩作戰,例如一九七〇至八〇年代遭受拷問的倖存者、曾經試圖自殺的解僱勞工、世越號*2遺族家屬等。在治療現場,我清楚聽見他們的痛苦呻吟,目睹他們幾乎不可能撫平的內在傷害。同時我也深刻覺察這樣的事實:心理治療相關的專家證照,在創傷現場根本派不上用場。
在社會災難現場,不僅有心理治療專家,也有社會運動家、一般志工等許多人的參與,但初期過後,現場就很難找到擁有心理治療相關證照的專家。這是我長久以來在各種治療現場中不斷接觸到的現實。擁有證照的專家之所以撤退,並非因為受害者情況獲得改善或好轉,尤其治療對象原本的混亂思緒經過一段時間後,心理上的傷害會更明確表現出來,此時治療師必須給予更多相關治療,然而這卻讓擁有證照的專家愈加卻步。
世越號慘案發生時也是同樣的情況。一開始有許多心理治療專家來到現場,後來幾乎消失不見,反倒是志工的數量隨著時間越見增加,志工們都說:「我沒辦法坐在家裡袖手旁觀,所以就趕過來了。」他們覺得自己什麼忙也幫不了,卻又一邊哭著幫忙打理每一件事。他們為受害者準備食物、洗碗、打掃,嘴上雖然不斷傾訴著自己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悲傷、憤怒與無力感,卻又握緊世越號遺族家屬的手,與他們一起哭泣。
他們這種真誠和態度,給受害者帶來了實質的幫助。現場多次可以看見這樣的場面:志工們以行動和眼神,告訴那些遭受創傷後不再相信世界和他人的受害者:「你不是只有一個人。」這才是真正的安慰關鍵字。
不具備證照的志工們,在現場尋找需要自己的地方,發揮小我的功能。世越號慘案當時,政府和政治家將遭受創傷的被害者壓在地上,在他們的傷口上灑鹽,但是志工們用他們始終如一的行動和悲傷、無力的人類共同情緒形成了「強大聯繫感」,成為拯救被害者的救命繩。
這條堅韌的救命繩充滿了銳不可當的治療能量。在這群志工中,有些人以自身經驗為基礎,用自己的方式輕易道出了治療的原理。或者說,他們根本沒有料想到自己所說的話和所做的行為,其實是最接近治療方法的事情。即便我從旁稱讚他們的舉動,他們也堅稱自己並不懂心理治療,覺得我的稱讚用在他們身上並不恰當。志工以個人的體會和經驗做出的行為,其力量與效果和用理論包裝話語的專家截然不同。
在其他創傷現場中,也不斷出現類似的情況。一開始,志工們雖然在混亂中手足無措,不過最後總能給予受害者幫助;相反地,許多擁有證照的專家一開始挺身而出,用自己專業領域的知識和經驗明確指出需要治療的地方,不久後卻喪失了存在感。與其說他們因為工作繁忙,必須立刻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不如說是因為受害者不再向他們尋求幫助,甚至拒絕他們的幫助,致使他們離開了現場。
這是為什麼呢?為什麼越是心理治療專家,越容易在現場嘗到失敗?如果在人命處於危急關頭的現場,專家都不能發揮自己的功能,甚至這種情況一而再、再而三發生,那麼證照究竟還有什麼意義?
我自己擁有相關證照,所以敢在這裡冒著被誤解的可能,舉精神醫學的例子說明。精神醫學是為了診斷與治療精神病或精神相關疾病,而在學術上或臨床領域上成立的一門學科。在這個領域中,必須固守從疾病的觀點來看待人類痛苦與衝突的傳統,所以精神醫學更重視從「病患」的角度來看人,而非「人」的角度。醫師們從入行開始,就已經習慣這種下意識的治療過程。對於我個人和精神科醫師來說,這種觀點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於是本該為人類最大利益服務的精神醫學或心理學,長久以來與學科原本的期待背道而馳,逐漸脫離了對人類問題本身的探索。
在創傷現場,我曾經聽過受害者向專家懇求「真正有用的幫助」。什麼是「無用的幫助」?「有用的幫助」為什麼幫得上忙?「無用的幫助」又為什麼幫不上忙?
在創傷現場,不少精神科醫師在充分聆聽受害者的悲傷與痛苦前,已經開出藥物處方箋。這是因為他們將受害者表面的痛苦視為主要症狀,並以此症狀作為疾病的判斷根據。這種以神經傳導物質失衡來解釋憂鬱症的原因,並投以藥物減緩病患症狀的行為,當然是只有醫師才能發揮的重要功能。
確實,當失眠或不安等症狀降低了當事人對眼前壓力的抗壓性,為當事人的日常生活帶來更大的痛苦時,利用藥物治療可以一定程度減緩症狀。但是對於受害者而言,失去子女卻遭受他人嘲弄、被傷口撒鹽的他們,已經承受了整個靈魂被撕碎的痛苦,然而醫師將他們視為病患的目光,又對他們造成了二度傷害。
創傷受害者所期望的,是對方將自己當作遭受痛苦的人,而非病患。這並非不切實際的期望。他們只盼望專家們別再反射性地開出處方,而是關懷他們難以啟齒的巨大傷痛,深入理解與體會他們的心情。
受害者的這種期望,並非只有在創傷現場才能看見。事實上,我們所有人在日常生活中遭受傷害、感到鬱悶或孤獨等情緒時,都會產生這種最直接的心理期望。
過去的我不曾這麼想過,然而,現在我已切身體認到包含我在內的所有擁有證照的人,對於人的認知仍存在一定侷限。我現在已經體認到這個問題,並在這樣的覺悟下持續學習與精進。要擺脫這種認知的侷限,其實非常困難。我接下來要說的話,也算是一種告解吧。
我也不例外
每當家中有誰向我抱怨感冒引起的各種症狀時,我總是回答:「那不是什麼嚴重問題,沒關係。可以的話,忍一忍就好。」這句話確實沒錯,但是他們對我的反應很不滿意。當時我無法理解他們為何感到失落,只當他們不了解感冒。因為那種程度的症狀,只要一段時間就能自行緩解。感冒的時候,其實不必吃藥,只要多喝柳橙汁這類富含維他命的食物,充分休息,身體就會自行痊癒。沒什麼需要特別照顧的,也不必特別照顧。就醫學知識來看,這句話既沒有說錯,更不是什麼冷酷無情的話。
但是聽到這句話的對方,想法卻不一樣。即使不是足以致死的重病,也希望他人真心關心自己身體的不舒服;即使是不需要特別治療的疾病,起碼告訴自己日常生活中該注意的事情,或者介紹一兩個偏方,這樣自己才會感到安心。
這些反應的背後,隱藏著希望他人對待自己身體的不適時,別「一副無所謂」的態度。他們期待自己的痛苦能被真誠對待。人類的這種期望或心情近乎本能,在身體健康時是如此,在身體不適時更是如此。
當時我並未察覺這種心情,只把重點放在對方抱怨不舒服的症狀上。在醫學上,沒有進入疾病範疇的所有狀態都是正常的,既然正常,那麼身為醫師的我當然無話可說。但從結果來看,我算是一位無情的醫學技工。
醫師很容易對人們抱持這種先入為主的觀念,我雖然是主要負責心理問題的精神科醫師,也免不了如此,我無法脫離以疾病為治療關鍵的認知。但是大眾對於精神科醫師的想像,又與現實不同。人們期待的精神科醫師,是對人類心理擁有深奧的知識和經驗的人,是心理專家+大腦專家+人文學家+社會學家+哲學家的模糊綜合體。很遺憾的是,事實並非如此。我只能坦白告訴各位,精神科醫師長久以來被禁錮在以疾病為主的醫療觀念裡。
還有更羞於啟齒的事要告訴各位。過去我站在疾病本位看待「人」時,每次在諮商室見到不同的個人,我都像是踏入迷宮般茫然。那時,我甚至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感到茫然無助。我試著從許多學者的理論著手,也積極參加各種學術會議和工作坊,甚至試著全心投入在諮商和累積經驗中。我也曾經就心理諮商向前輩醫師尋求私下指導,仍覺得不著邊際,那種空虛、慌亂的感覺依然存在。如陷五里霧中的感覺,總讓我深感絕望。
在如此困難的時候,其實有個方法能讓我擺脫困擾,一解憂愁。那就是把我眼前所有人都當成病患。
從精神醫學的觀點或疾病的觀點來解釋人,所有問題都會變得單純。因為幾乎所有問題都可以解釋為生理上的疾病,自然簡單得多,接著再根據疾病給予合適的藥物就行。只要那麼做,我就能立刻擺脫自己心中沒人看得見的混亂。因為給予醫學說明後,沒有任何一位病患會提出異議,甚至越是那樣,我越是被推崇為專家,人們也會把我的意見奉為圭臬,因此「醫師(或專家)」的稱號經常能使我感到安定。在天下無敵的證照堡壘中,對於任何一位上門求助的人,我這位專家都擁有絕對的主導權。只要上門求助的人沒有離開我的治療室,我就能繼續發號施令。
儘管我對自己提出了關於人的根本問題,但即使我跳過深入思索答案的過程,證照也能使我誤以為「我深知所有答案」,不會感到不安。但是當我逃避這些問題,就像用棉被蓋住沒有打掃乾淨的汙垢,我的內心對於人類本質的不安與混亂,反倒日漸擴大。
這樣的我,迎來了一個重要的轉捩點:我開始在診療室以外的地方,聆聽人們內在的聲音。近十五年來,我持續與大企業CEO和員工、公司會長、政治人物、法律人等社會各領域的佼佼者暢談心事。
我深入聆聽他們的人際關係、生命與內在的矛盾、欲望與創傷。他們不是找上我講述自身症狀的病患,而我當然也沒有把他們當作病患。他們大多樂意告訴我自己生命的一切和真實的自我。於是我終於明白,在這些人當中,有許多人是過去我在診療室總會接觸到的人物類型;而過去我在診療室見到的那些人當中,也有不少人本質上和這些人並無太大差異。
換言之,我和人們見面的場所(取決於是或不是診療室),深深影響了我如何看待他人。過去我之所以無法將眼前的人視為全然獨立的個體,原因就在於此。我終於知道,長久以來身為精神科醫師對於「人」感到混亂的原因了。
來到診療室的人,多數都是忍了又忍、忍到不得不尋求醫師協助的時候,才前往醫院看診。對他們而言,當下的自己需要他人的幫助,只好放棄尊嚴的底線,被當作病患也無妨。從另一個角度解釋這句話,就是進入診療室後,醫病(醫師-病患)關係永遠是對醫師絕對有利的關係,也是以醫師為中心的關係。
而在診療室以外的日常空間中見到他人時,人們總想努力表現自己的魅力,守護自己的自尊。要在那種日常空間中宣洩真實的心聲,就需要特別且充分的理由才行。
在診療室以外的現場,遇見不是「病患」身分的「人」
在診療室以外的地方接觸過人們的內心後,我才真正知道,走出診療室後,我們是需要在心理上一較高下的。因為他們不把自己當作病患,而我當然也不認為他們是病患。
過去我總是將診療室內的人定義為病患,不自覺地站在醫師的優越位置上面對他們。在診療室外,沒有了「白袍」的保護外衣,這才在聽著他們內心話的同時,發現了過去的自己。在這個世界上,不可能用「病患」的框架來看待對方,還能覺得對方不錯的。那種觀點並不正確,也不恰當。
任何人都有創傷,也有某些比別人更敏感的心思之處。沒有人是例外,再怎麼健康的人,也不可能二十四小時保持健康;有神經衰弱症的人,也不可能二十四小時都活在神經衰弱中。
在診療室以外的地方,看見(非病患身分的)人們的內在後,我過去對「人」感到混亂的內心,也猶如撥雲見日般豁然開朗。在診療室外和無法立刻定義為病患的人溝通的經驗,逐漸改變了我。
現在,我覺得自己可能與傳統意義下的精神科醫師有所不同。也就是說,我對人的觀點或態度可能遠離了同為精神科醫師的同業。我要說的不是誰對誰錯、誰有效誰無效,而是覺得兩者出現了極大的差異。
近十五年來,我白天和企業主、法律人、政治人物見面談心,晚上或週末則到創傷現場陪伴受害者。世越號慘案發生後,我投入了所有時間陪伴受害者。經過這段時期,我才完全找回對人的感覺,脫離了在診療室中經歷的混亂期。事件現場儘管危險,我的內心卻感到前所未有的寧靜、沉著與堅定。
心理創傷的現場猶如野外戰場,所有傷口直接暴露在污染之中,沒有乾淨的消毒室,也沒有手術室。塵土沾附在傷口之上,引起發炎造成日後二次創傷、三次創傷。既沒有可以顯示醫師形象的白袍,也無法仰賴先進醫療設施和設備展現權威。炸彈已經從腦袋上飛過,就像臨時搭建的野戰醫院,得在帳篷內接電提供照明,才能進行手術。在這種地方,不可能放著傷口不管,也不可能用專業知識或口才蒙混過去──其實也蒙混不了。
對創傷受害者而言,他們甚至沒有多餘的精力承受專家的誤判或疏忽。在內外渾身是傷的狀態下,他們無法接受專家任何一點錯誤。情況危急,不得不如此。他們雖然高呼自己不是病患,而是受害者,但是他們比世界上任何一位病患承受著更致命的傷害。在他們袒露自己的傷口前,必須與他們展開一場心理戰。在創傷現場上不可能用證照來顯示治療師的存在感,證照在那裡派不上用場。
擁有證照的人不等於是治療師,能拯救他人的才是治療師。在創傷現場,唯有了解人的本質、創傷的本質後採取行動的人,才可以是治療師。創傷現場更是殺戮的戰場,不能單憑花拳繡腿,要靠威力強大的實戰技術才能贏得勝利。
此外,由於我同時接觸到社會頂端的人,以及人生瞬間被推入泥淖中的受害者的內心創商,我從中發現了一個事實:無論處在什麼情況下,擁有什麼樣的外在條件,總有影響人心的最根本因素。
影響人類生命至最後一刻的,不是環境或情況等外在的條件,而是人類本身。無論是聲名遠播或家財萬貫的人,還是遭逢悲劇的創傷受害者,在他們擁有外在條件之前,他們都只是一個個體。唯有明白這個事實,他們才能從自我內在發現未來的生存方式,這點我比誰都要清楚。至於在劃分出上述兩個極端後,處在這個區間上任何一點的普通人,就更不用說了。這個發現也為我帶來了巨大的改變。
如今我可以說,把生命的痛苦看作是疾病的醫學觀點大錯特錯。不是只有疾病專家的精神科醫師,才能撫慰人心的痛苦,幫助人們正向地省視內心。將「人」視為「人」,才是真正的專家該有的目光與態度。我相信在這個基礎上,「適用心理學」是所有人都能夠善用幫助自己,也能直接幫助家人或旁人的工具。
我親身體驗過的治療原理與機制
自從弗洛伊德研究其門診病患,建構精神分析理論後,至今已過了一百多年。其影響範圍之廣與深,自不必贅言。身為治療專家,我個人觀點中的一部分也是建立在精神分析學的學習與經驗上。我深入研讀過他的各種理論,自然也在他的影響下成為精神科醫師這樣的專家。
但是我在這本書中,並未引用弗洛伊德或榮格、阿德勒等教科書中出現的精神分析學家的理論或學說。我也不認為有那樣的必要。
我想從我個人的視角,談談到目前為止的案例中體驗到的、我所認為的治療核心原理和機制,希望藉由我們社會中每一個活生生的生命故事,提供「有用的幫助」。我將會以我過去個人的經驗為重心,談談實際的治療技巧,這些技巧可以真正為自己與身旁的人帶來幫助,甚至讓你在不知不覺中拯救旁人。
就像適用技術可以改變人類的生活一樣,我希望適用心理學也能達到那樣的效果。我們也可以換個說法,適用心理學不是理論,而是在實際生活中具有實質威力的實用心理學。這個可以幫助我理解自己和旁人內心的簡單心理學,我稱之為「適用心理學」。
如果法律規定只有具備廚師證照的人才可以做飯,我們的生活會發生什麼事?想要解決飢餓,勢必得每天到擁有廚師執照的餐廳排兩次隊才行。如果為了維生而必須滿足的基本需求──食慾,得用那種方式才能解決的話,那麼做為一個人類最卑微的尊嚴將難以守護。
在實際生活中,我們通常自己做飯解決飢餓。雖然有時也會外食,但是並不完全仰賴廚師。即使不吃廚師準備的高級料理,也不會有任何問題,可是如果長時間不吃家常飯,甚至可能造成心理上的不安。那正是家常飯的力量。
像生理飢餓那樣隨時找上我們的,還有在人際關係中的衝突與衝突帶來的焦慮。我們不可能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每次都去找擁有證照的醫師或諮詢師。如果這個問題的頻繁程度就像三餐總會出現的飢餓感那樣,並且每次都得尋找專家幫助的話,如何過上正常的生活?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像家常飯那樣可以自行解決的心理學。
在日常生活中,當飢餓無法獲得滿足時,人們容易感到厭倦、變得暴戾或充滿無力感。同樣的,當做為生命根本的人際關係遭遇衝突而無法獲得解決時,長久下來,不僅容易造成性格扭曲,人生也將困難重重。為了過上安定的生活,我們需要像家常飯一樣的治療方法。而這個治療方法,正是適用心理學。
適用心理學的核心--同理
近來,醫學界總是將造成我們生活不便與困擾的原因,例如精神疾病、憂鬱、不安、怯懦等,歸咎於人腦中的生理問題,並且這股趨勢越演越烈。對於這種偏差的主張,我完全不認同。和我抱持類似想法的精神科醫師不少,但是我們的想法散播至整個社會的速度仍如龜速般緩慢。這是因為目前精神醫學界長久以來脫離醫學、科學領域,轉而進入了產業鏈所造成的問題。
產業鏈的力量對臨床的影響相當巨大,幾乎難以想像。事實上,想要在普遍將不安或憂鬱等問題視為腦部疾病的認知上,創造一個有意義的思考空間,必須有一個強大的新的力量,足以超越製藥公司這樣龐大的資本與政府、媒體建構起的銅牆鐵壁。
這個時代在面對幾乎所有心理上的困境時,都試圖從大腦尋找原因,然而我想要向世人傳達的心理力量,雖然比那圓形水桶的外表更不起眼,卻具有莫大的威力。這個力量可以隨時啟動,也比藥物治療更能快速撼動人心,有效應付真實生命的痛苦。這個力量的關鍵,正是同理。
我所說的同理,是體認到「界線」的同理。關於這個部分,將會在書中詳談。
這個「界線」分明的同理、立體的同理,就像是家常飯一樣的治療,也是適用心理學的關鍵。不知道的人可能會說:「喔,那種東西有什麼好說的。」但是同理的威力比任何力量都要強大。
同理適用於任何人,無論是富裕或貧窮、強者或弱者、知識豐富者或貧乏者、老人或小孩。只要徹底了解同理,你將會像觀看一段紙鳥化為白鴿的魔術一樣,內心為之震動。
2018年9月
鄭惠信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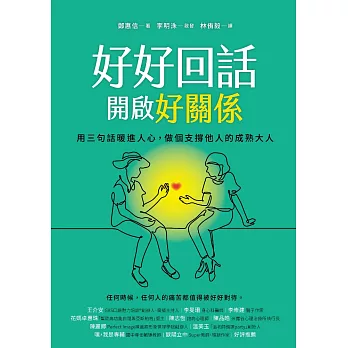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