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時間裡的癡人
黃暐婷寫出了她的第二本創作,長篇小說《少年與時間的洞穴》。小說裡的人物與情節處理得疏宕有致,感覺作者已經從前作短篇集《捕霧的人》裡拘謹的文學青年蛻變為一位成熟的小說家。小說雖說是觸及了奇幻類型的元素,更多的是根植著她細緻的寫實筆法和理解的世事人情。我讀完的感覺是:在奇幻和寫實的交融之處,你有翱翔的的愜意,也有望見樹影的踏實。
小說始於看似主題的「新時」。
新時是時間提早了一小時。關於時差,我們多半只會聯想到日光節約時間,歐美還是現在進行式,有親朋在那兒或者常看美國職業籃球和職棒大聯盟的人們會比較有印象。台灣在上世紀四○年代到七○年代也斷續實施過。初夏時間撥快一小時,夏末撥慢一小時改回來,沒太大的問題。說電腦會因此出狀況,西元二千年預想會出包的千禧蟲最後也沒怎樣。
小說裡提到的時差倒是關聯了政治。台灣曾在日治時期改過一次時間,戰後又改了回來。時區的依違充滿政治性,作者只是略略帶過,並未出現激烈的爭論。或著說作者更大的關注或野心是藉著這樣的小小時差縫隙,撬開更大的時空,來遂行她歷史的尋索。
就我的閱讀觀察,包含黃暐婷在內成長於九○年代之後的寫作者,對台灣認識得更深更廣,小說布局和敘述起來更有底氣。他們持續的追索,使作品帶有時間的縱深。黃暐婷追蹤老照片的人物服飾、面容神情以及光線和氣息;也穿過又濕又暗的神祕路徑來到異國般的古物攤市,瀏覽各式時間遺物,三○年代的寄藥包,木炭熨斗,原版海 報,……等奇妙的老東西。她對歷史未必抵死纏綿,但努力追尋被遺忘的時光,竟也讓她筆下的作家莉卡到臨面對死人骨頭的境界,讓阿美族少年朗展開他在現代都市裡的奧迪賽,一路尋找他的阿公。
作家莉卡與編輯阿基的合作關係與互動是這部小說的一個重要部分。
作家與編輯的往來千種百樣,因人而殊。絕大部分的狀況是雙方就熟悉或專業的部分各盡所能。就算是一般通稱的合作,作家還是得負責完成那個原始的基本的內容主體。她或他的生活,無論絢麗或沉靜,總不免心思上的多岐,「地下社會」般的冒險遊逛也好,只是在名為汽水店喝著實則是類似調酒飲料的小店看著私下被稱為邦迪亞上校的顧客也好,作家莉卡都得獨自度過寫作卡關、停滯的惡夢狀態,一如「被浪打上岸的魚,被惡作劇的孩子翻倒的烏龜,被拔掉一隻腳的金龜子」。
至於編輯,大致是公司政策的執行者,有多少空間,可能因過去成果和掌握的資源而異。曾具編輯工作經驗的小說家黃暐婷,熟識這個行業的眉角,拿捏頗有分寸,不為誇張,寫來倒有幾分幽默。又或者也可視為年輕上班族的日常,有時候也只是尋求一個小小的華麗心情?就像阿基和他的企劃同事米猴每隔一些時日會多走一段路到一家店吃碗麵,為著老闆娘從不會因為匆忙而把油膩的拇指浸到麵湯裡,也為著前往麵店中途有一隻名為咪嚕的貓,會跑過來在自家柵欄邊「沒有節操」地翻肚討拍。
作者沒有要寫小說寫作指南,也沒要寫編輯工作指南,她更重要的是藉這兩個熟悉的腳色開展精心的故事。
僅提出兩個大背景和看法,親自閱讀將會是感受這部具張力和驚喜的小說的好路徑。
◎陳雨航
(陳雨航,小說家,出版人。曾獲《亞洲週刊》十大小說獎、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台北國際書展大獎等。著有小說集《策馬入林》和《天下第一捕快》、《小鎮生活指南》、《小村日和》,以及散文集《日子的風景》等。)
後記
有火照亮的地方
幾年前我讀到一則新聞,有網友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上提案,希望將標準時間加快一小時,從原本與中國相同的時區(UTC+8),改成在經度上與臺灣更為接近的日韓同步(UTC+9),藉此象徵性地與中國切割,向世界宣示我們自己國家的主權。當時引起正反兩方激烈討論,贊成的人相信如此一來可與中國劃清界線,冬日作息也能享受到更多陽光,反對者則認為這麼做只是在擾民。這件事像一顆小石頭,在我心裡產生了漣漪。我忽然意識到,我所依賴的時間,幾點幾分,其實並不是自然的存在,而是人為的、政治性的選擇。不像日蝕,發生時鳥類紛紛歸巢,松鼠回到樹洞,河馬退回水下。時間加快或變慢一小時,太陽不會減損光芒,月亮不會更改潮汐,蜘蛛也不會拆掉編織的網,唯一影響的,只有人的生活。做到一半的夢,可能會因此而中斷。
這個念頭開始在我腦中浮現淡淡的影子。閱讀一些史料後,我發現臺灣歷史上也曾經歷過時區更改,在日本統治五十年間就發生了三次。第一次是一八九六年一月一日,被畫入西部標準時(UTC+8);第二次是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改成與日本相同的中央標準時(UTC+9);第三次是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一日,二戰結束後,又改回西部標準時。第二次更改時區,島內民眾其實也是意見分歧,紛紛在報紙和雜誌上表達自己的看法,有點類似現在的「鄉民意見」、「網友怎麼看」。我忍不住想像,如果更改時區發生在此時此刻,會是什麼樣子?
當時我正好在讀艾加‧凱磊(Etgar Keret)的〈謊言之地〉,關於一個從小遇到麻煩喜歡說謊應付的主角,後來發現自己謊言中的人物都在另一地過著被虛構的生活的故事。我發現這個本質跟寫作很像,跟時間很像。於是,有幾個人物開始從黑暗中走了出來。先是一位在出版社工作的編輯,接著是為下一本書苦惱的小說家,然後是錯過自己年輕時所愛的老人,深夜出門工作的女人,還有始終存在我心中、總是將目光望向這個世界的少年。我決定把時間調快一小時命名為「新時」。然後,小說開始了。
寫作這部小說的期間,我的人生接連發生了幾個意外。我出了一場嚴重的車禍,我的貓女兒罹癌過世。有些人對我背轉過身,永遠離開了。死亡的陰影籠罩我的心頭。我失去了自信,失去對自己的愛。我開始思考自己活在世界上的必要性。某個墜入深淵的時刻,我想起被我擱置的小說。那些角色站在黑暗中,眼神充滿憂傷,對自己的未來感到不知所措。我對他們似乎仍有責任。他們的人生因我而開始,我必須陪著他們走到有火照亮的地方。我仍時常感到悲傷,對自己感到失望。但是寫小說有一個重要的過程,你必須忘記自己的悲劇,才能貼近角色的內心,你的人物才會向你展示他的恐懼和脆弱。我慢慢從痛苦中爬起,握住他們的手,扶著滴著水的洞穴牆壁,一步一步尋找遠方微弱的光亮。
這部小說最終得以離開幽暗之地,出版問世,要感謝許多人的善意。謝謝國藝會提供寫作補助,並容許我延遲一年才寫完。謝謝珊珊主編願意給長篇小說機會,你是這本書的第一個讀者,你的意見對我來說像金一樣貴重。謝謝陳雨航老師與洪明道先生喜歡並願意為這部作品說話,尤其陳雨航老師,研究所時期若是沒有你介紹宮本輝的作品,我不會發現自己創作的源頭是童年時工廠旁那條充滿垃圾的水溝。謝謝我的家人和朋友,我的貓女兒Nori,相依相伴的這十年,你教會我什麼是愛。
最後,也謝謝願意拿起這本書的每一位讀者。我把我一部分的人生交到你手上,願你的心有一處能安放它。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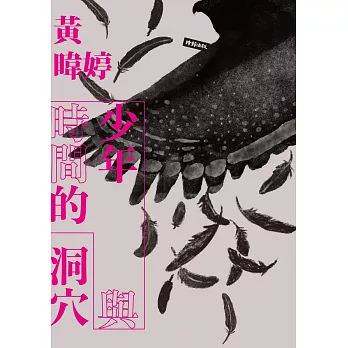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