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序〉
劉俐
海明威在二十二歲時(一九二一)來到巴黎,正值一次大戰結束,法國揮別戰爭的恐懼與匱乏,重獲自由,整個社會沉浸在歡樂的氛圍中,迫切地享受當下,尋歡作樂,夜夜笙歌,展開了一段熱鬧喧囂的「瘋狂年代」(Les Années Folles, 1920-1929)。
海明威筆下「懂得開人生玩笑」的帕辛,每晚吆喝著一批模特兒、吉普賽人和遊手好閒之徒,從一家夜店鬧到另一處酒吧,直到天亮。拉博喝醉了就到街上跟汽車鬥牛,阿波里奈爾牽著他的寵物龍蝦招搖過市⋯⋯巴黎容許理直氣壯地荒唐度日。
相對於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壓抑和美國的清教徒傳統,巴黎的自由、包容和文化活力,吸引了全世界的藝術家、作家到這裡尋找更好的創作環境與成功的機會。
當喬艾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因內容與形式過分大膽在美國被禁,巴黎為他出版;當王爾德(Oscar Wilde)因同志戀在英國受盡凌辱,是巴黎接納了他;當黑人在美國被隔離,飽受歧視,巴黎擁抱非洲藝術﹕非裔藝人約瑟芬·貝克(Josephine Baker)以一齣黑人音樂劇《La Revue Nègre》轟動巴黎,成為「瘋狂年代」的偶像人物,葛希文(George Gershwin)的「一個美國人在巴黎」(An American in Paris)使爵士樂風靡一時,畢卡索也從非洲藝術中找到全新視野。巴黎包容各種性向、各種宗教、各類人種。
當時聚集在巴黎的藝術家,許多成為藝術史上閃亮的名字,如俄國的夏卡爾(Marc Chagall)、蘇丁(Chaïm Soutine)、保加利亞的帕辛、義大利的莫地里安尼(Amedeo Modigliani)、波蘭的季斯林(Kisling)⋯⋯從各種不同種族與文化的碰撞中,誕生了「巴黎畫派」(École de Paris)。常玉也恭逢其盛,但他生性孤傲,家財散盡,潦倒以終。而個性張揚、喜歡奇裝異服的藤田嗣治(Foujita)卻如魚得水,成了巴黎畫派的風頭人物。
藝術家們相濡以沫,也會激辯不休,咖啡館就是他們的聚會之所,特別是各據蒙帕那斯大道(Avenue Montparnasse)一角的「圓頂」(La Coupole)、圓亭(Rotonde)、穹頂(Dôme)形成一個文藝三角洲,每一個嚮往藝術的年輕人都要到這裡過一段波西米亞的日子。三餐不繼,就把畫作典押給咖啡館,或幫客人畫像。一九二四年開張的「精英」(Select)咖啡館,整夜開放,使蒙帕拿斯一帶的歡宴徹夜不眠。揮霍不盡的活力使它成為各種新藝術的實驗場﹕立體派、野獸派,還有顛覆中產價值的超現實主義,他們的聚會經常上演全武行:相互叫囂、大打出手,甚至跳上桌子,吊在水晶燈上玩空中飛人,直到驚動警察來收場。。
在大批湧入巴黎的外國人中,美國人最多,從戰前的六千人,最多時達五萬。因為美金比戰前漲了五倍,「五美元夠兩個人過一天,還可以旅行。」同時美國從一九二0年起推行全國禁酒令(Prohibition),禁止釀造、運輸和銷售含酒精飲料。而在歐洲,海明威寫道:「喝酒和吃飯一樣自然。」他和喬艾斯可以日以繼夜,從天黑喝到天明,各灌下二十杯威士忌。他不只喝威士忌,也接觸到法國各產區的葡萄酒。這位重感官的作家,對吃的、喝的從不含糊﹕從葛楚史坦家的紫梅燒酒到丁香園的蘭姆到佐餐的葡萄酒,都詳加記載[1],巴黎給了他酒文化的啟蒙。
海明威不但有幸在年輕時住過巴黎,還遇上巴黎最璀璨的年代,與眾多各自精彩的人物相遇:葛楚史坦、龐德、費滋傑羅、喬艾斯、畢卡索等。同時,他大量閱讀、旅行、逛美術館和畫廊……這豐富的饗宴,他受益終生。
二零年代之後,他不斷重遊,巴黎是他一生的至愛。一九六一年六月二日飲彈自盡時,他書桌上、打字機旁就放著這本寫給巴黎的情書──紀念他年輕時那段「很窮但很快樂」的日子。
海明威昔日流連之處,多成為巴黎的觀光地標:莎士比亞書店、丁香園、圓頂咖啡、力普小酒館。他住的左岸拉丁區一帶已是巴黎房價最高之處,各種名牌精品店大舉進駐,小出版社、書店、電影院只能一一撤離。
然而,「在巴黎這個城市裡,不管你多窮,都能活得很好。」飢腸轆轆時,還可以去看塞尚。只要塞納河無恙,「河邊永遠不會寂寞」。河岸有看不完的藝術品,從羅浮到奧賽,從大洋洲博物館到阿拉伯文化館,河畔的舊書攤依然是一條結合自然與人文的風景線。夏日黃昏,可以站在藝術橋上看滿天彩霞,待夜幕低垂,對街貝聿銘的金字塔就亮燈了。
海明威的巴黎不再,但巴黎永遠是一席饗宴。
[1]海明威的作品中,什麼樣的人物在什麽樣的情境喝什麼酒都有講究,見Philippe Greene《一杯接一杯 》(To have and have another:A Hemingway Cocktail Companion),(諧仿海明威的作品《To have and to have not 》)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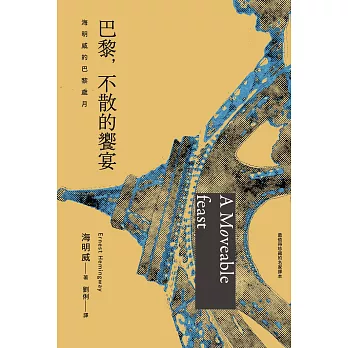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