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爾・麥葛瑞格 透過
紙上博物館《德意志:一個國家的記憶》
向我們展現
一個國家如何從歷史裡找到自我認同
以及國家的意義?
過去一百五十年以來,德國躍升成為歐陸強國,如今他們承擔歐盟東道主的身分,負責維繫歐洲分歧複雜的運作。作者麥葛瑞格回顧了德國歷史上的神聖羅馬帝國,下了這樣的註腳:「那些碎片知道它們屬於彼此,是一個整體當中的小部分。唯一的問題僅僅在於,它們應該緊密結合到什麼程度,而且應該由誰來主導整合的進程。這些都不是英國人和法國人所擅長提出或回答的問題。多虧了神聖羅馬帝國,德國人已經有過一千年的實務經驗。」
作者試圖從德國人對「物件」的創造、挪用、棄用與再利用,編織一部數百年來的德意志歷史。他視野所及包括:雕塑、繪畫、瓷器、紀念碑、建物大門,還有啤酒、香腸、汽車、代用貨幣、字體、潛水衣、馬路上圓孔蓋、塗鴉等等。每件物品背後的歷史,都勾勒出德國的追尋、挫敗與重生,都是集體歷史記憶的一個篇章,也是當權者的意志(見「被納粹貼上墮落藝術的標籤」)和人民重新詮釋(見「柯爾維茨」)的權力爭奪場。
歷經「大浩劫」之後,許多猶太人仍回到德國,德國統一之後,更有二十萬猶太人移居原本傷害他們的國度(見「猶太會堂」)。德國人將罪愆背在自己身上,想要彌補過去的錯誤,但「集體的罪責」之外,他們的一般老百姓如何面對戰爭帶來的傷痛?(見「巴爾拉赫的〈新天使〉」)這裡沒有英雄,只有多元的價值。過去,德國人從歷史裡找尋自我,現在,則要從歷史裡望向未來。
試舉例書內物件:
@啤酒:
除了大家熟知的慕尼黑啤酒節可以盡情暢飲啤酒,啤酒的製作方法也是認證夠不夠德意志的入場券。一八七一年進行德國統一談判的時候,巴伐利亞加入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國的條件之一,就是必須實施《啤酒純淨法》。所謂《純淨法》就是確保只有無污染的水可以使用於釀造啤酒,以維護這種國民飲料的完好性。不過為什麼製酒一定要用純淨的方法?事實上,無關健康與否,而是間接禁止人們用可以製作麵包的小麥與黑麥來釀造啤酒。
@情治人員訓練用的「腓特烈大街車站」模型:
東、西德分裂的時候,兩方之間若有人員要進出邊防,必須在「斯塔西」的監控下進行。這個物件是柏林「腓特烈大街車站」的空間模型,如果把模型翻轉過來,可以看見背面有一個開關和一些按鈕,用意是要訓練「斯塔西」,若有人試圖非法離開東德時應當如何處置。
@國會大廈:由英國建築師諾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負責國會大廈的修建,他設計了玻璃透明圓頂,可供市民觀看議事的進行,象徵公民對政治的控制。不過,國會大廈的命運不是一直都很順遂。十九世紀設立的時候,保王派並不尊重議會;而希特勒根本就移往別的地方舉行議會;到了二戰,國會大廈被俄軍攻陷,士兵還在牆上塗鴉。福斯特重建時,並沒有洗刷乾淨,在巍巍的議會殿堂留下了「希特勒完蛋了」(Hitler Kaputt)的穢語。
@布痕瓦爾德集中營
「布痕瓦爾德集中營」鐵門的內側,裝設了「JEDEM DAS SEINE」的標語,每年重新油漆一次,它不是給路過的人看,而是讓囚犯每天經過大門時,都會看到這句古羅馬法律格言「各得其所」。很諷刺的是,設計字體的法朗茲・埃爾利希(Franz Ehrlich)是包浩斯的藝術家,也是這裡面的犯人。包浩斯卻是納粹所欲肅清的一種藝術風格。而「各得其所」不只提醒犯人國家囚禁他們的正當性,事後看來,這句話充滿玄機,某位囚犯做了一首詩,透露:黨衛軍有天也將被繩之以法。
@柯尼斯堡的人孔蓋:
長久以來,德意志的地理疆界和歷史發展一直都是變動不拘,因此,沒有所謂內在一致、可統攝所有德國人的德國史,這種情況在歐洲國家裡面,算是很特別的。例如哲學家康德的故鄉――柯尼斯堡,如今不再屬於德國,而是俄羅斯的加里寧格勒;文學家歌德發現德國偉大藝術和歷史之泉源――斯特拉斯堡,如今屬於法國。如今在加里寧格勒已不復見任何德國的痕跡,除了地上的人孔蓋。
@慕尼黑「勝利門」:「勝利門」應該是為了紀念自己的軍隊打了勝仗,凱旋而返。但在慕尼黑,「勝利門」被獻給「巴伐利亞軍隊」,卻避開了一件令人難堪的事情:那支軍隊在「拿破崙戰爭」的大多數時候,是跟法軍並肩攻打其他的德意志邦國。「勝利門」因而是一座具有雙重模糊性的紀念建築,它顯露出一個尷尬的事實,那就是敵人很容易就從外國人變成德國人。
@巴爾拉赫的天使塑像
德國沒有年年舉辦紀念活動來追憶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有什麼樣的儀式能夠用來紀念德國不但打輸了,而且還被宣布有罪的一場戰爭呢?一般國家都有高聳入雲的紀念柱或者熠熠生輝的陵墓,但德國反而只有一尊真人大小、水平飄浮的青銅人像,從大教堂的天花板垂掛下來。這是巴爾拉赫(Ernst Barlach)的作品,代表的是「一個紀念而非告誡」,他曾經表示過:我們面對戰爭時的態度應該是回憶與內省。
本文取自左岸文化出版《德意志:一個國家的記憶》
For the past 140 years, Germany has been the central power in continental Europe. Twenty-five years ago a new German state came into being. How much do we really understand this new Germany, and how do its people now understand themselves?
Neil MacGregor argues that uniquely for any European country, no coherent, over-arching narrative of Germany's history can be constructed, for in Germany both geography and history have always been unstable. Its frontiers have constantly floated. Königsberg, home to the greatest German philosopher, Immanuel Kant, is now Kaliningrad, Russia; Strasbourg, in whose cathedral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Germany's greatest writer, discovered the distinctiveness of his country's art and history, now lies within the borders of France. For most of the five hundred years covered by this book Germany has been composed of many separate political units, each with a distinct history. And any comfortable national story Germans might have told themselves before 1914 was destroyed by the events of the following thirty years.
German history may be inherently fragmented, but it contains a large number of widely shared memories, awarenesses and experiences; examining some of these is the purpose of this book. Beginning with the fifteenth-century invention of modern printing by Gutenberg, MacGregor chooses objects and ideas, people and places which still resonate in the new Germany - porcelain from Dresden and rubble from its ruins, Bauhaus design and the German sausage, the crown of Charlemagne and the gates of Buchenwald - to show us something of its collective imagination. There has never been a book about Germany quite like it.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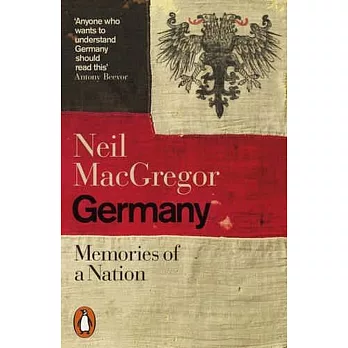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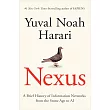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